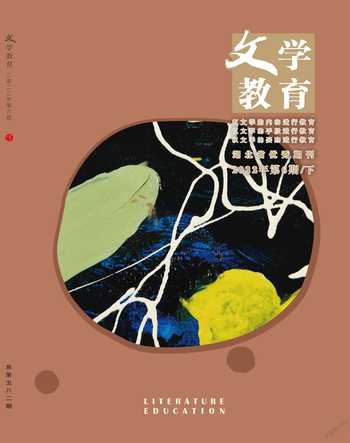形象学视野下张翎小说《劳燕》赏析
黎月新
内容摘要:海外华文作家因其所面临的特殊的文化境遇,身处漂泊异乡的特殊环境,使得在“异国形象”和“中国形象”的塑造上有特殊且独到的方式,这也为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研究从比较文学角度入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牧师比利这个异国人形象可视为“他者”,刘兆虎是被边缘化的“自我”,伊恩与阿燕的异国恋是相互拯救下的恋情。
关键词:《劳燕》 张翎 异国形象 海外华人作家
海外华文作家张翎的小说《劳燕》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浙江温州城一个名叫姚归燕的女孩在战争中遭遇精神和肉体的巨大创伤,在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中与三个男人———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牧师比利和美国大兵伊恩的爱恨纠葛。这三个男人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基督文化、美国青年文化在阿燕身上的碰撞、激荡与互补。张翎以超强的叙事把控能力,使“阿燕”成为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特质、拥有复杂而丰富特征的独特生命体。
张翎所塑造的“异国形象”和“中国形象”蕴含着复杂的文化结构。本文试图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劳燕》 这一小说文本为中心,对其中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与剖析。
一.“他者”:异国人形象——牧师比利
形象学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对异国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同了,宣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1]“牧师”对西方人来说,是沟通世人与上帝的中间人,散发着神性的光辉,而对异质世界中经受着物质窘迫的中国移民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归宿。牧师形象在张翎的小说中尤值得注目。张翎是一位基督教徒,基督文化对她影响颇深,这给她的创作提供了西方文化的视角,加上曾经的故国文化记忆,使牧师形象在东西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文化想象。在《劳燕》中,美国牧师比利生活在东方,却充当着西方文明启蒙者的角色,代表着有神性的救赎色彩的基督教文化。在还没有遇到女主人公姚归燕之前,他在中国乡村做着布道、行医、赈济的工作,在阿燕惨遭日本人蹂躪,命悬一线之时,牧师比利最初以毫无功利心理的从身体和精神上拯救了她:实施手术缝合、用米粥和鸡汤补充营养、给她使用“她可能一辈子都未曾使用过”的抗生素、抄写圣经、在阿燕受村里人欺负之时将她带离四十一步村并且收留她、教会她说英文、将她培训成为一个医生使她有了谋生的手段。这一切都给了阿燕重新站起来的自信和勇气。张翎借美国大兵伊恩的口说出阿燕在被比利拯救后的变化:“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眼睛是直视我的。仅凭这一点,就足够把她从其他乡村女子中分离开来,这大概是牧师比利在她身上留下的潜移默化的美国痕迹之一,她已经和她出生长大的背景有了第一丝的不吻合”[2]。在刘兆虎看来,“阿燕看上去跟从前很有些不同了,阿燕的腰上似乎长了一根新的骨头,走路硬挺挺的。不止是骨头,她仿佛把从前的那层皮肉都换过了——她是把日子从头来过了。”[3]中国传统道德中对女性“贞节”的极端重视与其说是“糟粕”不如说愚昧人性的痈疽,它无法拯救阿燕的生命,却能摧毁她的精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清洗她的耻辱,除了死”,女性自身对这种传统道德深度认可,使得耻辱感伴随她们一生。在阿燕的“重生”过程中,以牧师比利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体现了它的优越,当西方宗教精神介入阿燕的生命中,在宽容博大的基督文化的影响和拯救下,阿燕慢慢消除了自身的耻辱感,“耻辱突然就丢失了震慑力,斯塔拉完成了从蛹到蝶的蜕变。”[4]阿燕最终完成了与耻辱的和解,也因此迎来生命的转机。
牧师比利在小说中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是作为一个“拯救者”出现的。他将西方文明带到中国百姓之间,开化民智,尤其对阿燕的蜕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这一形象实际上透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审视。比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外国人,他有着多重身份,他即是牧师又是医生的,同时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同时还有宗教背景,因此他具有复杂的文化性格。这个人物的设置,既体现了张翎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回归,也体现了对于异国文化的认同。
二.“自我”:被边缘化的中国男性——刘兆虎
“作家们赋予他者形象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总是有意无意在维护、扩张或颠覆自我文化。因此,他者形象一经产生,就会反作用于自己,对自我民族意识发生巨大影响”。[5]如同照镜子一样,作者在创造一个“拯救”的“他者”形象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自我———一个被拯救与边缘化的自我。小说中,在牧师比利和美国大兵的强大力场之下,本与阿燕有最深渊源的中国人阿虎,却被边缘化与旁置了。他的存在或为凸显西方人的优越感、或是突出阿燕的善良、无私与宽容。
刘兆虎与阿燕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她生下来我就认得她了,我不用专门走很远的路去认识她,我早就知道她的一切。我信她,也知道她信我”。[6]原本两情相悦的两个人却因为战争无法走到一起:“假若没有那场战争,这个叫姚归燕的女孩子,会慢慢长大,长成一个美丽的女子——我已经从她的眉眼里看出了端倪。她会找一个敦实可靠,最好识点文墨的男人嫁了,那个人也许是我,那个人完全可以是我。”“可是战争的手一抹,就抹乱了世间万物的自然生长过程。我们都没时间了,我没时间逐渐生长爱情,她没时间悠悠地长成大人。”[7]横在他们中间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贞洁”这道槛。东方传统文化中对女性“贞节”是极端重视的,甚至认为所谓的“完整”比女性的自身的生命更为重要。在那样的环境下的,传统男性认为,女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失贞”,即使她们自身是受害者,都已不再“完美无瑕”,男女间对等的平衡关系已被完全打破。而传统女性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也使得她们永远无法摆脱深深的羞耻感。在当时已受过较为开放教育的刘兆虎也无法摆脱那样的精神桎梏,对贞操依然愚昧地执着。“我知道我可以为阿燕报仇,为她赤脚行一万里路,跨一千次火坑,为她手刃九百九十九个日本人,不惜搭上自己的三条性命。可是,我会认她做我一生一世的妻子吗?”[8]是的,他可以随时献上自己的生命,为阿燕为家人复仇,他给得起生命却给不起爱情。因为这是一种“耻辱”,接受它等就有损于他的男性“尊严”。他对阿妈说的“你若真想认她做婆姨,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想一想,咱家的脸面往哪里搁啊?”[9]深度认可,因此当他回到四十一步村,撞见阿燕被欺负,他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心疼,不是同情,而是感到恶心,“我隐隐闻到了她身上的气味。那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复杂气味,是泥尘的味,呼吸的味,也是身体的味。睡得身体?日本人的?瘌痢头的?还是……”[10]那果真的是气味吗?那不过是对“失贞”的偏见带来的厌恶。阿燕原本以为刘兆虎能够拯救自己,却不曾想被真心维护和依赖的人所厌恶,他实际上抛弃了她,也不可能接受她成为他的妻子。面对这样的刘兆虎,阿燕的心死了。
刘兆虎对阿燕的态度正是传统文化中歧视女性的写照。他所代表的愚昧的传统文化在以美国牧师和美国大兵为代表的先进的文明体系里,被淘汰出局了。西方文化中塑造的东方形象并非基于西方对东方实际的了解,而是基于自己意愿来塑造东方形象,张翎身在异域回望故国时,对故国的观照具有跨越文化和国界的双重含义,其认识和理解也比实际更为深刻,在这里,张翎实际想要借外来者的客观目光透视本土文化中糟粕,从自身角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三.“拯救”姿态下的异国恋情
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异国恋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这必然产生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想认清楚“自我”,“他者”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与大陆作家对西方形象的塑造有所不同,置身于西方国家的海外华文作家,对“他者”有着自己的理解,将东西双方互为“他者”,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美国大兵伊恩和阿燕是以互为“拯救者”的姿态出现的。伊恩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奔一条值得献出生命的危险的路,实践自己内心深处的英雄意愿。当珍珠港遭受日本突袭,美国舰队人员损失惨重之时,伊恩有了参加战争的梦想,二十一岁时他成为了美国海军中国事物团的新兵。如果不是为实现英雄意愿,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自己深爱的亲人和女友,来到一个“大多数人还饿着肚子,竟然可以喂饱如此庞大络绎不绝的跳蚤队伍”[11]的国度,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度,一个被疟疾霍乱伤寒追赶的国度。但美国青年还是来了,正如张翎所说,这是“一个与热血相关的故事”,“一个美国海军在远东战场上和中国军民携手作战的感人故事。”[12]在战场上,他与中国军民携手作战,教会刘兆虎格斗技术,使他赢得了尊严;在情感上,远离故国与文化在异乡无所寄托的美国大兵伊恩,爱上阿燕,给她取名“温德”,渴望她成为他与世隔绝缺乏变化的生活中的一丝涟漪”[13]阿燕在中国的环境里,屡屡受到强奸的威胁,她在乡村里,被无癞强奸,在兵营里,受到中国士兵的强奸,唯一给她爱的,是美国大兵伊恩。大兵伊恩不认为姚归燕遭受的凌辱是耻辱,他看到了一个女性美好而青春的一面,所以他说“只有我,穿越了她的过去,无视着她的未来,直截了当地截取了她的当时。我是我们三人中间唯一一个懂得坐在当下,静静欣赏她正在绽放的青春,而不允许过去和将来闯进来破坏那一刻美好的人”。[14]正是在美国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润泽下,阿燕焕然一新:“她的心长大了,她原先那层哀怨的薄皮再也裹不下她了,她把那层旧皮脱在身后,迎风长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人。”[15]与刘兆虎的纠结与犹豫不同,无论是牧师比利还是伊恩在当时他们的情感都是坚定的,伊恩临走前便想过与温德结婚的事:“我是想和温德结婚。按照战时新娘法,我可以申请她来美国”“我想到战区事务办公室问了申请程序之后,再写信告诉温德。”[16]
阿燕的出现给远离故国的伊恩带来生活中的一丝慰藉。在伊恩受重伤之时,阿燕整夜守在身边,“温德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前守着伊恩,就像先前守着那对母子。这两种守候看起来模样相近,其实本质不同,前面的守候是用眼睛和耳朵,后边是用心”。[17]当伊恩高烧迟迟不退,温德开始“求”耶和华显灵拯救伊恩,在阿燕无微不至的照料下,伊恩终于活了过来。在伊恩准备离开之际,阿燕没有为留下伊恩说出怀孕实情,阿燕留下了他们的孩子,并且抚养成人,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精神和身体的苦楚。如果說伊恩在爱情上给予阿燕以滋润,在精神上给予她力量,那么阿燕的出现则给了伊恩从身体到精神的拯救。可惜的是阿燕并未因为伊恩而结束后半生的苦难。伊恩回国后,没有兑现承诺,而是很快有了新的事业和家庭,这段异国恋也便无疾而终。
海外华文小说中的异国恋故事,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的人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移民作家在海外生存过程中的跨文化的特征。他们生活在东西文明的相互交织影响之下,有着双重文化背景,切身体会着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也感受着过程中的矛盾、与困惑。面对现实的困厄,死亡与逃离是他们赋予异国恋解脱的一个必然结局。
海外华文文学来自“中国”这一母体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既是本土的又是异域的,既是注视者又是他者,“他者”与“自我”交织在一起。《劳燕》中的“中国”不仅代表地理空间,更意味着情感的归属与心灵的皈依。张翎在小说中创作的各类形象,是在跨文化背景下,将母国放置于“他者”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勾勒“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建构“异国”的“他者”形象以重新审视、探寻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1).
[2]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38).
[3]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1).
[4]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77).
[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3).
[6]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5).
[7]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5).
[8]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6).
[9]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6).
[10]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8).
[11]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17).
[12]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95).
[13]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239).
[14]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15]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289).
[16]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273).
[17]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253).
本文为2020年度广西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中的张翎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20KY55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桂林学院(原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