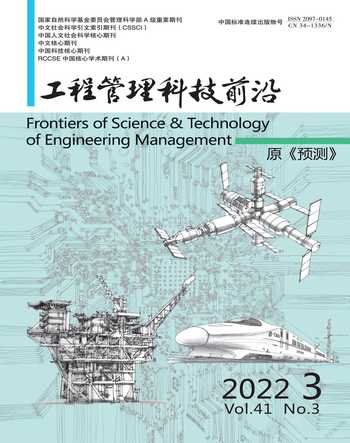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吗?
曹阳 孙晓华 李鹏升





摘 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集聚经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本文以沈阳经济区为例,利用系统GMM和差分内差分方法对南南型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发现: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带动作用不显著,且以往资本投入型的增长驱动模式失效,但一体化政策通过改善区内贸易自由度和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同时,一体化政策实施有利于促进经济的集聚发展,为将来区域内核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创造条件。所以,政府应减少对夕阳产业和落后产业的制度性扶持,集中资源提高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在全域范围内统筹规划,进一步降低城市间发展要素的流动壁垒以提高区域核心城市的首位度。
关键词:南南型区域一体化;城市经济发展;沈阳经济区;差分内差分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7-0145(2022)03-0061-08doi:10.11847/fj.41.3.61
Does South-south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mot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O Yang, SUN Xiao-hua, LI Peng-she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realiz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ion. Taking Shenyang economic zon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systematic GMM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south-south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uth-south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olicy has no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Shenyang economic zone, and the previous growth pattern of capital-input is invalid.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policy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gional economy by improving the freedom degree of trade and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olic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core cities in the region to play a leading rol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could reduce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sunset industries and backward industries, an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reg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imacy ratio of regional core cities, overall plan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further reduce the flow barriers of development elements.
Key words:south-south regional integration;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nyang economic zon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1 引言
改革開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通过20多年的探索成功地完成了当时的国家使命,其尝试和实践的多项改革性政策也逐步得到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如今中国改革也逐步迈进了深水区,国家选择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沈阳经济区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核心区和典型代表,是全国唯一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改革试验区,对辽宁省、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在当下东北经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更是具有一定的迫切性。从2010年至今,沈阳经济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实施多年,那么此项政策是否取得了预期的经济发展成效?区域一体化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区域内城市的经济发展是趋于发散还是收敛?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项复杂的城市系统工程,不同于城市内部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遵循要素流动、产业分工、协同发展的基本范式。其一,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打破城市间的要素流动壁垒,促进商品、劳动、资本及技术的跨地区流动,使市场能够充分遵循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来获取资源,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改善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提高区域整体的生产效率。其二,随着一体化区域内市场分割度的降低,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产业同构现象得以缓解,产业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得以发挥,区域内的分工协作能力增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链条的延伸,有助于增加一体化区域的经济效益。其三,由于区域一体化成员之间的禀赋差异,由异质性成员构成的城市系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协同性,表现为高附加值要素追求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向优势地区集聚,而低附加值要素受制于成本和规模不经济的限制,向周边地区扩散,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相互作用使得不同城市从一体化政策中的获益方向和获益效果存在根本差别。因此,一体化政策效果的评价不仅需要关注一体化系统整体的经济收益,还需要聚焦系统内部各城市的发展过程。
目前关于该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区域一体化和国内区域一体化两个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大量学者开始对此进行深入研究。Henrekson等[1]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影响静态效率,而且对成员国经济增长具有经济和统计上的显著促进作用。Brodzicki[2]对27个发达经济体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发现在长期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成员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呈现积极的正相关关系,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均有利于成员国长期的经济增长。Campos等[3]通过构建反事实情景,研究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加入欧盟的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都获得了提高。总体而言,大多数现有研究表明以欧盟为典型代表的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样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越来越多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很多学者也通过研究证实了其与成员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4~6]。但对于南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均未发现其与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显著关系[7,8]。
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国内发展较早,且一体化水平较高的三个区域。但目前为止,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研究较少,其中卜茂亮等[9]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数,研究指出,在地区高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市场一体化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毛艳华和杨思维[10]则以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指出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政府投入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实中,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其一体化模式类似于国际上的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属于一种强强联合。
沈阳经济区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虽然工业起步较早,但产业以装备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国有企业庞大且体制僵化,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困难,落后产能过剩,劳动力大量外流,经济发展滞后,使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发展不同于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强联合。而这样的情形并非孤立存在,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广泛铺开,截至2010年,国内已形成了23个大城市群、若干个都市圈和同城化发展地区,其中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一体化地区具备较强的国家综合竞争力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在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政策背景下,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使得一体化政策效果的评价无法一概而论,尤其对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慢增长”地区,一体化模式是否依然具有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我们难以从已有研究中找到依据。
基于此,本文将从“慢增长”地区的一体化角度出发,以沈阳经济区政策的实施为例,考察区域一体化方案究竟是否能够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同时,还考察了政策实施后区域内城市发展的收敛性。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首次从南南型区域一体化角度,客观检验了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的总体实施效果,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二是系统梳理了一体化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并据此为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措施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是分别通过σ收敛方法和绝对β收敛方法证实了沈阳经济区当前所处的极化发展阶段,进一步预示了南南型一体化区域先极化后辐射带动的演化过程,为其他南南型一体化区域发展提供实际参考。
2 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2.1 差分内差分方法
差分内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是一种在现阶段被广泛用来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的计量方法,能够有效排除政策以外的其他环境因素的干扰,从而科学地评估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国内外已有学者利用差分内差分方法,研究在税制改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环境改善、政府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实施效果[11~14]。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效果评价提供了有益思路。
该方法最早由Ashenfelter和Card[15]提出。其核心思想是:在政策实施点前后,将一组受政策影响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与另一组未受政策影响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来判断该政策的实施是否产生了效果。Meyer[16]对该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假定政策变化前后,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均能被观测到,那么就可以利用回归模型来估计这一效应
yit=α+βDt+eit(1)
其中yit表示处理组的某经济个体i(i=1,2,…,n)在t(t=0 or 1)时刻的观察值,Dt为虚拟变量,当t=0时,Dt=0;当t=1时,Dt=1。α为截距项,eit为随机误差项。β为用来衡量政策效果的系数,可以通过方程(1)得到,也可以通过计算t时刻前后yit的均值的一阶差分来估计。但现实当中,观测值的变化情况不仅仅受政策实施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诸如经济周期在内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某一经济体受政策实施影响的情况,就必须尽量排除政策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为此,引入与处理组性质相似的控制组来规避由其他因素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使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可靠,所以,给出如下差分內差分模型
yjit=α+β1Dj+β2Dt+β3Djt+ejit(2)
其中j代表组别,当j=1时,表示处理组;当j=0时,表示控制组。Dj为虚拟变量,当j=1时,Dj=1;当j=0时,Dj=0。Djt为虚拟变量,是考察的重点,其系数β3反映了政策实施效果,当t=1且j=1时,Djt=1,否则Djt=0。β1表示实验组和控制组本身的差异,即如果不进行实验,二者之间也存在的差异。β2表示实验前后两期本身差异,即如果不进行实验,也会存在的时间趋势,ejit为随机误差项。此外,在评价政策有效性的模型中,加入一些可观测的控制变量能进一步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所以模型的最终形式设定为
yjit=α+β1Dj+β2Dt+β3Djt+δXit+ejit(3)
其中Xit为影响经济体的控制变量集合。
需要注意的是,差分内差分方法适用的前提是所选对照组在性质上和处理组非常接近,且有相同的时间趋势。相对于沈阳经济区而言,吉林省不仅地理位置毗邻、产业结构和人文环境相似,且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人口持续净流出等现实问题,两者还同时受国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政策扶持,所以,吉林省是本文理想的对照组选择对象。
2.2 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考虑到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战略在2017年后进行了调整,经济区的城市数量由8个变更为5个,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济空间。为了排除政策调整对于估计准确性的干扰,保障政策效果评价的一致性,研究选择2003至2017年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包括沈阳经济区8个城市以及吉林省8个城市。在政策评价的过程中,沈阳经济区战略可以被看成一个自然实验,选取纳入沈阳经济区的8个城市: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和铁岭作为实验的处理组;选取吉林省的地级以上城市作为政策实施的控制组,分别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松原和白城。样本时间区间的确定是以政策实施的2010年为政策时间点,前后共15年的时间跨度。2003年至2009年为政策实施前7年,2010年至2017年为政策实施后8年。同时,我们注意到:沈阳经济区正式被中央批准是在2010年,但经济区建设在2010年前已经开始,尤其处于沈阳经济区核心位置的沈抚同城建设于2007年正式启动。并且从指标分析结果来看,2007作为经济增长拐点的重要时期,我们很难否定经济趋势的变动不是政策作用的结果。因此,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将选择2007年作为第二个政策时间点,对一体化政策效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效果,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ΔGDPi,t=α+α1ΔGDPi,t-1+β1Dpolicy+β2Dyear+
β3Dpolicy×Dyear+δXi,t+ei,t(4)
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ΔGDPi,t为被解释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在考察地区的经济增长时,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能够相对快速地对经济变动情况做出反应,并且可以更好地预测经济增长的趋势,因而政策效果更容易直接体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上。本研究为了便于更好地反映政策的实施是否带来了地区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标来进行衡量。同时,考虑到前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对本期的增长率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因此在模型分析中,引入滞后期的GDP增长率ΔGDPi,t-1作为控制变量。
此外,Dpolicy为政策虚拟变量,沈阳经济区所属的8个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Dpolicy=1,其余城市Dpolicy=0,用来控制经济体自身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year为时间的虚拟变量,2010年至2017年为政策实施年份,Dyear=1,2003年至2009年为政策未实施年份,Dyear=0,用来控制沈阳经济区政策实施以后的时间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虚拟变量交叉项的系数β3代表了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该模型研究的重点。
Xi,t是本文为了剔除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天然差异,引入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控制变量。具体如下:固定资本存量(lncap):用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对数来衡量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值的计算以2003年为基期,通过固定资本价格指数平减后,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劳动力投入(lnlab):利用年末全市就业人口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产业结构(str):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本研究旨在分析沈阳经济区一直以来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升级情况,因此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用三产增加值和二产增加值的比值来表示[17];贸易开放度(open):贸易开放度反应了一个地区对外贸的依存情况,以及国外资本、技术的进入对于国内生产活动的影响,本文用进出口总额与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贸易开放度,其中进出口贸易额根据各年度汇率的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区内贸易自由度(lntrade):区内贸易自由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内贸易活力以及区域内生产活动联系的紧密程度,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区内贸易自由度通过单位产值的货物周转量的对数值来衡量[18],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货物周转量用各地区货物运输总量来代替;人力资本(lnedu):用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反映各地区受教育水平的总体情况;基础设施建设(lnfaci):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前提,本文用城市道路面积的对数值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估计方法
估计面板数据模型一般使用的方法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但是当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时,这两种模型均不能保证参数估计量的一致性。在模型(4)中,解释变量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模型内生性问题随之出现,并且解釋变量中劳动力投入和区内贸易自由度等因素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导致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得到一致、有效的参数估计,Arellano和Bond[19]提出一阶差分GMM,即对差分后的方程进行GMM估计,但一阶差分GMM容易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20]。为此,Blundell和Bond[21]将差分GMM 和水平GMM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即为“系统GMM”,从而有效提高了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Che等[22]也通过实验证明了系统GMM的优势。所以,本文将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4)进行估计。
3.2 实证结果
系统GMM方法要求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因此,本文首先通过检验扰动项的差分是否存在一阶与二阶自相关来判断该方法的适用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模型的AR(2)检验值均大于0.1,所以,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同时,系统GMM方法中引入了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因此,需要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Sargan检验。表1结果中所有模型的Sargan值均超过0.1,所以,同样接受“所有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在表1中,第(1)列为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同时也表明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是合适的。在沈阳经济区与吉林省的差分内差分估计结果中,最为重要的衡量政策效果的估计系数,即政策和时间的交叉项(Dpolicy×Dyear)系数不显著,表明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实施后,其经济增长速度较控制组无明显改善。在第(2)列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以上两个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保持一致,说明结果较为稳健。
第(2)列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中,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型的增长拉动方式已经失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速的提高。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两方面的可能问题:一是新增投资主要流向了现有传统工业产业,并未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增量不提质,产品附加值低;二是新增投资进一步增加了落后产能,导致产能过剩、滞销而拖累经济增长。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同样也说明新增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低效率的传统制造行业,并进一步加重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以上两点表明,目前沈阳经济区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其根源在于占经济主体地位的大量国有企业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缺乏改革与创新。产业结构的系数不显著,也说明沈阳经济区服务业的相对增长主要源于传统服务业,而非现代服务业,即工业化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而传统服务业对以工业作为支柱的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贡献有限。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沈阳经济区以国有企业为主,其主要面向的是国内市场,同时国有企业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引进也相对较少,所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区内贸易自由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沈阳经济区内随城市间壁垒的减弱、交易成本的降低,产品的自由流动更为顺畅和符合市场规律,经济效率明显提高。人力资本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表明高端人才对区域内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表明工业急需从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向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后,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沈阳经济区内部现有的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完全能够满足现有规模工业的正常运行,再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的边际回报较低。
为了确保模型对政策效果评估的稳健性,我们将处于沈阳经济区核心位置的沈抚同城建设的起始年2007年作为政策实施年,来对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重新考察。回归结果如表1第(4)列所示,政策和时间的交叉项系数同样不显著,表明一体化政策实施后并没有给沈阳经济区带来比吉林省更高的经济增长,依然支持沈阳经济区的区域一体化政策目前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与上文的结论一致。同时,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与2010年作为政策点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只是在估计系数值上略有不同,同样说明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4 一体化驱动机制的实证检验
为了进一步明晰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是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我们通过差分内差分方法估计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对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影响。由表2最后一列的差分内差分估计结果可知,2010年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实施后,沈阳经济区在劳动力投入、产业结构、区内贸易自由度、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于吉林省有所改善,但在固定资本存量和贸易开放度方面相对吉林省有所下降。
具体而言,区内贸易自由度的提高表明一体化区域范围内市场分割减弱,促进了商品、劳动、资本和技术的跨地区流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了交易成本;同时使区域内的市场主体能够跨地区进行市场竞争和扩张,不仅有利于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而且在竞争中进行产业整合,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区域优势。目前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級是东北地区产业体系彻底重建的根本之道,也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原动力[23]。产业的转型升级核心要靠科技创新来实现,而高端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所以,培养和留住人才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表1第(2)列和表2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确实通过改善区内贸易自由度和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建国初期,在自身优良的资源禀赋和国家的大量投资建设条件下,东北地区形成了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并据此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地位得到不断强化,但由于开发利用早,当时的重工业技术水平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而东北地区长期的计划经济残留、僵化的制度使国企改革缓慢,地方政府也一直坚持对传统优势产业的财政性扶持,从而形成了大量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的产能过剩企业,甚至是一些“僵尸企业”。 如此情况之下,盲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只会导致更多落后产能的重复建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增长的下降。表1第(2)列的回归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表2最后一列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实施后,沈阳经济区相较于吉林省的固定资本存量增长有所下降,说明一体化政策下使区域内各城市能够从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划,减少以往城市间无序竞争导致的低效甚至无效投资,间接提高了经济的增长。
根据表2的结果,区域一体化政策虽然使沈阳经济区相较于吉林省的劳动力投入、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但在当前环境下,三者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情况的还有贸易开放度,在一体化政策后虽然相较于吉林省有所降低,但同样对沈阳经济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看,尽管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率的提升效果不显著,但通过差分结果可以看出:一体化政策通过对区内贸易自由度和人力资本的改善,也对区域内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影响。那么,在南南型一体化的过程中,沈阳经济区内部究竟是存在着以沈阳市为发展核心的极化拉力,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还是在沈阳市的辐射带动下,区域内城市发展趋于收敛?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南南型一体化政策的有效性。
5 区域发展方式的实证检验
为了明确沈阳经济区内各城市在一体化政策影响下,经济发展存在着发散还是收敛趋势,我们对沈阳经济区内部的经济收敛性进行考察。本文首先通过σ收敛方法对沈阳经济区2003至2017年的人均GDP收敛情况进行分析,在σ收敛检验中,σ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差,若标准差随时间逐渐减小,就表明城市间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存在σ收敛。如图1所示,在2010年之前,沈阳经济区内城市发展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即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在区域发展整体落后的背景下,这更可能是因为作为区域内核心城市的沈阳市发展速度下降所致。而在一体化政策实施后,收敛趋势被抑制,甚至部分年份开始发散,说明沈阳经济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出现了分化。这可能是因为一体化政策实施后,地方保护主义减弱,城市间壁垒降低,人财物等发展要素更高效地流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等较好的核心城市,形成“虹吸效应”所致。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体化政策实施后,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由收敛转向发散,符合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的观点[24],即一个地区基于自然条件、历史偶发事件、倾斜政策等开始出现增长,从而地区间收入差别开始拉大,发达地区不断吸引落后地区的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实现经济的更快增长,进而一个累积性的因果循环开始,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发达地区开始向落后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最终将导致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本文认为,这种地区不平衡发展现象更可能出现在南南型的一体化区域,主要原因在于一体化政策实施初期,区域内核心城市还不足以对周边城市的发展产生辐射带动作用,这也能够间接说明国家间的南南型一体化并不能显著提高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具体到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实施后,以沈阳为核心城市吸引着周边城市的资源并不断集聚,获得更好更快发展,同时也可能使周边城市发展相对落后,形成典型的“回波效应”;但只要有合理、正确的政策引导,实现沈阳市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则必然产生扩散和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加速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均衡。
为了进一步说明以上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利用宏观经济学中常用到的地区间绝对β收敛来反映沈阳经济区发展的收敛情况。绝对β收敛表现为贫穷地区的经济增速高于富裕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贫穷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额逐步缩小,最终,所有地区将收敛于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本文利用沈阳经济区的人均GDP平减数据,构建如下绝对β收敛的基本模型
ΔPCGDPi,t+T=α+βlnPCGDPi,t+εi,t(5)
其中ΔPCGDPi,t+T反映经济区内各个城市实际的人均GDP增长率,lnPCGDPi,t为初始人均GDP,当β<0时,说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其对应的经济增长率越低,由此判断沈阳经济区内存在绝对β收敛。为了明晰经济区一体化政策实施对地区发展收敛性的影响,对观测期进行分时段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由表3第(1)列可知,初始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一体化政策实施前,沈阳经济区内城市发展表现为绝对收敛,而第(2)列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数变为显著为正,说明一体化政策实施后,沈阳经济区内城市发展开始出现分化,区域一体化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以沈阳市为核心的极化发展方式,与上文结论一致。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政策为例,利用系统GMM和差分内差分方法对南南型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带动作用不显著,但通过改善区内贸易自由度和人力资本对区域内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同时,一体化政策实施有利于促进经济的集聚发展,为将来区域内核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创造条件。
根據本文的研究,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减少对夕阳产业和落后产业的财政性扶持,安排“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坚决淘汰落后的过剩产能,并结合沈阳经济区内产业的基础优势,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努力向高端化、绿色化、精细化、信息化和服务化的方向发展。为此,沈阳经济区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外部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培养和留住本地区优秀人才,提高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其次,建立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实行区域整体一盘棋,在沈阳经济区内进行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并进一步降低区域内发展要素的流动壁垒,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在沈阳经济区内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现政企分离、市场化经营,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最后,要进一步提高区域核心城市沈阳的首位度,使其早日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1]Henrekson M, Torstensson J, Torstensson R. Growth effec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8): 1537-1557.
[2]Brodzicki T. New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the growth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EU[R]. International Trad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 2005.
[3]Campos N, Coricelli F, Moretti L.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estimating the benefits from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using the synthetic counterfactuals method[R].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8162, IZA, 2014.
[4]王微微.區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模式选择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5]张彬,朱润东.经济一体化对不同质国家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9,(4):69-74.
[6]Vamvakidis 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2): 251-270.
[7]杨勇,张彬.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来自非洲的证据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2011,(11):95-105.
[8]Vamvakidis 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r broad liberalization: which path leads to faster growth[J]. IMF Staff Papers, 1999, 46(1): 42-68.
[9]卜茂亮,高彦彦,张三峰.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的经验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0,(6):11-17.
[10]毛艳华,杨思维.珠三角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7,(2):68-75.
[11]David C, Krueger Alan B.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4): 772-793.
[12]Branas C, Cheney R A, Macdonald J M, et al..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of health, safety, and greening vacant urban sp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1, 174(11): 1296-1306.
[13]李楠,乔榛.国有企业改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27(2):3-21.
[14]Eissa N, Liebman J B. Labor supply response to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111(2): 605-637.
[15]Ashenfelter O, Card D. Using the longitudinal structure of earning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raining program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67(4): 648-660.
[16]Meyer B D. Natural and quasi-experiments in economics[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95, 13(2): 151-161.
[17]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18]宋蓓,谷艳博,沈玉芳.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京津冀地区差异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8):17-24.
[19]Arellano M, 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 277-297.
[20]Windmeijer F. A finite sample correction for the variance of linear efficient two-step GMM estimator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5, 126(1): 25-51.
[21]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22]Che Y, Lu Y, Tao Z, et al.. The impact of income on democracy revisited[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3, 41(1): 159-169.
[23]赵儒煜,王媛玉.论“东北现象”的成因及对策[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56-64.
[24]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J].管理世界,2002,18(3):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