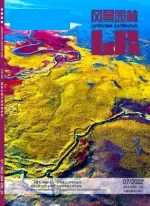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路径
钟乐 赵智聪 王小珊 杨胜兰
2021年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治理而言都是重要的一年。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15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COP15)在中国举行,会上通过的《昆明宣言》提出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开启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征程。202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26th Meeting of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C COP26)在格拉斯哥举行,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Glasgow Climate Pact),为《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的进一步落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2021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科学家首次发布联合报告,代表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协同治理在主流化上更进一步。中国在CBD COP15和CC COP26中都有精彩的表现,持续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方面都发挥出关键性、建设性和引导性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治理都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自然保护地建设是两大战略共同的工作抓手。自然保护地是中国主体功能区中禁止开发区域的核心,是中国“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①。截至2020年,中国已建设总量占陆域国土面积18%的自然保护地,已实现并超过生物多样性保护“爱知目标”中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17%的要求,中国的自然保护地建设已具备国际引领力。中国的自然保护地既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直接载体,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碳库。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管护绩效已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紧密关联。目前,中国已有部分研究从风险评估[1]、规划[2]、管理[3-4]等角度讨论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保护地的响应策略,也有研究评估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的有效性[5],但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有效路径的研究还很少。综上所述,研究二者协同治理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路径已成为必要且紧迫的议题。
1 发展历程
1.1 国际历程
1.1.1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协同治理
当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共荣共损虽已取得共识,但真正在国际环境公约中的协同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掘。通过系统梳理历届《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BD COP)、《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C COP)的决议,探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治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明晰其发展历程的3个特点②。1)早期两者平行发展,直到1998年的CBD COP4才开始在决议中首次出现气候变化相关内容,即“深切关注”由于“异常高温造成的广泛而严重的珊瑚礁白化”,2001年的CC COP7才开始提出与CBD的协同作用。2)历届CBD COP对气候变化的重视逐年增加,CBD COP5的决议中提出通过“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来“应对气候变化等长期变化”;CBD COP6形成专门决议倡导与UNFCCC等合作,并提出评估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从CBD COP7到 CBD COP14都至少有1项名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决议,以及多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其他决议。3)CC COP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不足,涉及生物多样性内容的决议仅在CC COP7、8、10和13中出现,且均仅提及与CBD的协同作用;涉及生态系统的决议在CC COP6、7、8、9、22中出现,仅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几年的CC COP24、25中才开始讨论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显然,与CBD相比,UNFCCC更关注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单向影响,尚未充分认识到二者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导致治理措施往往单一、片面。2021年6月,IPBES和IPCC共同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科学报告》(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tific Outcome),期望将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协同治理推上新的台阶。
相较之下,在区域联盟和国家尺度,二者的协同治理得到了更好的发展。2009年4月欧盟发布的《适应气候变化——迈向欧洲行动框架白皮书》(White Paper–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Towards European Framework for Action)[6]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The EU Strategy o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7]
都承认生态系统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性,鼓励制定“以综合方式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措施”。欧盟多个国家还专门发布了与二者均直接关联的文件,如荷兰的《生物多样性气候防护适应战略》(Adaptation Strategy for Climate-Proofing Biodiversity),英国的《英格兰生物多样性战略气候变化适应原则:保护气候变化下的生物多样性》(England Biodiversity Strategy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rinciples:Conserving Biodiversity in a Changing Climate)和《自然环境适应气候变化》(Natural Environment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等。
1.1.2 自然保护地在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中的地位与实践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自然保护地内受到严格保护的各类生态系统也是重要的碳库,因此自然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共同抓手。国际上,2004年的CBD COP7首次提出将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纳入保护地及其体系的规划和管理中,此后的CBD COP9、10、11、14都在“保护地”章节中提到气候变化,其中CBD COP10所涉及的内容最为丰富,专门将“气候变化”列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从技术准则制定、财务机制设计、关键区域识别等多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②。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也践行了众多行动,200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WWF)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联袂发布了《保护地:增强自然韧性应对气候变化》(Protected Areas:Buffering Nature Against Climate Change),同年,世界银行和WWF将气候变化威胁纳入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ITT)的评估维度[8]。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世界银行、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WCS)、世界自然保护地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WWF、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共同发布《自然的解决方案: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保护地》(Natural Solutions:Protected Areas Helping People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IUCN在2012、2014、2016年分别发布《保护地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概括研究,格鲁吉亚》(The Role of Protected Areas in Regard to Climate Change:Scoping Study,Georgia)、《避风港:减少灾 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保护地》(Safe Havens:Protected Areas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适应气候变化:保护地管理者和规划者指南》(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Guidance for Protected Area Managers and Planners)[9],并于2015年10月成立了保护地气候变化专家组(protected areas climate change specialist group, PACCSG),通 过 了《PACCSG:战略规划2016—2020》(PACCSG:Strategic Framework 2016—2020),提出了6项建议及其近期行动、远景承诺[10]。
在区域及国家尺度,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美国的行动较为典型。欧盟发布了《气候变化和Natura 2000指南:处理气候变化的影响——管理Natura 2000 网络中的高生物多样性价值区域》(Guidelin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 2000:Dealing with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ura 2000 Network of Areas of High Biodiversity Value)[11]。英国发布的《国家公园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n National Parks),从可持续土地管理、低碳乡村社区、适应范例、宣传教育4个方面总结了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12]。西班牙发布了《全球变化背景下的保护地: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规划和管理》(西班牙语:Las áreas proteg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ambio global: Incorporación de la adaptación al cambio climático en la planificación y gestion)[13]。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启动了“气候友好型公园项目”(Climate Friendly Parks Program, CFP)。
1.2 中国历程
1.2.1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协同治理
通过分析“北大法宝”数据库中的中央政策文本,系统梳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协同治理方面的部署情况。中国最早有关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政策文本分别是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但直至2007年才出台有关二者协同的政策文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提出将研究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交互作用、响应机制及其适应技术和措施”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科技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14]。截至2021年12月,有关二者协同的现行有效的政策文本有32份,多聚焦于气候变化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其中仅有5份真正要求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作为气候治理的路径。随着时间演进,中国治理政策呈现出更全面、更科学的明显趋势,仅以中国在NbS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行动为例,即可见这一趋势: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峰会确定NbS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9个重要行动领域之一,指出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式来减排增汇,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能力,而中国和新西兰是应对气候变化的“NbS联盟”的共同牵头国[15]。
中国政策文本所映射出的协同治理的思路主要有:1)适应气候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包括评估气候变化影响、识别脆弱区域、建立影响监测体系、制定适应对策及行动计划等;2)协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气候变化应对,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视为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路径之一,强调彼此的协同增效。
1.2.2 自然保护地在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协同中的地位与实践
2007年,国家海洋局要求在气候敏感区域“选划建设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这是中国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治理协同增效的最早的政策文本。2009年,《国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情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自然保护区立法和建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之一。截至2021年12月,共14份现行有效的政策文本体现了气候治理和自然保护地建设的协同作用,一方面强调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护对于气候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明确要求加强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管护以增强中国的气候治理能力。随着时间的推进,政策文本内容的全面性、科学性也在增强,表现为从局限于自然保护区延展到自然保护地体系,从强调适应气候变化延展到减缓气候变化。
2 优势、机遇和挑战
2.1 优势
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拥有三大天然优势,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管护可以认为是气候治理的根本要求之一。
1)中国自然保护地数量多、面积大,是巨大的天然碳库。截至2020年,中国已建立约占陆域国土面积18%的万余处自然保护地,仅自然保护区就涵盖了全国森林总面积的15.1%、全国湿地总面积的30%、全国荒漠植被总面积的30%和全国草原总面积的11%[16-17]。显然,中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成效紧密关联着中国陆域生态系统碳库的稳定。
2)中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管理措施与气候治理要求天然契合。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是导致生态系统碳库中碳储量变化的关键原因,中国已执行非常严格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其中面向自然保护地的用途管制更为严苛,这些制度和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措施共同作用,保障碳库稳定甚至增加碳汇,对生产、生活、游憩等活动的严格管控要求也与碳减排目标一致。
3)中国自然保护地与气候变化响应关键区表现出高度的空间耦合。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是中国气候变化响应的关键区域[18],这些区域同时又是中国自然保护地集中分布地,仅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总量就超过中国其他地区自然保护区面积总量的数倍[19]。
2.2 机遇
依托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面临着三大历史性机遇。
第一个机遇是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广泛关注。在2021年10月CBD COP15通过的《昆明宣言》中,“气候变化”共出现5次,既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威胁,也强调通过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来适应、减缓气候变化,在同年11月的CC COP26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生物多样性”被提及2次,一是强调确保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并保护生物多样性;二是将保护、修复生态系统及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并形成专门条目进行阐述。结合此前IPBES和IPCC的首次合作报告,反映出协同治理开始成为国际新趋势。
第二个机遇是中国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建设受到的关注日渐凸显。中央政策文本反映了这一趋势,笔者于2021年12月在“北大法宝”数据库进行检索,并进一步统计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2013—2021年所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数量已远远超出会前所发布的文件总和。继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20年中国郑重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后,中国更明确地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组成部分的高度[20]。《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作为“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的内容之一[21],充分表明中国已不再只是单方面重视气候治理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而是更多地开始强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
第三个机遇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工程需要。能够集中体现气候变化应对和自然保护地建设协同治理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主体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能体现二者协同的重大工程则以“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为典型,服务于前述重大战略的各类行动,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这些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成为实现协同治理的行动基础和具体抓手。
2.3 挑战
与此同时,依托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也面临着3个重大挑战。
挑战之一是顶层设计对协同治理还缺乏足够认识。多数中央政策文本将“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地”等视为独立议题,进行了协同考虑的政策也多从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角度展开,很少有政策真正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对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
挑战之二是协同治理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下基本缺位。在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现有治理体系中基本未涉及气候变化:1)法律体系缺位,无论是《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专门性法规、规章,还是《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与自然保护关联的法律中均基本未体现对气候变化的关注;2)资金机制缺位,近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中用于自然保护地的资金种类、项目众多[22],但并无与气候治理相关的资金来源和用途;3)管理体制缺位,分析目前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从各级主管部门到各自然保护地单元,都没有明确负责气候治理事权的机构和专业人员,不同政府间机构也缺乏协调机制;4)社区机制缺位,当前的管控措施能确保社区发展契合自然保护目标,但缺乏提升社区主动参与气候治理积极性的激励措施。
挑战之三是协同治理所需的科学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当前研究集中于气候变化对自然保护地个体单元内保护对象的潜在影响识别和威胁评估,就研究对象而言缺少对自然保护地体系整体展开的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缺乏实施协同治理所需的包括法律体系、管理体制、资金机制、社区机制等在内的多元化研究(图1)。

1 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优势、机遇与挑战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ynergy of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3 建设路径框架
3.1 框架构建思路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提出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框架的3个主要构建思路。
1)适应与减缓协同。自然保护地建设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可分为2类,一是自然保护地对生物分布格局改变、物种分布区漂移和保护地失效等的被动适应,二是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利用NbS依托生态系统碳库进行主动减缓。对于自然保护地来说,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直接关联到保护地存续的关键,而通过自然保护地的管护实现生态系统碳库的保存、增加则是主动减缓的重要路径。因此,不应将二者孤立定策,而应化被动适应为主动减缓,将适应与减缓相融,实现协同增效。但同时也应正视人工营林等增汇方式有可能与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管理目标和管控要求相背离等问题,需在满足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科学地开展主动减缓行动。
2)界内与界外协同。一方面,对于自然保护地的具体治理而言,要有生态系统的整体观,保证在空间上实现自然保护地边界内与外的协同管理;另一方面,对于自然保护地建设、气候治理这两项工作而言,在顶层设计时就要超越不同职能部门的管理边界范围,实现内与外的“跨界”协同治理,即将气候治理内容全面融入自然保护地建设工作,将依托生态系统固碳的内容切实纳入“碳中和”“碳达峰”建设和气候治理工作。
3)体系与个体协同。既在宏观层面将全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视为整体应对气候变化,又在微观层面针对性地对具体的自然保护地单元施策,同时,确保面向整体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路径与行动能够被有效分解、传导至各自然保护地单元,确保形成多层级、多维度、多面向的建设路径框架。
3.2 各类型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核心要点
依据建设工作所作用对象的不同,可将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地建设工作要点分为3类:1)面向本底资源管理,强调对以NbS为内核的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目标为实现本底资源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以及通过本底资源增加碳汇以减缓气候变化;2)面向园区运行管理,目标为减少自然保护地日常运行管理所需的能耗,降低园区的碳排放;3)面向访客管理,目标为帮助访客了解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并促成访客在自然保护地内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活动时的碳友好行为,降低访客的碳排放。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①,由于它们在定位、保护对象、利用程度、管理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建设路径上也有各自的核心要点(表1)。其中,在园区运行管理中融入的气候应对理念适用于各类自然保护地;鉴于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对象存在差异,从生物多样性视角出发,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并不以生物多样性或其载体为主要保护对象,因此对于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面向本底资源管理的建设路径相对次要,但对于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地而言,面向本底资源管理的建设路径均为主要工作;各类型自然保护地应将访客体验和自然教育作为重要使命,访客管理应为主要工作,但由于自然保护区的访客相对较少、活动强度较低,访客管理应为自然保护区的次要工作。

表1 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对象、访客机会和建设要点Tab. 1 Protection objects, visiting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uction priorities of all kinds of protected areas
3.3 具体建设路径
在国家公园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中,工作抓手聚焦于全民认识、法律体系、资金机制、管理体制、社区应对、科学研究6个维度,因此虽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依据工作对象不同,在本底资源管理、访客管理和园区运行管理3个方面各有侧重,但其具体建设路径均包括前述6个维度(表2)。

表2 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路径框架Tab. 2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ynergy of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3.3.1 全民认识
加速协同治理主流化。努力将自然保护地建设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的相关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全教育阶段和全年龄段教育的覆盖。面向全人群开展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并设计、组织、展开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普宣教。
3.3.2 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协同治理相关的法律体系。1)将协同治理的内容纳入相关法律政策体系的制修订,一方面明确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需针对气候变化识别威胁、评估影响并提出适应策略,另一方面明确生态系统碳库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路径之一。2)相关标准、规范、指南和技术导则等的制修订,将协同治理的内容纳入自然保护地标准体系及“碳达峰”“碳中和”的标准体系中。
3.3.3 资金机制
建立健全支撑协同治理的长效资金机制。1)财税投融资机制,包括建设专项资金渠道、打通碳汇相关资金渠道的财政资金机制,以及基于协同治理绩效的碳汇投融资机制和碳汇财税机制。2)社会资金机制,包括申请国内外碳汇相关项目和基金,建立健全体现协同治理绩效的市场交易机制。
3.3.4 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协同治理的管理体制。1)管理
体系,需明确负责自然保护地气候变化治理的事权部门和人员,建立起国内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国际合作与交流机制。2)管理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地气候变化治理的日常管理制度,以及基于治理绩效的监测评估和审计、监管、督查、考核制度等。3)规划制度,将协同治理内容融入国家宏观战略统筹、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1+N”规划体系,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各类型规划。4)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和人才储备机制。
3.3.5 社区机制
建立健全激励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社区机制。1)基于引导生计类型改变、气候移民等的社区适应气候变化机制。2)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激励社区主动减排增汇。
3.3.6 科学研究
奠定科学治理所需的多元研究基础。包括基础研究和协同治理研究两大类。一方面,围绕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保护地所受影响及其治理绩效的调查、监测和评估等展开;另一方面在NbS理念的指导下分别围绕自然保护地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规划和管理技术方法展开。
4 结语
中国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气候治理方面的努力和成绩为全球所瞩目,所作出的承诺更展现出大国责任、大国担当。中国也分别于2019年、2020年明确绘制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气候治理的时间表,将于2025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30年实现“碳达峰”,2035年“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2060年实现“碳中和”。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超过18%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重要的生态系统碳库,它的建设目标要先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完成,显然,确保自然保护地体系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建设成效有助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当下正处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关键阶段,是将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理念融入的最佳时期,本研究所提出的基于气候治理目标协同实现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路径构想,是抛砖引玉式的初步思考,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自然保护地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加入探索,为2020年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治理贡献力量,也为全球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注释(Notes):
①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整理。
② 根据CBD COP历年决议(https://www.cbd.int/decision/cop/?id=7128)整理。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 and Tables):
文中所有图表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