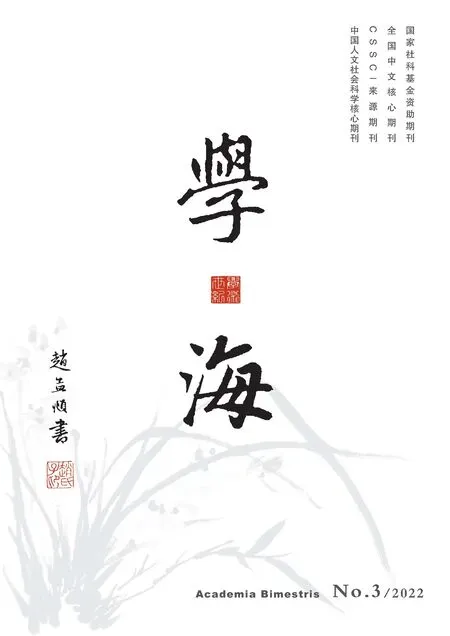受益圈·受苦圈论的理论构成及当下意涵
堀川三郎
内容提要 受益圈·受苦圈论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原创理论之一。受益圈·受苦圈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日本新干线公害问题研究,此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层理论。这一理论着眼于环境问题中受益圈与受苦圈的形态分布,即包括相关群体和相关区域在内的受益圈与受苦圈是否重叠。当受益圈与受苦圈重叠时,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害后果容易得到关注和接受,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当受益圈与受苦圈之间发生错位甚至分离时,环境问题及其损害后果所具有的复杂性,则会使问题难以呈现与解决。在受益圈与受苦圈不重叠分布的情况下,基层自治体无法为受害群体充分发声,使得受害群体的权益维护在深层结构上处于不利地位。受益圈·受苦圈论清晰地描绘了环境问题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有助于大型开发项目的公共性探讨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受益圈·受苦圈论对于环境正义重建与环境问题中的公共性理论构建等具有重要意义。
“事关众人,个人有不便要多忍耐,应该以大局为重”——当你面对这样的话语,内心又难以接受的时候,会怎么办呢?如果将这样的话放在“公共性讨论”的框架下,环境社会学对此又能给出怎样的思考和答案呢?
受益圈·受苦圈论,作为诞生于日本环境社会学的诸理论之一,或许能为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解答视角。这一理论的内涵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理论解释力?本文将尝试对这一系列疑问进行解答。
受益圈·受苦圈论诞生的时间与空间
一个理论或概念的诞生是有过程的,针对什么现象,解决什么问题,经历了怎样的提炼,了解和把握这个过程是评价这个理论概念的重要前提。因为一个理论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试图说明的问题对象的特性。一方面,这个理论能够对问题对象的特质进行有力解释;另一方面,问题对象的特质也可能在这个理论里留下了某种先天不足。所以,对于一个理论主要想说明什么,以及伴随着什么次生问题——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如果不能做到充分理解,就难以进行准确的评价。①
那么,受益圈·受苦圈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受益圈·受苦圈论诞生于1977年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们创立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从1981年开始以名古屋新干线公害问题为主要研究课题,在调查、分析过程中提出了受益圈·受苦圈②概念。③最初以研究会之名出版的著作《新干线公害》提出了“受益圈”“受苦圈”概念,④并成为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公共性问题研究等一系列重要研究的先声。可以说,这个概念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共同研究之中。⑤随后受益圈·受苦圈这一中层理论逐渐形成。如今,受益圈·受苦圈论无疑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⑥
回溯概念诞生的过程,社会问题研究会的畠中宗一首先在1979年做的报告中提及了名古屋新干线公害问题。⑦围绕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由此展开,大家逐渐发现用以往的社会学概念和视角已无法很好地统摄这个问题。另一位研究会成员梶田孝道认为:
大规模开发问题,应该作为被称作“新社会问题”的问题群的一个典型。“新社会问题”频发,换言之即意味着,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斗争,仅用以往的社会问题观、社会冲突观来解读已经很困难。⑧
梶田所说的“困难”,说明大规模开发并不只是在开发计划的规模上或者工程量上的扩大化,同时也伴生着质的变化。一方面,因开发所带来的利益集中在一部分地域而形成了差别分化;另一方面,开发的负面影响又会被强加于人口过疏地区等一些局部地方。因此,这已经不单是社会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主义根本”⑨的问题了。用“受益圈”“受苦圈”这样的新概念来尝试表述当是可行的,如梶田所说:
在各种各样的公害问题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有时重叠、有时分离,有时集中于一地、有时扩散于多处。“受益圈”“受苦圈”以及……“重合型纷争”“分离型纷争”这些概念,正是从事实得到启发而提炼出来的。⑩
上述引用中值得注意的内容有两点:一是从公害问题、地域问题实际调查的“事实”中“发现”了新的问题特质;二是关注到了问题的分布方式。前者充分体现了“基于案例研究进行中层理论建构”这一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特质。后者则明确了受益圈·受苦圈论的理论构想原型,即问题解决的方式会因受害的分布方式而不同。
关于受益圈·受苦圈论,也应该了解其与研究会核心成员舩桥晴俊个人理论建构的内在关系。因为,“受益圈”“受苦圈”既是作为有效解释具体公害案例的概念工具,同时亦是作为舩桥所构想的宏大社会学理论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也即是说,受益圈·受苦圈有两个面向,其一是作为中层理论的个别说明理论,另一则是作为舩桥之理论体系的构件。前者,是它在环境社会学理论中的定位,而后者值得作为一个议题,置于理论社会学的范式革新中进行讨论。
受益圈·受苦圈论的理论构成
社会问题研究会的问题意识是“受益圈”“受苦圈”概念的出发点之一,以新干线公害问题为例,来具体分析这一概念、理论原型及模型构建,得出定义要件有以下四点。
第一要件,“(解释对象)是否能够满足其社会成员的需求”(即“需求满足”要件)。以新干线来说,就要看其是否满足了对“快捷”等便利性的需求。对于能够得到满足的一方,就可以称之为“受益”;而从需要安静生活、不受新干线噪音干扰这一需求来说,无法得到满足的一方,则被称为“受苦”。
第二要件,“受益及受苦是否形成了一个可概括的范围(圈域)”(即“圈域”要件)。用舩桥的定义来说,“所谓受益圈,是指这样一种社会性圈域,它能够使人们因位于圈内而获得在圈子外所无法得到的特定受益”;“所谓受苦圈,则指这样一种社会性圈域,人们由于位属其圈内而要承受外部所没有的痛苦和伤害”。这样,用一种具有空间扩展性的“地域集合体”来定义圈域,受益圈就是使用新干线的全体国民,受苦圈则是承受新干线噪音扰害的沿线地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第二要件并不一定局限于空间。舩桥认为,“这个社会性圈域的定义,虽然从空间的视角来定义最具有代表性,但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或者从抓住代际之间利害对立的时间角度等等也都是可以的。”在此解读新干线公害问题时,我们不妨先确定这一空间维度的定义。
但“加害者和受害者有时候重合、有时候分离”这一分布关系,只用上述两个要件还无法体现出来。因此,需要导入第三个要件,“一种需求(功能要件)得到满足,而另一种需求(功能要件)得不到满足,这种状况是存在于同一主体之内,还是同时存在于其他的多个主体之间”(即“主体的重合”要件)。一个主体同时属于受益圈和受苦圈两方的情况即为“重合”,而如果只能属于受益或者受苦的其中一种情况即为“分离”。也就是说,主体的重合/分离本身也是问题。
第四要件,是地域的重合/分离(“地域的重合”要件)。可以分为受益圈和受苦圈在空间上是重合,还是不重合(即分离)两种情况。地域重合的实例,比如要在某一个基层社区的范围内建一个垃圾焚烧厂等。地域分离的例子,前面所述的新干线公害恰为典型。
基于上述四个要件,受益圈·受苦圈得以定义。对于受害“者”立场与被害“地域”分布方式具体如何影响其后的社会纷争过程,又如何理解“以圈域的临界线为分界,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化”,受益圈·受苦圈概念提供了一个标尺,这是该概念的最大特点。也因此,比起用“层”或“集团/群体”来表述界定,受益圈·受苦圈则成为更好的选择。
这样诞生出来的概念,能够揭示什么呢?下面结合图1来具体分析。
出处:舩桥晴俊:《社会学をいかに学ぶか》(現代社会学ライブラリー 2),弘文堂,2012年,第41页,图2。
首先,可以看到在图1“平面图”部分,深浅程度不一的受益区域在铁道线的左边成片状扩展开来。理论上说,所有能利用新干线的人都能划入受益圈,所以全日本都可以说是受益圈,其圈域是非常广泛的。其次,新干线车站周边的工商业者因上下车乘客带来经营受益,日本国家铁路(现在的Japan Railways)以及与其关联的业界也因为新干线的运行而获得利益,当然也属于受益圈。
与此相对,受苦圈则是沿着铁路以线状分布的,与受益圈的宽泛形成了鲜明对比。噪音和振动与铁路的距离呈负相关,距离越远,影响越小,于是受苦圈就限定在铁路沿线的狭长范围之内。正是由于这种分布形态,“受害居民的抗议,虽然渐渐在沿线区域发生,但相互孤立的情况使他们处于互相不知存在的状态”。所以在提出“新社会运动论”“资源动员论”等理论之前,应该先把受苦圈的分布形态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搞清楚。
然后,再看图1下面的“立面图”部分。平面图表现了区域的范围与延展,而这里所呈现出来的是受益之高和受苦之深。如图所示,“国铁”的受益呈现为一个最高的深色柱体,这是因为“国铁”通过运营得到了莫大的利益。车站前的工商业者以及铁道关联行业也因新干线而受惠,所以其柱形图也向正方向延伸出一定的高度。相比之下,偶尔利用新干线出行的一般乘客享受的便益则是在水平轴上横向展开,以较低的柱形分布。
另一方面,在水平轴以下,表示受苦圈的狭窄而深入的锥状部分一见可知。住在那些狭窄圈域中的人们,每隔几分钟就要被剧烈的噪音和振动搅扰一次,不论是近在眼前的电视声音,还是正通话的电话筒里的声音,都会被淹没。于是,“受苦”部分被绘制成山谷深渊的形状向负的方向延伸下去。被持续暴露在噪音和振动中的沿线住宅,通常在房地产市场的评估不会很高,不论是地价还是房屋租金都较便宜。正因如此,低收入阶层易倾向于在此范围内聚集居住,而这些人实际上基本是不会乘新干线的。所以,这个深受其害的受苦圈和受益圈并不重合,而是分离开的。从图1可以看出,不只是受益圈和受苦圈分离,同时还有“广泛的浅度的受益圈”和“狭窄的深度的受苦圈”这一非对称构造的存在。
受益圈·受苦圈论的认知突破和意义
公害的发生源如果不同,其分布方式也有所不同,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要特意概括一套复杂的概念来进行表述,意义何在呢?或者说,受益圈·受苦圈论的认知突破在哪里呢?舩桥的回答是“受益圈和受苦圈这样的用语,有利于从一些侧面对社会问题进行探索和发现”,“能够对社会纷争发生的根源及其展开过程,甚至社会共识达成的可能性和困难性,进行有效地揭示与说明”。
受益圈·受苦圈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指出受害者与加害者、受害分布与受益分布的不重合,即存在分离之处。在受益圈与受苦圈重合的情况下,由于损害会回到受益者自身(即“受害的复归性”),因此很容易被看见。比如垃圾焚烧厂建在了自己住的小区附近,垃圾问题就一目了然(受害的可见性),那么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但如果垃圾焚烧厂是建在远离自家的地方,在垃圾收集日把垃圾扔出去后,垃圾问题就已经从眼前消失了。于是在受益圈与受苦圈分离的情况下,不但“受害”这一状况,就连对问题本身的感知都很难产生,其解决也就难上加难。因为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提出解决策略之前必须先要向那些没有感受到损害的人证明损害是真正存在的。这种受益与受苦分离的分布状态,不但使受益者难以看到损害的存在,甚至还阻碍了多重参与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
受益圈·受苦圈论的另一项突破是揭示了受苦圈的分布方式与民主表决制度之间的背离。如图1所示,新干线公害的损害分布呈细线状,横跨数个自治社区。而作为基层意见决定单位的自治社区是片状分布的,众多受害者可能不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社区里可能只有住在沿线部分的居民受到损害,因此,虽然受害者有解决问题的诉求,但难以得到自治社区的全力支持。
新干线公害的受害地域,以高架桥两侧各约100米的幅度为轴线,呈带状扩展。因此被称为“线性公害”。……噪音超过75分贝的重度受害住家达到7.5%。被称作“面状公害”的机场公害,受害区域是以飞机起降跑道为中心向四周呈面状扩散的,与之相比,新干线公害的受害对于地方社会来说属于少数人群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就算受害者在人数上很多,但在“线性公害”的情况下,对任何一个自治社区来说,受苦圈的人群分布与有选举权者的覆盖区域是分离的,他们无可抗拒地成为自治社区的少数。由于代表选举制与受害分布形态不一致,使受苦圈人群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这一理论也从受害的分布形态方面揭示了民主制度无法有效运行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那些从新干线获益的行业与经营者,不但不承受其事业所造成的伤害,还要让他人(那些住在铁路沿线却并不享受利益的人们)受苦受害,这一点也在图1中展现出来了。即便此刻不使用新干线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买张票去乘车,因此他们也属于受益圈。但只要不住在新干线铁路沿线,就一辈子也不会属于受苦圈。再看看住在沿线的人,要从早到晚、一年到头、持续不断地受到新干线噪音和振动的侵害。的确,他们说不定也会有乘坐新干线的时候,但这不过是短暂一时的受益,而受害却是一辈子的事。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搬家,就终其一生无法从受苦圈中解脱。应该说,这种无法交换立场的非互换性结构,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结构。“只受益”“只受害”这样的圈域的存在,以及其结构逐渐固化的状态——除了“不平等”,别无他物。受益圈·受苦圈论所明确的,就是“广而浅的受益圈”与“狭而深的受苦圈”这种不平等结构的存在。大规模开发造成了严重的公害问题,其受害结构包含着极度不平等,这可以清晰地描述出来,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突破。
“为了广而薄的国民受益,而强使极小一部分圈域承受深刻的伤害是合理的吗?”这一构造使我们面临着社会与伦理的质问。在受益与受苦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受苦者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多数国民来说,能够维持快速舒适抵达目的地的方式,自然是更理想的选择,但为了实现这一选择而被迫受苦的人们却是没有选择的。能够做的选择和无法避免的强迫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其他概念就没有办法看出这一问题构造。试用成本和效益这两个用语举例,受益圈和受苦圈的分布呈现分离,也只是成本和效益不重合,二者处于分属其主体的状态,那么使用成本和效益,就不但不够准确,甚至还会造成对问题构造本身的认知失误。就算在考量涉及“我”自身的便益(受益和受苦)时是贴切的,但在把“我”和“某他”的便益放在同一面上进行讨论的时候就无法适用了。对于主体A的便益尚且不得而知,要对主体A之受益和主体B之受苦进行比较就更谈不上了。这是提出受益圈·受苦圈概念的意义所在。
因此,文章开头提到的“事关众人,个人有不便要多忍耐,应该以大局为重”这种话,并不完全合理。因为“像新干线这样的大规模事业,受益者(乘客等)和受苦者(建设地域居民)之间的立场明显相异,对于事业本身及其具体规划的是非评价,双方也是对立的”。只属于受益圈的人,对基本享受不到其“益”却要一生背负其“害”的受苦圈的人说“忍忍吧”,其中有多少道理和正当性呢?所以,受益圈·受苦圈论可能会使“新干线的公共性”本身也相对化。
如舩桥所说,“如果把支配体系也纳入考虑的话,伴生着公害与受苦的新干线设施供给,就是‘掠夺型共同便益性’,而并不是以‘具备普遍性的共同便益性’为规范理念的(公共性)”。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性)这个词语,非但不能作为形成社会认同的共通基础,反倒成为引起人们之间纷争的用语”。注意,舩桥的这番话,并不是单纯为了解决问题而批判国铁的,而是想要建构一种“作为规范性理念的(公共性)”。能够明确描述出现实发生的环境问题的构造,探索解决问题的条件,对公共性的再构建有所贡献,将成为受益圈·受苦圈论这样的理论的意义所在。
理论的发展与批评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大规模开发问题及公害问题,日本学界主要从三个方向推进了受益圈·受苦圈论的发展。第一是“圈域的精细化”;第二是向“数理社会学的公式化”推进;第三是成为舩桥晴俊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在第一个“圈域的精细化”方向上,有学者推出了重要的概念,即“疑似受益圈”“疑似受苦圈”。比如某一问题导致的受苦圈,其中一部分通过补偿得以受益,“受益圈化”后被称为“疑似受益圈”。补偿手段,包括送慰问金、优惠贷款或者以有利的土地置换等。“疑似受益圈”概念的导入,有助于明确对立构造的双重化,使问题在宏观层面上形成“扩大的受益圈和被局部化的受苦圈”的对立,在微观层面上形成“疑似受益圈和纯受苦圈”的对立。
此外,梶田还将受苦圈概念进行了类型化。比如在时间上,提出了“事后的受苦圈”(例如1959年开始施工的东海道新干线)与“事前的受苦圈”(例如1982年开始施工的东北新干线)等受苦概念的次级分类。又如在空间上,进行了“线形态”(如新干线公害)、“面形态”(如大阪机场噪音问题)、“点形态”(垃圾处理厂建设问题)的细分。这些是将时间轴和空间轴嵌入受益圈·受苦圈论的尝试。
第二点,“数理社会学的公式化”方向是指与数理社会学,特别是与社会两难论的结合。首先,海野道郎用集合理论对受益圈·受苦圈论进行再公式化,加入了舩桥和梶田的理论中所没有的“社会(无关系)圈”“两难圈”等概念(表1,图2)。由于在以往的讨论中没有对概念的外延进行定义,以至于无法充分实现类型化,但如果像表1以及图2所示,对作为全体集合的“社会”和“两难圈”也进行定位,就能够使受益-受苦的分布形态得到更详细的描绘。尤其涉及社会纷争时,往往是这些属于“两难圈”的人们决定着问题的走向,因此,上述概念化是非常重要的进展。

表1 受益圈·受苦圈的理论关系
出处:海野道郎:《“社会的蟻地獄”からの脱出——共感能力の獲得を目指して》,《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1982年第45号,第100页,表1。
出处:海野道郎:《“社会的蟻地獄”からの脱出——共感能力の獲得を目指して》,《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1982年第45号,第100页,图1。笔者基于原图制作。
同时,从“两难圈”的提出可以看到受益圈·受苦圈论和构成数理社会学分支的“社会两难”论的交集。舩桥通过发表论文《作为“社会两难”论的环境问题》,将受益圈·受苦圈论向“社会两难”论进行了延展。文章首先表明“所谓‘社会的两难’,……就是以集体财产为焦点的‘合理性的背反’现象”,而环境正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财产。然后,“从‘受益圈和受苦圈的重合与分离’以及‘得利·损失维度的单一性与复数性’这两个视角来更加详细地”进行类型化。从这一段引用可知,前面关于利害圈的部分借用了受益圈·受苦圈论的成果,而后面的利害维度部分则使用了舩桥与其他研究者共同提出的理念。以这两项标准为基础,得到了八种类型(表2)。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往往是包含着这些基本类型的混合形态,因此可以说受益圈·受苦圈论在精细化上有了一大进步。
表2 受益圈·受苦圈的八种基本类型
出处:舩橋晴俊:《“社会的ジレンマ”としての環境問題》,《社会労働研究》1989年第35巻第3-4号合併号,第40页,图1。笔者基于原图制作。
第三个方向,是作为舩桥晴俊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展开的。前面有所论及,受益圈·受苦圈论是舩桥理论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受益圈·受苦圈论因为舩桥的早早离世而未能在其生前公开刊行,但其全貌可以通过阅读2018年出版的舩桥著作得知。
舩桥的理论,由三层构造组成(图3),最基础的理论是“原理论”。面对“社会以及构成社会并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人是以怎样的基本方式存在”进行问答,为“基础理论”提供支撑假说。舩桥的“存立构造论”对应这一部分。
“基础理论”,是以“原理论”为基础,是“以较原理论更具体的标准,为掌握社会现象提供具有一般性的基础视点和概念框架”的理论。比如协同联动的两义性论、环境控制系统论等,均属于此类。
“正如R.K.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通过为社会现象的有限部分提供经验数据,对规则性进行把握,力图发现意义的一系列概念群和命题群”。“基础理论”发挥着统合“中层理论”的功能。本文讨论的受益圈·受苦圈论,正是作为“中层理论”之一,取得了其明确而稳固的地位。
出处:舩橋晴俊:《反訳·編集·補筆=堀川三郎·高娜·朱安新》,《日本環境社会学の理論的自覚とその自立性》,法政大学社会学部《社会志林》2016年第62巻第4号,第21—33页;茅野恒秀、湯浅陽一編:《環境問題の社会学——環境制御システムの理論と応用》,東信堂,2020年。笔者基于以上文献制图。
但是,受益圈·受苦圈论也受到一些批评,主要可以梳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批评是“由谁来定义‘什么是受苦圈’呢?”(即进行定义的问题)。带谷博明认为,在讨论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问题时,要设定受益圈·受苦圈,就需要先回答到底什么是受益、什么是受苦,以及当事主体的认识过程是怎样的,但是受益圈·受苦圈论却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存在着一个功能主义的前提假说,即“根据需求或者功能等要件的满足/不满足,可以将受益和受苦作为空间的范域,从外部进行客观的观察”。由谁、凭什么能够判定“这就是受苦圈”呢,研究者真的能够抛开当事者主体的认识过程从外部进行观察和定义吗?这些仍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批评是关于圈域内的共通性问题,换言之,可以说是分析单位的问题。对机场噪音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的金菱清指出,“受益圈·受苦圈模型是以一部分人群的共同受益、共同受苦为前提的”。在问题的展开过程中,圈域内的每一个个人的状况会不断发生变化,而“以共同受益、共同受苦为前提”的理论构成,则无法应对这种状况。带谷也认为“在社会生活受到强烈影响的水库淹没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对立”,“对于多层多样化的受淹地区的住民,其受益·受苦认知已经难以用‘圈域’来进行把握”。所以,如果用“圈域”作为分析单位,就不得不假定圈域之内都是一样的,那么每一个人经验中各不相同的受益·受苦认知就得不到体现。
从这个角度说,上述问题也会影响到受益圈·受苦圈论在舩桥晴俊理论构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前面谈到,作为舩桥更宏大的社会理论(可以说是社会学原理论)的一部分,受益圈·受苦圈力图对更宏大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它假设了一个受益圈·受苦圈的圈域内是均质的,受益圈·受苦圈具有一个凝练一致的内核。那么,一方面要有力地刻画出宏大的社会结构中受苦是如何不平等地分布着;另一方面却因为设定了圈域内的一致性而无法看到受苦的多样性。这种矛盾要如何解决呢?
第三个方面的批评,是圈域的多层性问题。在对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建设地址问题进行分析时,中泽高师提到“多个受益·受苦的结构形态可能重复地产生,从而形成叠加的多层性”。比如,某一地因为运作中的垃圾处理厂A已经产生了受益圈和受苦圈的对立,又规划了垃圾处理厂B,那么垃圾处理厂A造成的事后受苦圈和垃圾处理厂B引发的事前受苦圈的对立就会发生,“仅以受益圈·受苦圈论所设想的‘受益圈和受苦圈的对立’构图就无法把握整个事态”。因此,“需要把‘受苦圈和受苦圈的对立’这一构图也纳入视野中来”。当多个受益圈或受苦圈在同一地域社会内同时产生时,该如何分析受益圈·受苦圈呢?这一批评也非常重要。
虽然存在以上批评,但受益圈·受苦圈论所带来的认知突破,对于推动宏观理论建构的意义很明显。在对大规模开发工程等进行分析时,尤其对工程的公共性进行讨论时,受益圈·受苦圈论亦被认为是具有贡献的。
大丫说,舒曼在他下乡那个镇的西山上,给他那个不得志的养父建了一个纪念牌。碑建得挺洋气的,正面是他养父的塑像,碑文上记载着艺术家一生不得志的故事。建成那天,舒曼在碑前播放了养父最喜欢的世界名曲。还陪着他养父在山林过了一夜。正是深秋,晚上又下了很急很厚的雨。秋风秋雨,舒曼就那么挺着,回想着同他养父共同度过的那些日子。舒曼说,他的养父活着的时候,总是喜欢对他讲那些世界著名音乐大师生前潦倒穷愁的故事,养父希望他们贫穷的日子能过得更典雅一些,充满着幸福的旋律。可舒曼想,不能再学自己的养父,光认艺术而不认钱了。为艺术家流泪的日子该过去了!
综上所述,虽然对于把握圈域内“受害”的多样性,可能需要再提炼新的概念,但对大规模开发项目及发展中的公共性进行追问探讨,受益圈·受苦圈论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对东日本大震灾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激烈而深刻的受害事态进行思考时,这一明晰的概念也是有效的。比如核电站基地的建设,只选人口稀少的地方,完全避开作为电力主要消费地的大都市,这一现象不用受益圈·受苦圈论就难以说明。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形成了跨越国境的受益圈和受苦圈,但是日本关于核电的新规划,恐怕还将会在东亚区域内造成事前受益圈和事后受苦圈的对立。受益圈·受苦圈论,在解决了几个理论方面的问题之后,对于今后的核电问题亦有做出理论贡献的可能。
①参见Sen, Amartyá K.,InequalityReexamin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载池本幸生、野上裕生、佐藤仁訳《不平等の再検討——潜在能力と自由》(岩波現代文庫G393),岩波書店,2018年,第1—52页。
②因此舩桥说这个概念“并不是特定哪一个人的提案,而是共同研究的成果”。参见舩橋晴俊《環境問題の社会学的研究》,载飯島伸子、鳥越皓之、長谷川公一、舩橋晴俊編《環境社会学の視点》(講座環境社会学 1),有斐閣,2001年,第57页。实际上,虽然参与研究会的成员有舩桥晴俊、长谷川公一、梶田孝道,但是应该承认发挥了最核心作用的是舩桥晴俊。参见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28页;海野道郎《現代社会学と環境社会学を繋ぐもの——相互交流の現状と可能性》,载飯島伸子、鳥越皓之、長谷川公一、舩橋晴俊編《環境社会学の視点》,(講座環境社会学 1)有斐閣,2001年,第164页。另外,由于多位成员各自独立开展研究,(理论概念是)经由多人的思考讨论而形成,所以要明确诞生时间也比较困难。事实上应该说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另可参照角一典《受益圏/受苦圏概念に関する省察——可能性と課題》,《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2003年第53巻第2号,第79—89页。
③参见舩橋晴俊、長谷川公一、畠中宗一、勝田晴美《新幹線公害——高速文明の社会問題》(有斐閣選書749),有斐閣,1985年,第315—316页;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28页;茅野恒秀、湯浅陽一編《環境問題の社会学——環境制御システムの理論と応用》,東信堂,2020年,第80页。
④参见舩橋晴俊、長谷川公一、畠中宗一、勝田晴美《新幹線公害——高速文明の社会問題》(有斐閣選書749),有斐閣,1985年。
⑤舩桥晴俊也有相关表述,认为“受益圈和受苦圈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生的新干线公害以及垃圾处理厂建设等地方环境议题,尤其是公害问题的案例研究”。参见舩橋晴俊《受益圏·受苦圏》,日本社会学会社会学事典刊行委員会編:《社会学事典》,2010年,第752页。
⑥参见鳥越皓之《環境社会学》(放送大学教材12486-1-9911),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9年;舩橋晴俊、宮内泰介編《環境社会学》(放送大学教材1837613-1-0311),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03年;鳥越皓之、帯谷博明編《よくわかる環境社会学〔第2版〕》,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年;堀川三郎《受益圏と受苦圏》,友枝敏雄、浜日出夫、山田真茂留編:《社会学の力――最重要概念·命題集》,有斐閣,2017年;長谷川公一、浜日出夫、藤村正之、町村敬《新版社会学》(New Liberal Arts Selection),有斐閣,2019年。
(夏多曼 朱安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