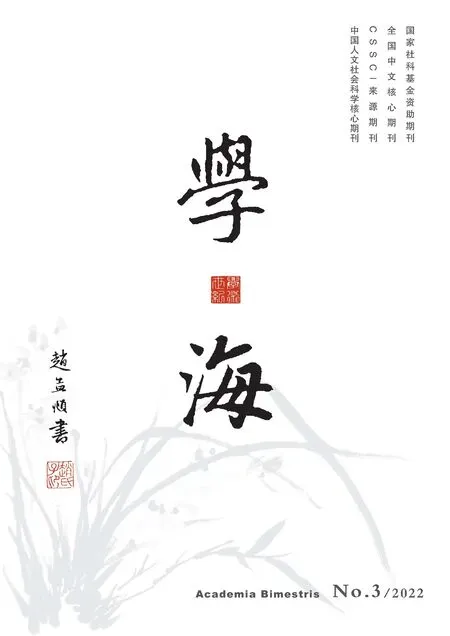由井及坊:曲村的邻里研究*
陈阿江 常巧素
内容提要 邻里介于家户与社区之间,是构成社会的一个基础性单元,但因其边界的不确定性,可操作化的研究仍很缺乏。本文通过对太行山缺水地区的实地调查,探讨因水而建的作为邻里的地域共同体井方。由于日常用水需要,邻近居民共同集资、投劳建设水井,进而圈定用水边界、构建用水共同体。长期共居一地、共用一井,形成稳定的地域共同体。井方内居民互帮互助,相互监督用水行为,乃至日常行为。以井方为单元的宗教活动与世俗文化活动,为本街坊居民提供了娱乐活动,也增进了街坊成员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地域社会的整合。
导 论
在社会学专业的概念体系中,有一个介于家庭与社区之间的中间概念“邻里”,或“街坊”。然而,无论是邻里还是街坊,都不像家庭、村落(社区)等概念那样边界清晰,一目了然,这样的概念无疑给社会学专业的学习者与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惑。那么邻里、街坊的边界在哪里?它是怎样的一个社群?它内部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本文借助河北涉县曲村①内部井方之邻里案例展开研究,回应这一话题。
在汉语词汇中,“邻里”一词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据《论语》记载,原思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小米九百,他不肯受。孔子说,不要推辞了,有多的就给你的邻里乡党。杨伯峻注释说,邻里乡党都是古代地方单位的名称,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②这样的注释可能过于理想,实际可能没有那么明确,从孔子说话的语境看,大意是说你有多余的就给你的乡里乡亲吧。
社会史学者雷家宏对中国古代乡里结构进行过系统的梳理。根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曾有过乡、遂制的设计。遂之下划分为县、鄙、酂、里、邻五级,五家为邻,五邻为里。③实际上,不同时期基层的设置各不相同,但大致形成由户而上的不同层级的管理单元。如北魏孝文帝时期设立“三长制”,村落居民按地域关系每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里,每五里为一党。④历史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官方在基层设置管理单元的演变情况,但在民间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未必严格按照某个历史时期所设定的邻或里来确定具体的户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描述了江村的邻里,他大概传承了中国古代五户为一邻的说法。他说:“这个村里习惯把他们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对此,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乡邻’。”⑤但费孝通随后在谈到日常生活中的互助时,又说:“此种相互帮助的关系,并不严格地限制在十户人家之中……”⑥
费孝通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邻里是这样被定义的:“邻里是依靠地域这个自然条件,如房前屋后,左邻右舍,经久相处,友好往来,逐步形成的一个守望相助、共同生活的小型群体。”⑦综合《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及其他文献,⑧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社会学概念,邻里的含义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
第一,邻里是一个社会群体。
第二,邻里是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或首属社会群体(primary social group)。
第三,它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地域边界往往与邻里的规模相呼应。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社会学的研究中,邻里的地域边界或规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们理解与研究它带来一定的困难,以至于邻里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社会学概念。
在社会学专业里,街坊与邻里在等同意义上使用。但就汉语的词源看,街坊与邻里有所不同,邻里更多地强调社群(若干户),而街坊则更多地强调地域。《辞海》对街坊的解释有三层含义:(1)街巷、坊里;(2)现代城市由道路或自然界线划分出的居住地块;(3)邻居。在社会学专业里,之所以把邻里与街坊置于同一意义上使用,是因为无论是邻里还是街坊,都是在“人群”+“空间”这两个复合意义上使用,即它们是指在特定空间里的有密切关系的初级社会群体。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型,现实中的邻里或街坊与理想型有较大的差距。
社会学术语的邻里或街坊来源于英语“neighbourhood”。关于“neighbourhood”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community”一词。在最新版的《牛津社会学词典》里,neighbourhood被视为community,⑨这大致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现状。社区的概念,来自滕尼斯1887年出版的“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他在该书中指出,社区的本质是关系,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⑩基于共同生活的地缘邻里共同体,正是他提出的三种基本共同体之一。“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被引入美国后,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将其翻译成“Community and Society”,同时为“community”赋予地域性含义。但随后,帕克等便指出家庭和邻里这类组织在城市社区中逐渐解体,它们在社会控制和道德秩序方面的权威和影响力也不断削弱。
从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出发,邻里研究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研究。作为社会学家兼建筑师的佩里,吸收帕克等芝加哥学派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并将其应用在城市规划中,发展出城市规划经典范式的“邻里单位”理论。即以学校或教堂为中心,规模约5000人,占地约160英亩范围的生活圈为一个邻里单位。新城市主义、城市规划等学科大多沿着这一路径,以某一中心为核心,扩大或缩小半径,规划城市居住区。另一条是关于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邻里效应”的研究。“邻里效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由威尔逊(William J. Wilson)1987年的著作《真正的穷人》所引发。他指出,贫民区对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的态度和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由此掀起了以生活区为邻里范畴的邻里效应研究的热潮。这其中包括邻里对犯罪、儿童社会化、个体心理健康、环境与贫困等多方面的影响研究。
正是基于这两条研究路径,西方邻里研究在2000年前后形成一个小高潮。人们认为在信息时代,家庭、宗教等在工业社会里建构的社会凝聚力被逐渐瓦解,社会出现新的凝聚力危机。而“邻里”,正是作为重建凝聚力的一个切入口,在新世纪得到重视。
我们最近在研究水议题时,在干旱缺水的太行山农村发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理想型的街坊邻里。经过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井方正是村内因用水而形成的邻里或街坊单元。它是一个地缘组织,虽然井方之内也嵌着深厚的血缘网络,但它是依托地缘而建成的地缘组织单元。它根据用水的原则设定了明确的边界。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从建井护井,井方内的互助、监督,到井方的社会文化活动,构建了明确的、丰富的地域共同体。本文以河北涉县曲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描述和分析邻里(街坊)结构与功能,呈现这一社会学基础概念在中国地方的实践样态,以补足社会学学界长期以来对邻里研究的相对不足。
本文主要以实地调查为主,结合地方志文献,进行邻里主题的研究。在进入实地调查点之前,我们对太行山地区、大别山地区以及贵州丹寨等山区的用水情况进行了长期关注。2019年4月,我们以涉县辖区内一个村庄的用水实践为研究对象开展实地调查。2020年12月,再次就本文涉及的井方议题进行专题调查。我们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同时结合当地石刻碑文、地方史志等文献资料,在历史情景中把握研究主题。
河北涉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571.7毫米,降水季节明显,年际变化大,旱涝灾害频发。同时,由于山区石灰岩广布,多裂隙、溶洞,致使地表水易下渗流失。地下水埋藏较深,难以开采,总体呈现缺水状态。曲村位于涉县东南部,清漳河沿岸,水源条件相对县域内其他村庄较好,是一个由自然村落构成的行政村。目前全村约5500人,分成36个村民小组。本文将以涉县曲村为例,展开讨论。
公共之井
涉县农村地区历史上主要以水井、水窖等设施获得饮用水。据不完全统计,涉县514个自然村中,仅有24个村庄依靠出露的泉水为饮用水,64个村庄分布在清漳河、浊漳河、漳河沿岸,以河水为主要生活用水水源。除此之外,215个村庄靠水窖、水池等旱井解决常年饮水问题,211个村庄从水井中汲水供人畜饮用。即依赖水井获取生活用水的村庄约占全县村庄总数的41%,依赖旱井的约占42%。从纵向上看,水井作为当地重要的汲水设施,也反映在境内“古井”数量上。据1993年《涉县水利志》载:境内百余个村庄有深浅不同的“古井”,浅的20米,深的50多米,井数达200多眼。目前至少有64个村庄以井、泉、池等命名,可见水井在当地社会的重要性。
人们对水井的重视,也可从水井的精美外观上看出。与邯郸东部平原地区汲水井不同,涉县山区水井一般修建得较为精美。水井周围10~20平方米的地面,多以条石铺就平整的井台。除了井及汲水水架外,一般有2~3个岩石凿就的石盆,用以洗菜、洗衣。井台附近还为龙王、井神等神灵安置神位。另外,有些水井附近至今还立有当年的修井碑,记录着该井修建或重修的历史。总之,平整的地面、共用的汲水设施、石盆、神位等是当地水井的“标准配置”。
修建如此精美和完善的用水设施,并非一家一户所能完成,它往往由多个家户联合共同修建。“家户共建”,是当地修建水井的重要方式,且作为传统惯习,在水井的历次重修中得到延续。当地村民记忆中最晚近的一次“家户共建”,是西巷方水井1964年的重修。
以前那是土井,不安全,容易塌,1964年重新修过一次。那时候的人自觉,一说要修井,都主动出钱。一般是那一井方的人出钱,外边的(其他井方)也有去帮忙的。修井比较麻烦,那次花了1个月呢,花的钱也多。都是他们井方自己管。他们会推选出几个明白人,收了多少,花了多少,最后都要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现在还有当时修井的账。你看,1964年西巷方58户,220口人,十几头牲畜。摊了300多元,用了450多个工。(20190504,吴先生访谈)
水井修建和重修中的家户联合、集资共建,这一特征也出现在当地历史碑文记载中。水井碑文记载,维首、善人发起重修水井的倡议,共井之人集资出工共建。如曲村现嵌于曲村火神堂墙壁的《重修井碑记》记载:
即此东井者,不知穿自何时,屡经修砌不得艰固根基,于清乾隆壬申岁有维首岳文斗、姚得富等见其颓坏深有垒卵之忧,出而捐资重砌……本方善人按人捐囗粮食以及人工,多寡不一,难以花开,神灵明鉴,永不朽矣。
“方”为井方,是指一眼井所辐射的地理空间,通俗地讲,即使用同一眼井的“那片地方”。“方人”即井方之内的所有成员,是为共享水井之人。在长期汲水实践中,人们有着固定的汲水井,归属着明确的“方”,是确定的某方成员,有着共同建设该方水井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井方是以水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地域单元。井方成员共享水井,也有共建之义务。在水井建设中强调“共建”,而非“平摊”,故出现“按人捐”,但又“多寡不一”的现象。
共建而非平摊,也发生在水井的日常维护中。日常维护,主要是水井清理工作。风吹落的尘土和人们汲水时不小心掉落的异物,使得水井需2~3年清理一次。不同于重建,水井清理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如果异物较多,清理工作可能持续2~3天;异物较少时,半天即可完成。与水井重建时相同的是,“方人”需共同负担日常维护工作。
下雨靡进去的啊什么的,要两三年清理一次,不然水会很浑。清理也是那一井方的人清理。把水掏干。找一个身材瘦小的人,蹬着石头下去。一个人在上面续桶下去。下面那个人把脏东西舀桶里,上面的人拔上来。洗个两三遍,就可以了。清理不需要那么多人,五六个人就行。一人替一会儿轮换着来。说是井方的人一起,其实也用不了几个人,也不怎么花钱。找个负责的人,组织一下,大家适当出点钱,两块、三块的,意思一下。家里实在困难的,不给钱也可以。这些钱就用来井上修个什么东西,买个什么东西的。出工都是义务的,都是井方的人,不给钱。(20201231,秦先生访谈)
从实践上看,虽井方内家户共同负担水井的建设和维护,但并非绝对平均。换言之,不平均才是人们共同参与水井事务的常态。人们并不强调平均,“按人捐”,指出坊内成员都有捐资出工义务的同时,并没有具体规定每人应捐多少。经济富裕的家户多出,经济条件差的家户可以少出,甚至不出。
共建时出资出工“不平均”,但人们汲水权却是相等的。每个家户都有从水井中汲取家户所需基本水量的权利。甚至那些平时不使用该井的家户,也可偶尔来该井汲水。汲水没有明确的书面规则,但有不成文的“规矩”。如一次最多汲取一担,汲水次序遵循“先来后到”,等等。“规矩”是有场景的,根据具体情境而变化。当某家庭遇有突发或重大事情,如婚丧嫁娶时,人们不仅主动让其先汲水,甚至帮其汲水,汲水量也不受限制。但如果主家不自觉,不知谦让,影响到其他家庭用水时,也会有人说“废话”(批评或骂人的话),私下议论其不懂规矩。总的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用水规则,但根据场景而定的用水“规矩”,使人们拥有基本相等的汲水权,并保证每个家庭在大量需水的情景下,都能得到“照顾”。
事实上,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井方成员“集资共建”的范围已不局限在水井事务。最初以水为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地域单元,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生活单元。人们不仅共用水井,也共用道路、庙宇等。水井事务中的“集资共建”,也延伸至井方内道路、庙宇等公共设施的共建。如现嵌于奶奶庙墙壁、立于1922年的《曲村修东街路序》碑记中载:
……此路迟之又久急缓而不修哉,推原固非不欲修,但经费无以筹也。王成春会,圣堂收掌与茶社收掌计算两社积蓄有钱九十余串。本方人等亦愿量力捐输,帮主效力。于是匠师任其要,方人助其余,勇跃争先不越月而功告竣……
当然,“集资”但非“平摊”,也是开展坊内其他公共事务的原则。在石刻碑文中展示的捐资各不相同,即是对这一原则的表达。从经济理性来看,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会选择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与他人相等的收入,即在“非平摊”中“搭便车”。如果确实如此,可以想象共同行动不会持续。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人们不仅在水井事务中合作,且在修路、修庙等其他公共事务中也采取合作行为。这恰恰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般性运行特征的体现。
在曲村,水井的公共性体现在人人有责与户户有权。人人有责主要是指每个井方内的人,都要承担对水井建造与维护的职责;户户有权是指本井方内的每家每户都享有用水的权利。它实际上也体现了井方之内居民建井与用水的公平原则。像中国社会较为普遍遵循的原则一样,曲村水井的公共性并不是简单的平均,而是综合的均衡。它是原则的公平性与规则的灵活性(不平均性)的有机统一。就是说,在原则上,水井的建设与维护是每个人的责权,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则奉行能者多捐、愿者多劳,以及需者多用、急者优先的做法。原则是清楚的,但操作规则不但有限而且需要在情景中具体地、灵活地应用,比如某户需要多用水或着急用水。这并没有像现代社会的某些法规那样具体明晰,但置于村落一定的社会情景条件下,村民很容易给出合适的判断。
因井成坊
曲村村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10个井方。当地百姓把由共用水井形成的地域单元称为井方或方。如前所述,这个方是邻里或街坊的意思,所以我们不妨假借街坊之坊,称之为坊。
曲村十井十坊是逐步形成的,发展至明末基本定型。曲村靠近清漳河,常受河水侵扰,所以家户最初聚集在地势最高的“高堰方”。随着人口的增长,庙下方、麻地方、西道方等逐步形成。十坊的形成过程,也是地势稍低的地方逐渐开发的过程。十坊,将曲村划割成相对独立的十个单元。坊的大小不一,主要受水井辐射的地域范围影响。用水户多,坊便大;用水户少,坊便小。而影响用水户多少的主要因素是汲水距离。事实上,越早形成的坊,人口越多。后来修建的井,受土地局限,所形成的坊,面积一般较小。每个个体和家庭都离不开水源,都需要从水井中汲水,所有成员都有所归属的坊。当然,水井的使用并不完全固定,当某坊中的水井干涸或重修时,人们也可以从其他坊的水井汲水。曲村十坊如图1所示。
一个坊,通常由一条街、几个小巷或胡同组成。坊多以井、巷为边界。一条小巷或一个胡同的多个家户,基本同属一个坊。但一条大街,左右两边,或前后两段,可能会分属两个不同的坊。水井通常坐落于坊的靠近中间的位置。图1中圆圈所示的便是水井所在的位置。以高堰方和仁义方举例,高堰方占地长约600米,宽约520米,家户约320户。它以一条主街为核心,几条小巷与主街左右相连。主街及两边小巷的家户从高堰井中汲水,都属高堰方成员。小巷也可与其他街道相连,坊并不封闭。而规模较小的仁义方,仅为一条单向开放的胡同,长约200米,宽约100米,约有住户85户。
从坊内家户来看,分布较为密集,甚至四五户聚居在一个院落。“户”,在当地指独立开设锅灶的小家庭。成年子女成婚后,从父辈那里分得一间房,有独立的锅灶,便与父母分属不同的户。故一个院落中可以有多个家户。这些家户一般情况下是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当然,也存在房屋买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支系,甚至不同姓氏的人便会聚居在一个院落。事实上,即使一个院落是一个“大家庭”,整个坊也是不同姓氏的集聚。特别是大坊,多由不同姓氏的家户组成。可见,坊是由用水关系构成的地缘组织,它与中国东南地区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宗族有较大的差异。
作为有组织的社群,坊意味着共用水井的家户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集合,更是有着情感联系和一致行动的共同体。
因汲水和水井事务形成的坊,成员间的共同生活,不仅是水井事务中的暂时性横向联合,而且是世代相承的。子承父,汲取着同一眼水井,也延续着同样的水井事务。家户的横向联合和纵向延续,使“坊”不仅是“面对面的社群”,更是在世代间延续的绵续性社群。这种绵续性,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今社会,甚至跨越了空间限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人口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人们开始被动或主动地从坊内迁出。迁出的人口,在新居地开掘了新的水井,但并没有形成新的坊。他们仍以原来的井方为归属坊,参与原井方的各项社会活动。
离井不离坊,这意味着水井事务只是连接坊内成员最初的关系纽带。坊内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有着更深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坊内成员的社会交往,包括日常互助和家庭重大事件中的社会支持。
日常互助,以平常的互帮互助、生产生活工具共享为主。生活在坊内的成员,因住房紧邻,彼此熟知,交往频繁且持久。在平常的生活里,互通有无,互帮互助,以行动践行着“远亲不如近邻”的生存理性。
若邻居家人手少,则人畜相助,遇天阴下雨,邻居不知或无人,即主动呼唤或帮忙收起所晒之物……出门孩子常托于邻居照料。邻里之间碾、磨、工具、牲畜等,凡闲即可使用,常谓“谁家也没置全的物,谁家都有求人的事”。
家庭重大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主要表现为坊内家户,在婚葬等大事中的互助。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婚葬对单个家庭来说,耗费极大。婚葬不仅要遵循繁复的仪式,也要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很多时候,一场婚礼或葬礼会使家户致贫。在婚葬中,邻里的帮扶,是普遍的需要。任何家庭都不得不相互依赖,即使那些富裕家户,也需要邻里帮其完成特定的事务。
一场体面的葬礼,是主家家庭实力的展示。而一场糟糕的葬礼,则会使整个坊被人们评头论足。
现在主要是葬礼体现井方的作用。如果井方内有老人去世,当天,井方里的男人就要主动去帮忙。听主丧人安排,帮忙干些杂活,比如把锅灶垒起来,烧水做饭。邻里在葬礼中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五服以内的都要陪灵,不能干这些杂活的。这时候就指望邻里了,就是一井方的人。主丧人,从里面挑选合适的人,去打墓。还要安排人在葬礼当天接待主家的亲戚。一个井方的算是半个自家人,亲戚是客。葬礼上主家不能离开灵棚,只能委托井方的人接待。现在主要是帮忙干些活了。以前穷,都是井方里一家一家啊捐点,把老人埋葬了。现在本身主家也不缺钱,不在乎钱了,就只是干活。(20210101,秦先生访谈)
坊内的社会交往,特别是内部互助,将坊建构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在农业生产力落后且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内部支持、守望相助是人们解决生活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运转的关键。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寻求帮助的需求。你困难时我帮你,就默认着我有困难时你要帮我。只接受帮助,而不提供帮助的人,会被排除在互助的范围之外。因此,守望相助,是在熟人社会习俗型信任基础上,成为内生的生存理性和约定俗成的“规矩”。而在曲村,以距井远近,成独立片区的坊,正是邻里守望相助发生的主要单元。
除互助外,坊也是基本的监督场域。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坊成为有着显性监督作用的场域。坊对个体的监督,不仅体现在集体活动中,也发生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受当地狭小的生活空间所限,人们将更多的家庭生活推至坊的公共空间,如将洗刷活动推至井台,饮食在饭市。这种将某些家庭或个体活动置于公共空间的行为,无形中也将个体行为暴露于公众的监督视野下。个体在坊的公共空间暴露的行为越多,越处于“全景敞视”式监控之中。
井方内没有严厉的惩罚机制,对于越轨行为,坊只能通过舆论压力,对居民起着规训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坊内的人们彼此熟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重视“人情”和“面子”,他们多会遵守熟人社会的规范。一旦出现失误时,就会因受到人们的议论而丢面子。在生产力落后的小农社会,个体生存离不开群体。被排除在群体之外,意味着失去了群体的支持和帮助。这无形中增加了个体的生存成本。从生存理性的角度看,坊的舆论监督作用,使坊内成员的一致行动成为可能,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坊不仅是一个世俗的地域社会生活单元,而且还是一个祭祀单元和信仰组织单元。
由井成坊,每眼井都有一个井神,每个坊也便是一个独立的井神祭祀单元。水资源短缺,且受掘井技术的局限,人们将获得稳定水源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于是,井神信仰成为重要的信仰。人们在与井台紧密相连的墙壁上,凿出约50厘米宽、80厘米高、10厘米深的长方形石柜,再以砖砌成拱形神龛。内侧墙壁贴以“龙王神位”或“井神神位”的字样,便形成了井神神龛。若没有与井台相连的房屋墙壁,人们也会用石头垒砌一个类似的神龛供奉井神,并在二月二“龙抬头”及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为井神烧香上供。一个井方一眼井,一眼井供奉一位井神,每个井方都是供奉井神的独立单位。
有水的地方就有神,管水的神,保风调雨顺。像水窖、水池等旱井边上,也要供神,不过简易点,只有一个香炉。井旁边,都要有供井神的地方。一有井就有井神了,刚开始也很简易,后来条件好了,就用石头给井神搭了个石房子。据说,以前村子里没这么多庙。最开始只有一个龙天土地庙,后来人口多了,才开始将庙里的神仙请出来。请到哪里?就请到给井神盖的各个石房子里。这才有了村里这么多的庙。其他神仙进来了以后,井神就又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在井边又给井神辟了专门个地儿。(20191203,刘先生访谈)
井神供奉和村里各个庙宇的关系,是否确如传说那样,无从考证。但在曲村,井附近50米的范围内,多能找到庙宇。有的庙直接紧邻水井,如麻地方水井井台紧邻奶奶庙,庙下方水井与龙王庙毗邻。
与井神供奉相似,一个坊,至少会有一座庙宇或神堂。这些庙各不相同,共同组成了村里“九庙十八堂”的村庙结构。当坊的规模较大时,坊内的庙宇也会较大,有时不止一座。当坊的规模较小时,可能只有一间供奉神灵的神堂。
庙的相关活动也主要以坊为单元,大多数情况下,坊内居民是庙的直接管理者和忠实信仰者。直接管理者是指庙所在坊的居民,最为关心该庙的重修事宜。人们与坊内的庙接触最多,也熟知庙宇的损坏情况,故重修庙宇的发起者一般是庙宇所在坊的成员。忠实信仰者是指庙所在坊的居民最为热心为该庙宇举办庙会等祭神活动。坊内成员对本坊庙宇祭神活动的热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体现得最为明显。2020年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村庄取消了所有庙会。但在庙会的当天,庙宇所在坊的人们仍主动到庙里烧香、上供、捐钱。不能请戏班子“谢戏”,他们改用喇叭播放唱片“谢戏”。不能聚集,他们烧香上供后,只留本坊二三十人作代表参加聚餐。特殊时期的管控措施,虽然影响到了庙会的正常开展,但却也在村庄内部做出了划分。庙宇所在坊的成员,成为该庙举办庙会最积极的分子。
除庙会活动外,在村庄举办的元宵社火活动中,每个井方都要为社火准备娱神节目。在元宵节前,各坊已各自进行节目的准备工作。在社火仪式上,他们要以坊的名义,在村庄几条大街上表演跑旱船、配合武场面的“二鬼扳跌”、吹乐等多种节目。事实上,娱神节目不仅是献祭神灵,也是人们在漫长冬季最重要的娱乐活动。
神祇及庙宇是由人来建构的,同时满足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推动基层社会的有序运行。早在19世纪,费尔巴哈就指出,上帝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本质的理想化存在形式。建构庙宇、神祇,以及围绕庙宇、神祇所开展的活动,是井方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促进地方社会的整合。与此同时,人们借助全民性的宗教活动,为讨论世俗的公共事务提供社会论域与合理正当的理由。如元宵节的灯棚,汇集了坊内绝大多数男性成员——“当家人”,成了商定坊内公共事务的重要场合。重修、清理水井,重修庙宇、道路等决定,多半在灯棚中商定。
总之,在曲村因共用水井而结成的地域社会共同体,成为呈现社会学之邻里、街坊概念的经典样本。曲村井方之内的人群,从共建共享,到互帮互助;从守望相助,到相互监督、相互约束、内部规训,维护社会秩序;从共构井神、庙宇,祭神、娱神,到回归世俗社会的公共事务建设,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地域群体的社会性特征。
余 论
水与社会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行龙和他的团队研究了水利灌溉与区域社会的关系。他们以晋水流域为研究重心,探讨水利灌溉及水案纠纷,与流域社会生产、生活、文化之间的关系。后续水利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还发展出泉域社会、库域社会、围垸社会等概念。
曲村的故事,在微观层面上呈现了水与生活共同体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呈现了由井及坊,再由井方构成村落社会的基本格局。受自然条件及传统经济实力的约束,曲村人无法像南方或华北平原地区那样便利地利用水资源,这迫使他们动用集体力量来利用和分享有限的水资源。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井方这一建井与用水共同体。由于长期毗邻而居、相互熟悉,并且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形成一个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生活共同体。与此同时,在生活实践中,井方之内还发展了坊人公共评价与相互监督的社会机制。在世俗之上,还发育了井方之内共同的井神等民间信仰体系,进一步整合和凝聚了井方社会。毫无疑问,井方成为一个权责明确、地理边界清晰的地缘社群单元,为社会学人理解街坊、邻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认知样本。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自然村落是社会学经典意义上的社区。从村庄形态来看,南北方的实际差异比较大。大致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村落一般较小,在人民公社时期,通常由一个自然村落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大队通常由十余个自然村落组成;人民公社解体后,虽然叫法不同,但村委会、村民小组的结构、规模传承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生产队。但中国各地区间差异较大,对农村社区分析时,需要在类型学上做区分。不同于南方的自然村落,华北地区自然形成的村庄规模一般较大,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村落构成一个生产大队,公社解体后即为一个行政村。以1983—1984年河北省邯郸地区为例,邯郸14个县共有行政村(大队)4916个,自然村5034个,平均每个行政村(大队)的规模是1.024个自然村,行政村与自然村高度同构。
贺雪峰认为自然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而行政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一判断在他调研的长江中游地区是成立的。但华北的自然村与行政村大致同构,村民虽然毗邻而居,却因为人数较多,自然村落整体呈现半熟人社会状态。当自然村规模较小时,成员之间彼此熟识,分享着不言自明的规矩,是传统的自治单元。这种自然村落,在现今行政管理体系下,仍然是重要的社群自治单元。但当自然村落规模较大,少则两三千人、多则四五千人,甚至更多时,村内居民很难做到彼此非常熟悉。因此,即使为同一自然村的成员,彼此之间也只是“脸熟”,而并不知根知底。这些较大规模的自然村,内部还有更小的社群自治单元。只是社群自治发生在家族、邻里等村落内部,没有形成特别清晰的地域界限,故容易被忽略。家族、宗族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家族、宗族组织往往忽视地域及其边界。曲村内井方的存在,则提供了村落内部以地缘为纽带且有清晰边界的自治社群的典型样板。
社区治理已经成为社会学界以及政府部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管理部门,社区治理的研究和实践都依然困难重重。其中的困境在于地方政府、社区或村委会有积极性而居民缺乏动力。当然,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案例研究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组建一个多大的地域单元,以及如何在此地缘单元内找到公共抓手,以实现公共事务的自主与自为,是实现社区治理的社会基础。大致而言,可以利用有限的地域空间,以地域单元的公共事务为核心,培育街坊(邻里)内成员对本地域单元内公共事务的关切,给予他们处置本街坊(邻里)内公共事务的权利,同时调动他们的责任心,充分发挥与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夯实街坊(邻里)的社会治理基础,社区治理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①依照学术惯例,对所涉及的地名进行了技术处理。
②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80—81页。
③④雷家宏:《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13页。
⑤⑥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5、96页。
⑦《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⑧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67—168页;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165页;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
⑨J. Scott, G. Marshall, (eds.),OxfordDictionaryof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08.
⑩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