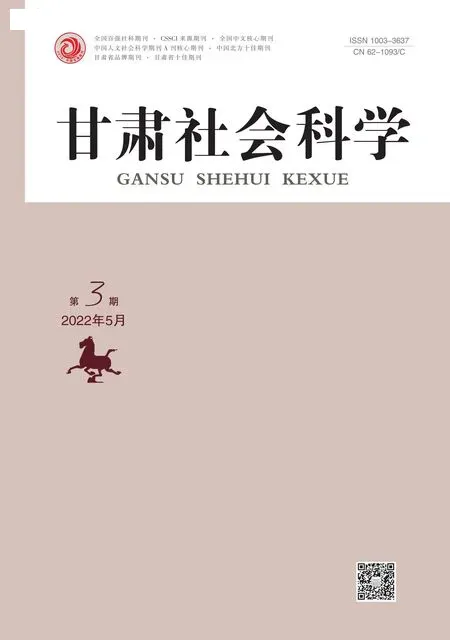当代疫灾的伦理生态学思考
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成都 610066)
人类从动物走向人的历史,也是一部灾变史。人类承受灾变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是环境灾害,它以破坏人的生活条件为基本表征;二是疫灾,它以伤害人的生命为主要特征。比较而言,疫灾对人类的伤害更大,因为“‘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1]。所以,疫灾构成“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2]175,既不断地改变人类伦理生态,也受不断变化的伦理生态的影响。由此两个方面,疫灾成为检讨伦理生态学的独特视角。同时,伦理生态学也成为审察当代疫灾的宏观方法。
一、疫灾与伦理生态
(一)疫灾的古今变势
疫灾,是指由流行性传染疾病(瘟疫)造成的灾害,它成为损害人类健康和剥夺人类生命的暴虐方式。从致疫因子和孕疫环境观,疫灾呈自然性质取向和人力性质取向两种类型,前者的致疫因子是自然因素,孕疫环境是地域自然。具体地讲,人类不适应自然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节奏而产生的流行性传染疾病,多发生在人类早年。人类早年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生存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疫灾是以异常气候为致疫因子,以地域自然为孕疫环境。因为在自然生存时代,人类只能顺应地球环境、顺应气候、顺应地域自然而存在,环境、气候、自然的任何变化都直接影响人类的存在,特别是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类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生命存在状况,当异常的气候推动自然界发生巨变,必然导致地域性生存的人类严重不适应,疫灾就此发生。
从根本讲,严酷的生存环境构成人类进化的动力,人类进化向前,逐渐改变纯粹的自然生存状况,即从完全顺应自然的桎梏中摆脱出来,转向改变存在环境、征服地域自然,人类的这一努力在农牧社会中后期得到更为明显的呈现。尔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的努力构成人类生存的主题,并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推动人类开辟近代历史,进入工业社会,这一发展进程从不同方面张扬“人定胜天”的力量,环境被人类驯服,自然也任由人类利用,消隐森林,锐减草原,沙漠化土地,截流断流江河修建水电大坝,移山填海和移山填湖,海洋富氧化,加之无限制的开发地下资源,掏空大地等等,地面性质,甚至地质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人力改变地面性质和地质结构的过程,就是改变地球生物活动和地球生物状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种大量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地球生境大面积破碎,地球生态链条破损进而断裂,地球承载力超出自身限度,大地自净化能力丧失,导致大气环流改变方向和节奏、臭氧层稀薄和太阳辐射加强等。如上所有因素整合发力推动气候丧失周期性变换运动的规律。气候失律,构成人类终结自然的标志,“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3],更改变了人类存在的边界。这种改变呈正反两个方面:其正面成就,是创造出现代文明,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及其高水准的物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其反面成就,是环境灾害和疫灾绵绵不绝的爆发。前者主要是气候灾害和地质灾害,它们不断对人类存在安全和生活保障带来摧毁性打击,对人类生存家园的破坏呈全方位性,比如台风所到之处无物能够幸免,酷热或高寒所到之处亦无可抵挡。雾霾一旦登陆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域国家,就会迫使该城市或该地域国家改变一切。环境灾害虽然暴虐,但毕竟是外部性的,被破坏和被摧毁的所有方面,均可重建,“在灾难中重建家园”,主要指环境灾害,却不适应于疫灾。因为以人力为致疫因子、以社会发展为孕疫环境的当代疫灾,既是内部性的,更是直接指向人类身体和生命,其表现出来的暴虐,是关于生还是死的惨烈。
疫灾因为致疫因子和孕疫环境的不同,形成古代疫灾和当代疫灾的区分:古代疫灾呈自然主义取向,因为其致疫因子主要是巨变的气候,孕疫环境是地域自然,所以古代疫灾体现地域性、局部性、偶发性和孤立性,疫灾与疫灾之间呈非关联性和非生成性。与此不同,当代疫灾的致疫因子是人力,孕疫环境是人力推动的社会发展,所以当代疫灾往往呈必发性、连续性、生成性、传播的跨地域性和全球化。比如2009年原发于美国的H1N1,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其后H1N9、H7N9等流行性疫病不断涌现。不仅如此,疫灾与疫灾之间呈关联的生成性和灵动的变异性,比如埃博拉病毒,它于1976年、1977年、1994年、1995年、1996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7年、2014年、2016年在非洲持续爆发,反复蹂躏人类;再比如SARS-COV-2病毒与SARS病毒之间构成变种关系,它之比SARS具有更强劲的传播能力而肆虐世界每个国家,恰恰在于SARS-COV-2病毒具有更强、灵动、快速的迭代变异能力。
(二)疫灾的伦理生态取向

古代疫灾呈现的自然伦理生态,其内在动力是生,基本朝向也是生。但对人类论,顺应自然伦理生态是生,反之,违逆自然伦理生态却是死;并且,相对个体言,其死,是死的永恒;相对种群或物种言,其死,却是死而复生或死而再生。与此不同,推动当代疫灾扩张性爆发的人力伦理生态,它的内动力虽然也是生,但却是人力之生。自然之生,指向自身而兼顾它者,不存在与他者合或不合的问题,而是存在于其中的其他有机体、存在物能否顺应的问题,顺应者则生,不能顺应者则死;反之,人力之生却指向他者(环境、自然)而目的于自己,它客观地存在与他者(自然、环境、地球生命)合与不合的问题:合者,人可生且生生不息;不能合者,则沦为死境而必死。所以,人力伦理生态的实际朝向,取决于人力本身与自然的生生运动合不合,人与自然合,其伦理生态呈生境取向;人与自然不合,其伦理生态呈死境取向,它的形态学敞开就是层出不穷的环境灾害和疫灾。
(三)伦理生态的生生内涵
要理解伦理生态,还需从“伦理”和“生态”概念入手。


二、生境与死境:伦理生态的两可朝向
讨论伦理生态问题,需要避免与“生态伦理”混淆。要言之,生态伦理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对象。生态伦理学原发于生态学,它是研究地球生命与其存在环境之间变动关系的科学,当人这个有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变动关系发生逆转时,就产生生态伦理问题,引发生态伦理学的诞生:生态伦理是人类行为如何符合自然环境之生的伦理,生态伦理学是研究调节人类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之重新恢复其生境的学问。与此不同,伦理生态指涉的对象是伦理的生存位态与人的生存之间的动态生态关系,这一动态生变关系既涉及伦理的生存位态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同时也涉及人的行为如何影响伦理的生存位态,对这一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的系统探讨就形成伦理生态学。
(一)伦理生存位态影响人类行为的方式
从历史与现实观,伦理的生存位态呈两可取向,即生生(或曰“生境”)取向和死亡(或曰“死境”)取向。生境取向的生存位态,是伦理的本原位态;反之,死境取向的生存位态,是伦理的继生位态,它是本原性的伦理生存位态遭受消解而呈现出来的逆向变异位态。
如前所述,伦理是人与他者发生关联时才产生的,所以伦理始终表征为实际的人际关系。所谓“人际关系”,指人与他者(包括他人、他事、他种生命、他种环境以及自然等)的关系,如此内涵丰富范围广阔的人际关系,存在伦理与非伦理的区分,体现伦理性质的人际关系,是以具体的利害为实质规定,并以对具体的利害权衡和取舍为基本诉求(见图1)。

图1 以利害取向为本质规定的伦理关系类型
伦理面对的是具体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得失,是对其利害得失的权衡与取舍。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组织,面对具体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取向而权衡和取舍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是只考虑自己的利害而不
考虑与此行为相关的他者的利害,这种利己损他的利害权衡和取舍方式,是反伦理的方式,因为它总是会造成利己损他的结果。二是既考虑自己的利害同时也考虑与此行为相关的他者的利害,这种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利他的利害权衡和取舍方式,是伦理的道德方式,因为它总是会形成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利他的结果。三是只考虑与此行为相关的他者的利害而不考虑自己的利害,这种损己利他的利害权衡和取舍方式,是伦理的美德方式,因为它总是会结出损己利他的结果。
综上,人际关系敞开两种类型:一类是非伦理的人际关系;一类是伦理的人际关系。伦理的人际关系呈三种形式:以利己损他的方式权衡和取舍利害的人际关系,是反伦理的人际关系;以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利他的方式权衡和取舍利害的人际关系,是道德人际关系;以损己利他的方式权衡和取舍利害的人际关系,是美德人际关系。伦理生存位态的两可取向均是在如上类型的伦理人际关系基础上展开。
仅静态观,呈生境取向的伦理生存位态有两种类型四种形式:首先是道德,它是伦理生存呈生境取向的基本位态,敞开两种具体形态,一是利己不损他,这是道德生存的底线性生境位态;二是利己亦利他,这是道德生存的日常方式,也是伦理生存的大众化生境位态。其次是美德,它是伦理生存呈生境取向的高级位态,也敞开两种具体形态:一是以主动尽义务的方式放弃将得的合法利益的无私奉献,是美德生存的基本生境位态;二是以主动尽义务的方式渡让已得的合法利益的自我牺牲,是美德生存的高级生境位态;而自我牺牲生命的极端形式,却构成美德生存的最高生境位态。
(二)人类行为影响伦理生存位态的两可取向
伦理生存位态不仅呈静态类型,同时也呈动态取向。从动态观,伦理生存位态敞开两个特征:一是开放性;二是生成性和变动性。就前者言,伦理生存位态敞开七个维度,即人与人、人与群、人与社会和人与事-物、人与地球生命万物、人与存在环境、人与自然宇宙。仅后者论,伦理生存位态始终因为人的“因生而活,为活而生、且生生不息”的利欲谋求而处于生成、变动的进程之中,由此带动人与人、人与群、人与社会、人与事-物、人与地球生命万物、人与存在环境、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也处于生成、变动的进程之中,并且这种生成、变动既可呈生境取向,也可呈死境取向。
综上,伦理生存位态到底呈生境取向还是呈死境取向,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的激发。具体而言,取决于人;整体论之,取决于制度规训和政府导向下的社会。但这都是从主体动力学论,主体动力并不是造成伦理生存位态两可取向的根本因素,其根本因素是伦理生存位态的自身限度,唯有当主体动力与伦理生存位态的自身限度发生直接关联时,伦理生存位态才呈现出生境或死境取向。具体地讲,无论个体还是社会,当其主体动力释放出来的功能没有超出伦理生存位态本身的限度,它就呈生境取向;反之,其主体动力释放出来的功能超出伦理生存位态本身的限度,并且这种逾度的主体行为持续展开为一种强化进程时,伦理生存位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而呈死境取向。
以个体和社会为整合方式的主体动力,推动伦理生存位态向死境方向逆转是全方位的,可将这种全方位的逆转大致归纳为两个维度,一是社会维度,二是自然维度。伦理生存位态从生境向死境方向逆转,就会形成伦理虚无主义盛行,比如“老人跌倒无人扶”和“扶跌倒老人反被讹”,就是其典型呈现:“老人跌倒无人扶”,铺开了美德消隐的伦理生存位态;“扶跌倒老人反被讹”,铺开了道德解构的伦理生存位态。伦理生存位态从生境向死境方向逆转的自然呈现,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没有限度和边界,这种无限度和边界的征服、改造、掠夺持续展开并强化拓展到自然世界的每个角落,甚至从地面到地下、从海洋到太空,所造成的无所不在的结果有二:一是环境死境化,自然死亡,其突出体现是气候极端失律,环境灾害日常生活化和全球化;二是生物世界遭受严重破坏,并振动了沉睡的微生物世界,源发于生物世界和微生物世界的疫灾突破偶然、局部、地域的限制而持续化、世界化、变异加速度化和疫灾苦难日常生活化。
三、防治疫灾的伦理生态学思路
从人类发展史观,当人力上升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并能够现实自己的意愿这种水平时,人力必然四面出击,造成强权社会。概括其要,人力铸造的强权所指不外乎社会和自然两个维度。仅后者言,人类强权指向自然,形成人力对自然的蹂躏和奴役,征服、改造、掠夺成为基本取向,所造成的伦理结果是:以生生本性为原发机制的自然伦理被人为地取消,人类为了“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决然地否定自然,因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7]。自然必然被人力奴役,大地被人类掏空,环境沦为千疮百孔的死境。人力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掠夺,最终改变了环境生态、地球生物生态、自然生态,使环境、地球、自然逆转为死境运动。环境、地球、自然一旦朝死境方向运动,又反过来改变人类存在,但首先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伦理生存位态。疫灾是最典型的例子:先是物质主义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后利欲突破人际伦理的限度,然后强权在人类社会内部无限度释放,造成生生取向的伦理生存位态逆向运动,最后突破人类社会的边界指向环境、地球生命和自然,展开无节制、无止境的征服、改造、掠夺,最终导致环境、地球生命、自然的逆生态反抗,这种反抗致人类于死境的最佳方式不是环境灾害,而是疫灾,因为环境灾害攻击的是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疫灾攻击的是人的身体、人的生命本身。疫灾频发的日常生活化和世界化,导致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生境功能整体性失灵。大流行于当世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其最好的诠释: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人类全部关进疫灾“笼子”里动弹不得,世界的原有秩序坍塌,人类已有的系统(政治、经济、伦理)规则出现失灵,一切都围绕不断变异的病毒展开,并被加速变异的毒株弄得忙碌不已。曾经以文化、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为自豪的人类,在世界大流行的疫灾面前苍白无力。康德关于人类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人立法”的人类主体观念遭遇挑战,加速变异和此起彼伏的各类病毒却成为为人类立法的角色,比如每个变种的毒株都将人类搞得手忙脚乱是最具体的说明。仅就伦理言,尤其在西方世界,大流行的疫灾正摧毁一切,比如个人自由主义丧失立锥之地,民主和人道人灵,理性和公正也失去用武之地,不同形态的管制似成常态,暴乱、抢劫等人性之恶暴露无遗,公义和道义被利己和自私取代,极端孤立主义、偏激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种族主义等死灰复燃。
当代疫灾解构着人类伦理,使传统的人类伦理生存位态呈死境朝向,与此同时,曾经被人类强行取消的以生生为基本诉求的自然伦理获得重新发挥引导和规训人类伦理的功能,人类伦理由此必然走向对生境位态的重建。
(一)重建疫灾认知
其一,在当代进程中,要重建人类伦理生境位态,需要正视当代疫灾,全方位反思造成当代疫灾频发及其世界大流行的人类作为,清算对待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极端存在姿态、生存方式和行动模式,重建疫灾认知。
“完全可以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疾病。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到由来已久的生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到达自然极限时,于是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摧残。故而,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稳定的慢性病关系。”[2]15
疫灾不可避免,彻底消灭疫灾不可能,因为自然是自在的存在,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只能适应自然的自在运动,但人类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完全地适应自然,疫灾就是人类不能完全适应自然的自然反映。虽然如此,但人类可以将疫灾减少到最低程度,即使疫灾不可避免爆发了,也可以使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在自然生存时代,更多可以避免的疫难之所以没有避免,是因为人类顺应自然的能力太差,或者有其能力但选择顺应自然的方式、方法不对。从古代走向近代而至于当代,更多的疫灾不是由人类顺应自然无力或无方造成,而是由人类无限度地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造成,当人类以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为能事时,人类自身已经沦为一种疾病,这就是无限度无节制地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自然资源方面的疾病。在疫灾世界化大流行的今天,人类不得不接受疫灾的规训,重新认知疫灾与人类行为的关系,自我医治其征服病、改造病和掠夺病,这是前提。人类能够自我医治此三病,当代疫灾可预防和治理,反之,人类将可能被瘟疫所吞噬。
其二,降解世界大流行的疫灾,不仅需要节制,更需要重建存在姿态、生存方式和生产-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人是有限的个体,这源于世界的有限性,正是这种有限性构成人类社会的限度。改变无限度姿态,包括世界无限论、资源无限论、物质幸福无限论等错误的存在观念,重建限度生存的姿态和信念,有限度的生产和消费,将生产和消费限制在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自生境范围内,促使地球、环境、自然保持自调节、自修复的生境状态,成为减少疫灾、降低疫灾肆虐人间的根本智慧和方法,因为“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1)人类舍渔猎而就农业生产;(2)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2]ⅶ。人类节制自己的存在想望、科技开发能力和物质生活无限富裕的诉求,是恢复人类与微寄生平衡的根本方式;而恢复人类与微寄生平衡,是阻止、降解、减少当代疫灾的绝对前提。
其三,应对频发甚至循环传播的当代疫灾,不仅应从可预知的、能确定性的方面努力,更要主动探索其不可预知的、非确定性方面,通过全方位的探索要在这些方面做好最坏的应对策略和更多维度的准备。并且,应将如上准备和应对纳入人类环境保卫战这一整体中来考量:预防和治理当代疫灾成为人类环保的有机内容,而“环保的核心是对未来的防御,但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致力于人们假想并以固执的疯狂追随的永久世界的持续性发展最终却沦为一个可怕幻景的牺牲品,人们必须对所有无法预见的东西做好思想准备,这也是一种充满忧虑和不很乐观的基本态度;因为乐观主义助长了片面性推断和错误安全感的滋生,它也容易导致人们忘记过去的消极经验”[8]。
(二)解构技术主义的调适方式
从根本讲,当代灾疫是由人力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所渐进积累起来的攻击和残害人类生命的灾难。阻止、降解这种人力造成的攻击和残害人类生命的灾难,需要重建人类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之间的调适方式。
人虽然是自然的产物,也成为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但由于人类物种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分离意识、对象性观念和自我设计与创造能力,更具有从顺应自然的众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调适他物、调适环境、调适自然的能力。疫灾从古代的自然主义向当代的人力主义方向演进和发展,最后形成疫灾的世界大流行,也主要源于这种调适能力。以石器生存为逻辑起点,自进入农牧社会以来,人类调适自己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技术。技术之所以成为人类调适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基本方式,是因为人类必须不断解决存在安全和生活资源保障问题的根本工具,只能是技术:技术是人类向生物世界要存在安全,向环境和自然要生活资源的根本工具,也是人类自主存在的主体性条件和创造性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构成人类调节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基本方式。技术之于人类的如上功能,使它必须伴随人类进化而发展,或可说,人类进化的基本形态学呈现就是不断发展技术,从石器时代起步,人类技术从农牧社会的手工技术体系向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体系再向后工业社会的生物工艺学技术体系方向的发展历史,也名副其实地是人类调适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方式的演进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类走了一条从遵循自然本性转向征服自然本性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征服、改造、掠夺构成人类以绝对主宰者的姿态强求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绝对服从人力意志的根本方式,是不断开发的技术,是技术主义。当代疫灾的世界化和日常生活化,恰恰是这种技术主义刚性调适方式无限度地扩张运用的体现,因为技术创造出人与存在环境、人与地球生物、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全新生态关系,这种新的生态关系却降低了人对存在环境、人对地球生物、人对自然世界的调适能力,强化了人对存在环境、人对地球生物、人对自然世界的征服、改造、掠夺能力,加大了人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分离和对立,破坏了人与环境生态的动态平衡关系及其调节机制。所以,人类要从根本上阻止、降解、减少疫灾,需要放弃技术调适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方式,有限度地开发技术,将技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的功能降低到最低限度,使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能够促进自然、环境、地球生物增强自恢复生境的能力。
(三)恢复伦理生态学的生物调适方式
从根本讲,自然始终是一个有机体,人类永远存在于自然这个有机体之中,自然的生生本性和限度存在对人类存在及生存敞开做出根与本两个方面的要求,建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物调适方式和文化调适方式。
从生境逻辑观,技术主义调适方式被推向极端,最终制造出源源不断的环境灾害和世界大流行的当代疫灾。世界大流行的疫灾,既把人类存在推向绝境,又为人类新生提供了可能性契机,因为世界大流行的疫灾警醒人类正视瘟疫的力量,正视生物、微生物以及细菌、病毒的力量,改变口福之欲和无限度的物质幸福之欲,学会有节制地存在和有限度地生存,为此需要重新正视和恢复生物调适的力量。
生物调适,是指以生物规律为准则来化解人类存在姿态、生存方式和行动方式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之间的对立,使人类行为适应生物规律。从根本讲,生物规律就是生物与生物、物种与物种、种群与种群之间的相生规律,或者说共生规律。生物存在于自然中,生物的相生规律的依据是生,源泉是生生之性。人类行为适应生物规律的实质是遵循自然本性,运用自然的生生本性来调节人类的生生利欲,使之有限度地释放。
从人类史和疫灾史观,人类的进化之路实是以生物调适为起步,它表征为人类拜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以自然为准则而谋求生存[9]。人类进化的阶梯,具体敞开为技术的发明与不断革新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类渐进地转向以自己为师,向历史和经验学习,并逐渐弱化生物调适生存的功能,最后以技术调适方式取代了生物调适方式。当技术成为调适人类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根本力量时,造成的必然恶果是对存在环境的破坏、对地球生物的蹂躏、对自然世界的征服,最终推动整个地球生物包括微生物以一种暴虐方式展开对人类的报复:当代疫灾就是地球生物和微生物以肆虐释放方式强迫人类的技术调适服从生物调适,或者说当代疫灾是地球生物和微生物以绝地反抗的肆虐方式强迫人类服从生物规律、尊重微生物规律,这种强迫促发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智慧在对付致病微生物上,几千年来仍然还停留在摸索阶段,因此,疾病在作物、畜群和人类当中的滋扰,在整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事务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27恢复生物调适方式,就是人类生存应以生生之性的自然伦理为准则来重建人类社会伦理和个人生活伦理,使伦理生存重获生境位态。
(四)重塑伦理生态学的文化调适方式
生物调适,是人类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共生存在的根本调适方式,但是,在人类进化走向技术化存在的当代进程中,“物种之间一般的生物调适似乎还不足以制约人口的增长。原因在于,产生和支撑人类进步的与其说是生物的调适,不如说是文化的调适,于是,每当一两种关键性资源被耗尽、人类利用自然的既定方式面临困境时,他们的智力总能帮他们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利用新的资源,由此一次次扩展我们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大自然的统治权”[2]19。在技术化存在的当代社会,恢复生物调适的根本前提是人对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根本认知,以此改变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存在姿态,这种改变需要重塑其文化调适方式。
重塑文化调适方式,实质上是依据生物共生规律和自然之生生本性来重建人类伦理生存的生境位态的基本方式。就其本质言,文化调适就是启动文化的力量来调节人与存在环境、人与地球生物、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对立,释放自然伦理的生成性功能,使之重新达于动态平衡,恢复生境。文化调适的根本要求是节制,重心是节制物欲和节制生产[10]。
节制物欲的根本方面有二:一是节制物质幸福无限论欲望。对人类生存言,物质幸福始终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物质始终是有限的,有限的物质也只为生活幸福提供可能性,并不为生活幸福创造必然性。二是节制技术创造生活幸福奇迹的欲望。在世界大舞台上,技术创造生活幸福的奇迹同样有限,因为技术原本是柄双刃剑,它为人类创造生活奇迹的同时也创造生活的灾难,它给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给人类制造阻碍,它为人类开辟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在压缩、剥夺人类的自由。比如,现代工业社会是机械技术体系向生物工艺学技术(或曰智能技术)体系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技术成就是电子通信、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会聚技术、大数据分析等,对这些新技术的整合运用,释放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奇特力量,这就是对物理时空予以任意的扩张或压缩。这种扩张和压缩物理时空体现出来的一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就是信息和交通世界化。然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构成当代疫灾世界大流行的重要推手,即世界化的信息和交通网络既成为当代疫灾世界化传播和变异的土壤、平台、渠道,也成为当代疫灾世界化传播和变异的基本力量,因为信息和交通世界化,将人类变成了一个村庄,使农村也成为城市的有机部分,使城市与城市之间拆除了地理空间和物理时间的阻隔之墙。以此可以明知,生存理性地节制对技术的欲望,成为文化调适人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的对立关系,从而恢复共生存在的伦理生境之根本方式。
节制生产的首要方面,是节制物质生产。节制物质生产的基本方法有二:一是解除物质主义的社会导向,破除经济和财富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的神话,取消惟经济增长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二是解构消费主义经济政策和消费促生产的社会动力机制,实施有节制、有限度地生产,使物质生产遵循“用废退生”的环境规律,即经济是嵌含在环境之中,经济发展必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经济向前发展的生存代价,就是环境遭受破坏;经济无限度地发展,环境就会遭受无限度的破坏;反之,经济发展越是有限度,环境就越具有自恢复和自修复生境的功能。有限度地生产,就是使物质生产能够促进环境充分发挥自调节和自修复功能,恢复生境。环境重获自调节、自修复、自恢复生境的能力,是阻止、降解和减少当代疫灾的重要方式。
节制生产的根本方面,是节制人口生产。从疫灾史观,推动疫灾爆发从自然主义向人力主义方向转化的根本力量,是无限增长的人口。
“1万年以前,地球上只有500万到1000万人。据联合国记录,第60亿个人诞生的日期是1999年10月12日。保守估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9亿,净增的人口中有90%以上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是促使环境毁灭的最强大的动因。迅速增长的人口扩大了人类造成的环境影响的规模,使变化的发生更加迅速。”[11]
“食物的生产允许人口数量大量而快速地增长,而且很快推动了城市和文明的兴起。人口一旦集中到了如此大的社群中,就会为潜在的病原体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其情形一如非洲草原的大型猎物为我们的远祖提供食物来源那样,在人类的村庄、城市和文明的发展所创造的新环境中,这回轮到了微生物可以期待猎食美味了。”[2]22
人口的无节制生产,不仅为“病原体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也为病原体的繁殖和传播提供了人口密集的空间土壤。节制人口生产,既是阻止、降解、减少当代疫灾的根本方式,也是指导人类恢复与存在环境、地球生物、自然世界共生的伦理生态学方法。
结 语
人类虽然已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人文存在的物种,但它依然保持本原性的生物存在,这是因为“人类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我们无一例外地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人类历史的界限和其他物种一样,相互渗透着”[12]。世界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此论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面对如上事实判断,身处环境灾难和疫难之中的人类,必须放弃意志主义的张狂,俯下身段承认两个存在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学会从两个方面调节自己的存在态度和行动方式。
第一个事实是人类存在于自然世界之中,人类要继续延续其存在,不能逾越自然法则。近代以来以崇尚自然资源无限论、物质幸福无限论和经济发展无限论为社会动力所构筑起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行动方式,实实在在地以一种“无限度的扩张”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3]的努力将人类推进环境灾难和疫难重重的“后世界风险社会”进程之中[14],完全是人类逾越自然法则的层累性“恶果”。重新向自然学习,学会尊重自然法则,接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是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陷阱的必须前提。尊重自然法则,以自然法则为存在指南和行动规范,必须从制度、法律、道德、经济、市场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整合性建构节制欲望、限度存在的社会引导体系。
第二个事实是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人类,只是众物中之一物,并与万物共享一个世界,其存在敞开既有界限,也与他物相互渗透而共存。在人类存在敞开的生存进程中,其偶发的、非连续的、局域性的瘟疫,更可能是气候环境和人类卫生能力低下造成。但是,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原本偶发性、非连续性、局域性的瘟疫以连续性、全球性和世界化方式爆发,并将人类存在和生活纳入病毒加速迭代变异的恐慌和繁忙之中,则意味着孕灾因子和孕疫环境更多地源于人类智-力基于物质主义的傲慢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对多样化的地球生物的狂暴掠杀、对微生物世界的张狂。改变疫灾世界使之重新恢复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回归人间正常生活的唯一理性方式,就是学会尊重生命,学会敬畏生命,学会善待生命,不仅仅是学会尊重、敬畏和善待人的生命,更要学会尊重、敬畏和善待生物世界的生命和微生物世界的生命,尤其是要学会尊重、敬畏和善待微生物世界的病毒这一生命存在。从根本讲,微生物世界是不能随意搅动的,一旦搅动起了微生物世界,病毒就会以一种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方式回馈人类的暴虐,新型冠状病毒的世界大流行,新毒株超越气候、超越地域、无视时空和任何形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而在任何场合加速迭代变异,或许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微生物世界不能任意搅动,一旦面对因人类的无知和狂妄搅动起的微生物世界的病毒暴虐,宜学会放下“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微生物病毒的愚蠢执念。因为,纵观人类灾疫史和病毒史,任何一次瘟疫的结束都不是以真正消灭了那种病毒为胜利的标志的,而是人类以生命为代价去学会适应这种病毒,并最终学会与之和解为标志。从人类疫灾史观,引发人类疫难的任何一种病毒都没有被消灭,每一次疫难的结束,仍然是病毒与人和解的方式或寄生在人体中、或伴随在人的身边或生活的周围。当身体健康能够压得住它时,它成为你的伴侣或者说你生命的一部分,当身体处于亚状态或出现更弱的状况时,它就在你身上兴风作浪,这就是疾病。在人与微生物矛盾对一统一的存在世界里,病毒可以消灭人之个体生命,甚至可以消灭人类,但人包括人类却无能力消灭病毒。妄想消灭病毒的执信最终会彻底解构人与微生物世界之间的极为脆弱的共生存在的平衡框架,结果只能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消逝和人类的毁灭。因而,学会尊重微生物世界,学会敬畏病毒,学会善待病毒,与病毒共存,是人类将自己从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疫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正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