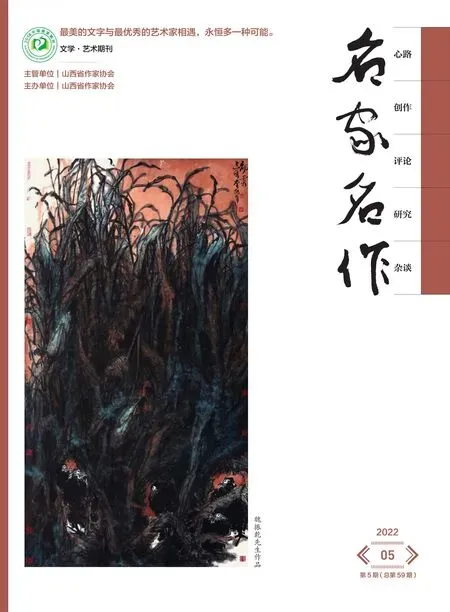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化文体范式—从语言文字运用的角度阐释
任晓兵
沈从文不是一个善讲故事的作家,故事的跌宕起伏亦与他无缘;同时他也不是一个能将自己内心动荡起伏的情感在小说中加以外化,并对外化物加以臧否是非的人。沈从文将自己的人性诗学审美理念倾注于湘西小说的叙述之中,他对这种审美理念所怀有的种种情感体验完全熔铸于文本中所描述的湘西的每一处地方。沈从文在文本中从不侧身而出,为自己的审美理念摇旗呐喊,他让自己的情感沉隐于叙述的底层,绝不让它浮现出来。于是,沈从文独特的艺术品性、精神气质、审美理念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人事与景物相融为一的叙述资源对他的滋养相融合,形成了其湘西小说绵细悠长、娓娓道来的诗化文体范式,虽略显冗长但却情真意切。本文即从诗意性语言和意境这两个向度入手,具体分析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化文体范式。
一、诗意性的语言
语言是小说得以以文本显现的最重要媒介,因此小说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语言现象。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语言运用是他实现其诗化文体的一个重要形式。“小说文体的实质不在于表达了何种故事情节或思想内容,而在于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体式去表达……相同的思想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技巧表达,因而,语言表达体式的差异导致了文体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语言是小说文体的物质外壳,也是认识小说文体特征的切入点”。
语言的锤炼是沈从文始终重视的因素,他甚至说:“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条件之一……不懂文字,什么是文学。”沈从文对小说语言的运用有着“推敲”的执着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痴迷于语言文字的艳丽和形式的精巧,他认为小说写作讲究文字若步入这样的歧径则会使文章成为“四六文章”,真正的语言文字运用要义是在于“以约见著,能于少分量文字中解释并表现给读者一种较深较持久的效果”。
多年的刻苦磨炼使沈从文对语言的实践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其总的特征是“格调古朴,形式简峭,主干突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呐却又传神”,带给读者一种诗性的古雅气息。如《边城》开篇的叙述语言: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的韵味,在娓娓道来的描述中为读者铺设了把情境投向旷古悠远氛围的通道,使得文本的情感基调瞬时确定。其文本中有众多描述景物的文字,如: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混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
这段景物描写具有古典山水游记的特点,读之疑是柳宗元《小石潭记》的现代白话译文,句子明白淡雅、长短并用,如一泓山泉汩汩流淌,有声、有色,又大体上采用排比的修辞技巧,间有回环与复沓,形成一种有着内在节奏和韵律的舒缓语调。
又如《长河·秋》中的一段景物描写:
“祠堂位置在山坳上,地点较高,向对河望去,但见千山黄草,起野火处有白烟如云。村落中乡下人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稻草,傍附树根堆积,无不如塔如坟。银杏白杨树成行高矗,大小叶片在微阳下翻飞,黄绿杂彩相间……幻异不可形容。”
作家在这段话中,融情于景,化静为动,在铺陈中显现凝练,于浅显中见出含蓄,田园风光的清新秀丽之质在语言的内在节奏和韵律中显现出来。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语言运用在外在形态上还具有如下鲜明特征,即作家使用最平常的语言文字却能生出异乎寻常的艺术美感。这种特质首先表现为沈从文湘西小说无论是描述景致还是叙写人事都极少使用修饰性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其效果是能在无意间提升语言表达的精确性与艺术性。《边城》的第二段全部文字都是在描写自然背景,但作家竟然只有三处运用了形容词,即“静静的”河水、依然“清澈透明”“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即便如此,沈从文仍旧成功地真切展示出湘西唯美的风情画卷。试看沈从文的描述语言“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这比直接描述为缓缓的溪水、弯弯的小径更具神韵。“一篙不能落底”“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这比直接叙述为“溪水清澈见底”更具审美效果。整个语篇段落沈从文虽未采用诗的格律以及修饰性的语言,但读来却诗意盎然。其次表现在沈从文擅长文白相间的四字句运用,如:
“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蜺,驰骤其间。绕城长河,每年三四月春水发后,洪江油船颜色鲜明,在摇橹歌呼中连翩下驶。长方形大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据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游人四瞩,俨然四围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
在这段语篇中,沈从文大量运用了四字句,除少数是作家化用了古人词句且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固定套语的四字句如“积翠堆蓝”“驾螭乘蜺”“视若无事”外,其余均是沈从文从湘西民间口语中撷取并刻意加以组合的,如“游人四瞩”“四围是山”“弄船女子”“危立船头”等。这些四字句不仅打造出一个情景相融的艺术境界,且使语言的表现紧凑、富有节奏。此外,湘西小说中沈从文还偏向使用长短交错的语句,如:
“她每天应作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摘南瓜花或狗尾草戴到小丈夫头上,或者亲嘴,一面说:‘弟弟,哪,啵。再来,啵’”。
“到了夜里睡觉,便常常做这种年龄人所做的梦……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或一时仿佛身子很小很轻,飞到天上众星中,没有一个人,只是一片白,一片金光……”
这些长短不一的句子交错使用在同一语境的逻辑表述中,句法上突破一般语法规则,讲究内在节奏和韵律,在变异中传达出新意,表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形成回环婉转的节奏美,使语言表现具有了流动的韵味。正是在此意义上,沈从文才说:“正如同很好的音乐,有一种流动而不凝固的美;如同建筑,现出体积上的壮美;如同绘画,光色和线恰到好处。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也能做到这个情形。”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语言除了上述特质之外,还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一是语言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模糊,语言的所指不明,往往超越符号本身的所指,隐含在话语群所组成的关系中,从而形成特定的语境;二是语言的隐喻性。
小说《边城》的结尾作家这样叙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语言符号所指与能指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两者间的关系模糊不清,造成难以得出明确的事实或判断,将读者带入了一种人生渺茫与孤独的境界,交织着憧憬与绝望、幸福与哀伤的淡淡哀愁。类似这样的语言表述在作家的湘西小说中比比皆是,如:“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船再次离岸之后,柏子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是否还能再次回来,一切都在沈从文所营造的言语所指与能指界限模糊的情境中,扑朔迷离,让人捕捉不到确定的答案。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化特色还在于语言表述的隐喻性。诗化叙述技法的小说与隐喻运用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隐喻其本质就是诗性的,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言有尽而意无穷”“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可不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正是由于隐喻这种修辞手法具有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差异,从而扩大其能指的内容,造成意义的延伸这样的语言表述效果,因而“一部叙事作品可以通过隐喻来丰富、扩大、深化文本的诗意内涵”。当隐喻喻指的旨意在于蕴含和揭示一些特定的精神内涵时,隐喻即象征化。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话语理解有时颇为艰难,这就是由于读者要时时停驻思索作家通过隐喻修辞设置的深邃语义,无论是语段的隐喻设置还是整个文本隐喻系统的构造。
《边城》中对翠翠有这样一段叙述——“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飞上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蹿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
这段描述表层是对翠翠梦境的叙述,但深层却是通过隐喻的修辞“引人于溟漠恍惚之境”,从而传递出为朦胧的爱情甜蜜感觉所陶醉了的翠翠的心理情爱感受。而《边城》的整个文本被看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文化隐喻体系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即“当《边城》的牧歌图式指向一个文化隐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边城》的牧歌属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中国想象——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为可感的艺术造型”。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语言表述一方面切近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语言表述技巧,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语言表达进行了融合,这是他创作湘西小说时文体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沈从文运用这种语言营造原始自然的湘西世界和淳朴优美的人性,用最质朴的语言感召最质朴的人之本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艺术形式服务于艺术内容的典范,质朴的语言也恰好是沈从文一生对质朴纯真人性追求的印证。
二、由语言建构的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的意境
1941年5月2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上做了一次演讲,后来该演讲以“短篇小说”为题刊登在1942年4月16日出版的《国文月刊》第18期上。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就小说创作的问题说:“一个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他会从传统接受教育,得到启迪或暗示,有助于他的作品完整、深刻与美丽,并增加作品传递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极自然的。”沈从文接着说明:“我说的传统,意思并不是指从史传以来,涉及人事人性的叙述……重要的是有个传统艺术空气,以及产生这种种艺术品的心理习惯。”这句话表明沈从文认同传统的文化艺术品质会对一个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
沈从文进而阐明了这种中华传统的文化艺术品质,即“一面承认材料的本性,一面就材料性质注入他个人的想象和感情。虽加人工,原则上却又始终能保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这句话的内涵即是艺术创造应尊重现实题材或材料的自然本性,用其自身的属性去表现它们自身的品性,但这种表现又不是自然主义式的直接阐发,而是要注入作家的理想和情趣,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在这篇文章中,关于现代小说创作与传统艺术的关系,沈从文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作小幅绘画上注意……见出短篇小说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这些绘画无论是以人事为题材,以花草鸟兽云树水石为题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品最高的成就,重要处全在‘设计’。什么地方着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过问。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著笔墨处,因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沈从文这些重要的认识,触及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范畴——意境。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审美理想的一个核心范畴,然而,什么是意境?张璪提出了他的艺术创作理念:“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和心源的凝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结晶体,鸢飞鱼跃,剔透玲珑,这就是‘意境’,一切艺术的中心之中心。”简而言之,意境就是创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交融渗化而形成的一种审美境界。王国维是意境范畴发展史的最后一位总结者,亦是终结者,他忠诚地守护意境这一艺术的古典审美理想,指出其“内足以憾己而外足以憾人”。构建意境,是沈从文湘西小说写作自觉的努力追求,是其湘西小说诗化文体的又一重要表现向度。
意境范畴被引入中国现代小说后,更多的是指“一种主客观统一,情景交融,物我无间而又饱含理趣的艺术境界,一种具有丰富的情感容量和高度美感价值的抒情场”。在写作过程中,主观情感的抒发与恰当客观世界相联系,达到一种物我无间的和谐境界,即构成文本意境。具体而论,沈从文湘西小说意境的营造,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情景交融,化情思为景物,景成了情的感性显现,是情由抽象的心灵变成可把握之物的唯一现实途径,有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二是虚实结合,寓虚境于实境,化景物为情思,在虚实的隐显间达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艺术效果。
沈从文的天性中包蕴着楚地之人热烈奔放、富于幻想的气质,早期都市生活中的碰壁,使得沈从文自然对家乡的山水风物心向往之。家乡山水景致、人事风物的一切情绪性印象都能迅速地打动他,强烈地刺激他。所以,湘西世界洁秀唯美的自然景致和朦胧秀逸的人生情事共同交织成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物境。在这样一个物境背景下,沈从文揉进个体的主观情愫,使人与物、景与情达到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这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特具的诗性魅力。
《边城》仍旧是无法绕开的文本: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
文本开篇的景物描写,仿佛化外之境,不带任何的瑕疵,它洁净、透明、清爽,处处给人以怡情陶醉的感觉。这样的景语如果没有沈从文主观上的心仪,是难以充满生机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些具有和谐诗意的自然景物中,生存于其间的人也仿佛与自然化为一体,显现出已经逝去很久的人之神性。老船夫活了七十年,摆了五十年的渡船,他任劳任怨、达天知命、宽厚仁慈、慷慨豁达、与人为善,中华传统道德的一切美德在老船夫身上都有迹可循;掌管水码头的顺顺,似乎都见不出任何上层人物的恶德,他为人大方洒脱、明事明理、正直平和、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即便是那些妓女,沈从文也赋予她们边地秀丽山水、淳朴习俗滋润下养成的厚实性情,虽出于生存,然在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里所有的人都有着自然山水的灵秀清新气息,景即人,人即景,对自然景致的用力描述与欣赏,无不寄寓着作家对湘西家乡人之灵动清秀品质的膜拜。文本中沈从文用笔的中心人物翠翠,更是遗落凡间的仙子,是白鹿原上飘逸的灵秀白鹿。她绝无可能是尘世的女儿,她只能是自然的女儿,自然的山水长养了她、教育了她。沈从文《边城》中的景物描写都浸润着浓郁的情,既包括文本中人物的情也包括沈从文在其中寄托的情;而情感的抒发又都可以外化为湘西别致的景;情与景难分彼此,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美感价值的抒情场。在这种抒情价值场中,沈从文构建的牧歌中国形象抗拒着已被现代侵蚀的世俗中国,让我们对未来产生憧憬。
在沈从文的其他湘西小说中,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创设也都具有艺术的别样魅力。《长河》中写夭夭在祠堂前扫地所见情景:“树叶子已落了一半,只有一点点微风,总有些离枝的木叶,同红紫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景物越发清疏和爽朗,一切光景静美到不可形容。”自然景致的描写透露出乡村静谧的气息,灵动秀美的女孩夭夭活动在这样的自然景致中,使得景更加美。在这里,人与景高度地交融于一,展现出了沈从文内在的情思。
虚实结合,寓虚境于实境,化景境为情思,在虚实的隐显间达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艺术效果,这是沈从文湘西小说意境建构的第二种模式。小说《菜园》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对玉家母子,相依为命,他们原是辛亥革命前来边地做候补的玉太爷的遗孀和遗孤,满族旗人。辛亥革命后清室被推翻,于是母子便以种卖白菜为生。因为母子种的白菜是当年从北京带来的菜种,所以在当地最为有名。母亲是位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的妇人。儿子玉少琛心地善良、对人诚实,闲来看看风景,吟吟诗文。儿子二十二岁那年,去了北京读书,三年后,带回来一位漂亮的媳妇。然而,三人其乐融融的日子没过多久,儿子和媳妇便被当局肆意地杀害。玉家母亲在孤寂痛心的生活中煎熬了三年后,也上吊自尽了。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沈从文以节俭的文字平淡地书写,即使是在人物那最揪心的痛苦过程中,沈从文叙述得也仍内敛。所有围绕这个事情要产生的情感沈从文都平静地寄寓在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中,然而文本中人物内在的情与作家本人的情却无一不历历可察。《丈夫》中对极端践踏人之尊严和人格的地方、新婚妻子外出为妓的情形,沈从文这样叙述:
“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是否这样的描述意味着作家对这赤裸裸的人间苦难已经失去了判断的察觉?还是意味着作家已经麻木?都不是。沈从文深受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熏染,即使是惊涛骇浪的情感波澜沈从文也能够将它们隐蕴在对生活场景和事件的纯客观叙述中。因此,在《丈夫》中沈从文将对造成这种人间畸形悲剧因素的内心愤激之情(虚)寄寓在不露声色的客观实态场景(实)中,从而真正做到了“大音希声”。
在小说《贵生》中,沈从文借助于“虚实结合,寓虚境于实境,化景境为情思”这种艺术表达方式,鲜明地写出了贵生在得知自己心爱的人弃他另择后的一系列发展着的情绪波澜,建构出了一个寄寓贵生极度痛苦愤恨相交心理情态的意境场。其具体表现就是作家极力回避对贵生心理情境的直接描述,而是以贵生一系列外在神态和肢体动作的叙述为主,将贵生内心所有的情感(虚)都转化为他的神情动作(实)。当贵生抱着最后一丝还没有熄灭的希望之火并用试探性的反语询问金凤渴求得到否定回答的企图破灭后,贵生回到铺子狠狠看了老板一眼,拔脚就走;当几个长工在背后戏谑即将嫁给五爷的金凤的话语被贵生听到后,沈从文是这样叙述的:“贵生不做声,咬着下唇,把手指骨捏了又捏,看定那红脸长鼻子,心想打那家伙一拳。不过手伸出去时,却端了土碗,咕嘟嘟喝了大半碗烧酒。”短短的几句话却将贵生刹那间的心理激烈情绪道出,在“实景”的描述中内蕴了丰富的“虚境”。“贵生不做声,咬着下唇,把手指骨捏了又捏”,这是贵生得知别人亵渎了他心爱的金凤而愤怒的情感表现;“不过手伸出去时,却端了土碗”,这时的贵生猛然醒悟金凤已不是他的爱人了,他没有资格去教训他人;“咕嘟嘟喝了大半碗烧酒”,写出了贵生内心的悲痛欲裂。在这里,沈从文将连串的“意”化为了具体可察的物象和行为,却更加实现了显现主观情韵的艺术目的。
从中国古典艺术创作中开掘出其永恒的艺术魅力精神,自我生命体验形成的人性审美理想,独特个人人格素养以及文化气韵的共同作用,使得沈从文在其湘西小说中努力创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天然本真的意境。这是他创作湘西小说时文体创新表现与语言构建并等的又一重要展示。沈从文运用意境展示原始自然的湘西世界和淳朴优美的人性,感召最质朴的人之本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湘西小说对意境营造的追求如其简明平实的语言风格一样也是艺术形式服务于艺术内容的典范,同样这也是沈从文一生对质朴纯真人性追求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