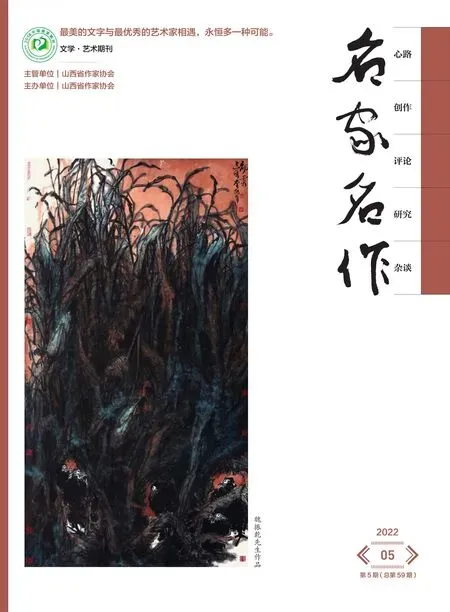细读《孔乙己》
张建春 杨 威
作为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孔乙己》以其冷峻的笔调克制地叙事,不经意间地臧否,成功地为我们展现了底层知识分子,准确地说——科举制度下进阶失败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作为吴敬梓《儒林外史》精神与文脉的延续,对于在新旧文化互相碰撞下,旧文化土崩瓦解下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作者以其生花妙笔予以了准确而客观的描述。“孔乙己”因其标本式的存在,在世界文学史的文学群像中熠熠生辉。
小说开头,详细地描述了独特的南方市井风俗图,“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随后,有一处貌似漫不经心的闲笔,“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这处闲笔,可以说是闲笔不闲。须知,作为具有虚构性质的小说,其最大的敌人就是虚假,而在此处刻意强调“现在”,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为了让读者更加直接地进入小说所描绘的世界——鲁镇,作者用贴标签的方式,将顾客分成了短衣帮与长衫派。短衣帮与长衫派以符号化的方式对鲁镇进行了解构,非此即彼,泾渭分明。
接着,“我”也就是文中的“小伙计”出现了,作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的所见所闻无疑也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小说中写道:“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注意“无聊”两个字,是整个小说的绝佳注脚,正如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所言:人生如同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作者写道:“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仍然是“无聊”,反复铺垫,为孔乙己的出场蓄势,“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孔乙己的价值仅仅是博人“笑几声”,又让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
接着,孔乙己出场了,鲁迅先生首先强调了他的身份,“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无疑孔乙己的身份极度尴尬,他自己也缺乏最起码的身份认同感,犹如蝙蝠一般——异于禽,异于兽。在精神层面,孔乙己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理所应当穿长衫,所以长衫无异于是他精神贵族的外化符号,而现实又无比残酷,物质上的困顿又不得不让孔乙己“站着喝酒”,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割裂,让孔乙己充满了荒诞性,孔乙己可以说是流动的行为艺术,自身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黑色幽默。作者对孔乙己的外貌以及服饰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其精神图腾长衫,“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让人不由生出“余生也晚”的感叹,这件长衫我们无缘睹其干净时的样貌,现在只剩下脏破,可是孔乙己还要坚持穿在身上,他最后的倔强不由得让人感慨唏嘘。“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众人的“笑”实际上并无恶意,最起码大家认为并无恶意。孔乙己以其精神上的高傲未做理会,“他不回答”,而且带有挑衅性质地“排出九文大钱”,注意这个“排”字,这可谓是孔乙己人生的高光时刻,于是看客们继续着孩子式的恶作剧:“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对于这种单纯的人身攻击,孔乙己可以不做理会,但人们说“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对于涉及人格的攻讦,孔乙己必须做出回应:“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金句频出,只得偷换概念,玩点文字游戏,他近乎天真地认真应对,终于“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人类的可悲之处是——有时候是狼吃羊,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羊吃羊。
为了让孔乙己的形象更为丰满,除了别人视角中的形象,作者还特意安排了别人背后的议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作者以另外的一种比较讨巧的方式来完善孔乙己的人物形象,同时作者说孔乙己虽“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强调“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作者实际在说孔乙己偶尔的偷窃不过是生活所迫,但对于儒家道德范畴的大节“信”,孔乙己是深以为然的,并不是像其他的知识分子说说而已,鲁迅先生寥寥数笔,就揭示出了孔乙己性格中包含的复杂性。
当然,猫抓住老鼠以后,最大的快意绝不是马上吃掉老鼠,而是纯享于一场精致戏耍所带来的精神盛宴。看客们是非常精通兵法的,看到孔乙己“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就先示弱:“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等到孔乙己志得意满之时,他们才发出致命一击:“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对于孔乙己人生当中最为惨痛的事情,看客们是深谙打蛇打七寸的道理,于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这“灰色”可以说是“死灰色”,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于是“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快活的空气”却让我们感到了一种浸入骨髓的寒冷,看客们的这种阴毒的玩笑,让我们感受到了底层人们之间的这种互相伤害,快乐似乎永远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按照马斯洛理论,需求可以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排列。作为底层知识分子,孔乙己在酒足饭饱基本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后,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然,在成人世界作为弱势群体,孔乙己是无法满足以上需求的,于是他只能将视线投射到孩子身上。“你读过书么?”孔乙己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渴望与人交流,也就是社交需求的一种体现,然后又很恳切地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自然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了,再看“我”,“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而孔乙己立刻“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因为自己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出现了经典的“回字有四样写法”,科举制度下所谓的学问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不由会想起吴敬梓写范进不知苏轼,马二不知李清照。可见八股取士对读书人学识、眼界、思想的禁锢——为了应考,他们只读考试用书,只做八股文章,对包括苏东坡、李清照的诗词文章在内的所谓杂学毫无接触。
接下来,是孔乙己与孩子们的良性互动,“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无疑这是孔乙己的快乐与别人的笑在文本中唯一一次完全契合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隐藏在文字背后不易被人察觉的温暖。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用自嘲式的笔调写道: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先生的悲悯于不动声色间流露出来。尤其是孔乙己的名言:“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好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他对整个世界抱有最大的善意,而现实却如黑铁般冷酷无情。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可谓是一语成谶,孔乙己的这种可有可无的存在价值,可以说是他悲剧命运的千里伏脉,悲凉的气息在文本中弥漫开来。
本来孔乙己的腿被打折,应该是他的生命中最为惨烈的部分,而描写也应该是高潮迭起,而鲁迅先生却并没有这么处理,他反而用了异常冷静与克制的笔调,如动作描写“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如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言描写,“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巨大的事件与情感的冷漠及行动上的无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此使文章内部具有强大的张力。再说对孔乙己腿被打折的叙述,由于小伙计是限知视角,所以只能由别人只言片语的讲述来拼凑还原事件,无形之中使得小说更加客观真实,作者尽可能退居到人物角色之后,当然这也是对中国传统小说写法上的致敬与传承,如《三国演义》中写关羽温酒斩华雄:“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当然,好的文章都是相似的,不好的文章才各有各的坏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冰山漂浮在海面上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它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可是在水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山体。海明威以此比喻写作:作家有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是蕴藏在文字背后的,真正通过笔端表现出来的只有八分之一。如果作家能够处理好这一点,读者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八分之七的分量。艺术上的克制留白在此有着完美的体现,中国艺术重视空灵之美。虚实,是中国美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虚实结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在虚实之间,中国艺术对虚更为重视,因为实从虚中转化出来,想象空灵,故有空际;空灵澄澈,方有实在之美。老子说:“大白若黑。”在至虚之处有至实之感,这个白,并非空白,而是一个灵气往来的地方。密不透风、气韵不畅无疑是失败的。留白即“冰山理论”中水下之冰,它静默无声,却又博大而深沉。
很快,就到了孔乙己谢幕的时候。首先,是鲁迅式文笔的景物描写“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真正地体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秋风好比人心,人情冷暖在孔乙己身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后,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温一碗酒”。接着写外貌:“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与前面刚出场时“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我们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到孔乙己已经日薄西山,马上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再看他的衣服,“穿一件破夹袄”,孔乙己已经被生活剥去了象征知识分子身份的长衫,他彻底被打回了原形,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孔乙己已经成为高不可攀的奢侈品,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成为必需品。掌柜的看到孔乙己后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他关心的仍然是孔乙己的欠账,与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被排在了第一位,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都是漠不关心的。然后是一如既往地拿孔乙己取乐:“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因为事实摆在面前,孔乙己只得说:“不要取笑!”老板步步紧逼刀刀见红:“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可以说老板撕下了孔乙己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用最为轻松的语气残忍地剥开了孔乙己的伤疤,孔乙己赤身裸体鲜血淋漓地在大家面前示众,老板可以讲是全无心肝。当然这并不是孔乙己的耻辱,而是整个社会的耻辱,丛林法则的使用程度可以说是社会文明与否的试金石,我们看到在鲁镇,丛林法则大行其道,整个成人社会弥漫着野蛮、冷漠、自私的味道,弱肉强食,每个人都渴望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而每个人又不可避免地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这也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到的旧中国的生态模式——“吃人”。下面又写到了“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两次“笑”,孔乙己的一生仿佛就是以笑开场,以笑谢幕,而所有的笑几乎都与孔乙己无关,笑都是与孔乙己疏离的,都是无厘头的,看客式的笑毫无缘由,充满了集体无意识的意味。孔乙己的此次出场,毫无疑问是对他死亡的一次预热。此时,出现了一个细节“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这次已经变成了“摸”而非“排”了,“摸”有从袋里往外挖出的意思,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折了腿,生活更苦,只能“摸出四文大钱”,神情沮丧。与前文“排”对比,鲜明地表现了孔乙己每况愈下的悲惨境地。随后,鲁迅仍然不动声色地描写“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用这手”“走”,我们感受到一种滑稽的残酷感,这无疑是鲁迅先生故意为之,这已经不是欧亨利式“含泪的笑”了,而是鲁迅式“神经撕裂的笑”了。
然后,孔乙己被人记起了两次,一次是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另外一次是到第二年的端午,掌柜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其生命的有无仅仅与微不足道的十九个钱有关,而更为荒诞的是记挂他的人其身份不过是债主而已。最后,孔乙己作为个体生命,犹如他在粉板上的欠账一样最后被轻轻拭去了。最后,鲁迅先生用神来一笔为孔乙己的生命做了最后的注解:“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表示是自己的推测,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但从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的状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是必死无疑的。当然我们不妨进行开放式阅读:文中的孔乙已是死了,但生活中的类似“孔乙已”的人实际是活着的。这是鲁迅的“冷”幽默,常冷不丁地激发你的思考。死了,连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没有,更深刻地表现了孔乙己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