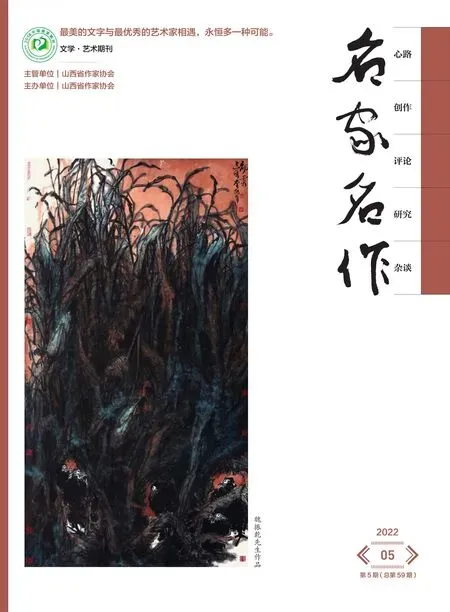不道德的战争故事—评《士兵的重负》
郎文畅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越战争,也称越南战争,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重大的战争。越战是冷战中的“一次热战”,这次战争对越南和美国都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越南所受损失更甚,而美国使用的化学武器至今都给越南留下难以磨灭的伤害。美国作家蒂姆·奥布莱恩作为一名曾经参与越战的退伍士兵,他善于将战争的故事讲述给读者,他笔下的故事无限接近越战的真实与参战士兵的内心。“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从来就不是道德的”,翻开这本书,读者能得到的或许与所期待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一次相当痛苦的阅读经历。
一、企图逃离的美国士兵
小说集《士兵的重负》又名《美国大兵都携带了什么》,作者十分专注和客观地分析了美国士兵在越南战场上的携带物。作为战争小说作家,作者并没有将战场厮杀的场面呈现到我们眼前,只讲美国士兵要携带的必需品有哪些,再逐一分析这些物品的用途。这些被携带的物品包括幸运物、披风、照片、一些恐惧和无数的幽灵。
美国大兵亨利·多宾斯带着神圣的仪式感将女友的连裤袜围在脖子上作为幸运物,即便女友要求和他分手,他仍拿出连裤袜围在脖子上安慰自己“魔力不会消失”。当他出于恐惧只能将安全感寄托于一条无意义的连裤袜时,他是可怜的。
在谈到披风值得带的原因时,作者解释披风可以作为裹尸布,并详细描述拉德文死时是怎样用它来裹尸的,这样沉静的叙述甚至有些残忍。珍爱的照片可以是克罗斯中尉永远得不到的纯洁女孩马莎的照片,也可以是年轻战士在粪坑中寻找的前女友的唯一的照片,他们在幻想的爱情中企图拯救自己,让精神暂时逃离战场。一路追随他们的幽灵是战友和敌人,那些战友死时有的像一堵墙砰的一声倒下了,有的则在粪坑中挣扎不久就了无生息,死亡的场景给每个人的内心笼罩了一层阴影。
然而最重的负担是懦弱。士兵们带着难以抑制的恐惧与懦弱,那是在惊恐时的大喊大叫、低声哭泣,那是在长时间暗夜行军后的精神失常并向自己开枪,那是想要逃离却不敢放弃名声的悔恨。他们恐惧战争,但为了声誉,为了避开逃兵的耻辱,他们不得不参战。在战场上他们也有着更大的恐惧,害怕死去,更害怕把这种心理表现出来,他们试图克服懦弱,但只能更加懦弱,承担着恐惧与懦弱向战场的更深处走去。《雷尼河畔》中的“我”试图做一个逃兵,但最终像个懦夫一样去参战。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参战的士兵早就想要逃离。《夜生活》中的拉特·基利难以忍受黑夜行军的无尽恐怖,打穿脚趾离开,他表面上的懦弱却是内心深处的勇敢,他实现了逃离,尽管背上逃兵的恶名。战场上的一切故事,美国士兵们的心理状态,都证明了没有人全心全意地投入战争,反而内心深处一直想要逃离。然而最为沉重的负担——懦弱让他们无法离开。与其说这是一部战争小说,倒不如说这是一部士兵想要逃离战争的小说。
二、消失的越南士兵
当这部小说集被视为战争小说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作为敌方的越南士兵去哪儿了?小说集的名字本来就叫作《美国大兵都携带了什么》,难道作者因为太过专注于讲述美国大兵携带了什么以至于忘记描述越南士兵了吗?其实作者的这种安排有着其背后的深意。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作者讲述的重心就是美国士兵的状况与心境,对于越南士兵的描写仅仅按需来完成,作者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其次,越南士兵并非完全不被描写,在小说《伏击》中,作者回忆起“我”因一时冲动打死的那个毫无威胁的越南士兵,长时间以来,“我”都未能原谅自己的所作所为,长久地被愧疚感所折磨,经常回想起那个年轻士兵的身影,他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永远的“负担”。在《我打死的人》中,“我”面对年轻的越南士兵的尸体,出现了幻觉,幻想出他成长的前半生——热爱数学、和女孩相爱、抱着必死的信念参战。心理学家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曾谈道:“幻觉代表了一种比人的情欲更深沉更难忘的经验,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幻觉的产生让“我”站在越南士兵的立场上体验了他的一生,而在这样的体验过后,难以接受的是手染鲜血的现实中的自己。这年轻的、被打死的越南士兵是作者未曾描写的越南军队的缩影。一方面,他代表了在美越战争中越南所处的地位——处在劣势的一方,被实力强大的美军士兵轻而易举地击倒。另一方面,越南士兵的惨死成为美军士兵的噩梦,是在他们内心道德约束之下难以承担的愧疚与自责,成为他们在行军时与退战后未曾甩开过的沉重的负担。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最为沉重的部分是越南士兵的幽灵。
尽管在这部小说中战斗的场面不重要,战斗的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大兵上战场时都携带了什么,但是作者刻意避开了战斗的画面,刻意不去描写越南军队,也隐藏着另一重背景。作为非正义的一方,美军士兵即便不情愿,也只能任人摆弄。非正义的战争使美军士兵没有所谓的坚定的信仰与战斗的意志,有的是对战争的恐惧与无奈。避开对惨烈战场的描绘同样意味着作者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对越南军队的尊重,对美国是非正义一方的肯定。“如果能使你害羞,那么你才能讲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作者认为战争的不道德正是其真实之处,因此会害羞。而避开越南战场的厮杀,避开越南战士的惨烈,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作者本身的“害羞”。
三、后战争时代
克罗斯中尉最渴望的白日梦是“他和马莎都光着脚,沿着泽西海岸行走,什么也没有带”。他不用躲避爱情,不用毫无目的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杀戮,不用带上约150磅重的装备行军,他什么都不用带。这是所有人的梦想。然而当他们回到现实,回到后战争时代,回到家乡,回到没有任何东西要带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切都变了,只有战争给予他们的噩梦没有变少,反而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经历战争的洗礼后,士兵们出现奇怪诡异的举动。战友之间成为敌人,在《成为朋友》中受伤的斯特伦克央求战友戴夫“不要杀我”;福斯的女友玛丽爱上了嗜血的战场,将死人的舌头串起来做成项链戴着;“我”因为记恨卫生兵乔根斯不及时救助而联合朋友假扮幽灵士兵戏弄他;莱蒙的牙明明没有坏却觉得疼痛难忍,非得牙医把他的好牙拔掉才觉得痛快。在战争中士兵们的心理遭受了巨大创伤,战后产生了怪异的行为与不安的心理。从心理学上看,这属于战后创伤应激综合征的表现,心理学家认为“在精神异常者之中,通过荒谬古怪的物质现实或者同样荒谬古怪的非现实来歪曲美和意义,这种行为是人格毁灭的结果”。战争所带来的黑暗回忆,使正常的人陷入怪异的毁灭自身的陷阱当中去。
死亡是战争的关键词,作者不吝笔墨描述死亡,小说充斥着对死亡的反复描述。在整部小说集中,死去的几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提及,如同梦魇笼罩着每一个士兵的心。面对战友特德·拉文德的意外去世,目睹一切的基奥瓦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四次描述拉文德像一堵墙一样砰的一声就倒下了的场面。蒂姆在冲动下打死了一名年轻的越南士兵,直到现在这段记忆都挥之不去。基奥瓦的死同样给士兵们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战友诺曼·鲍克在退伍后仍会回忆那次死亡的恐怖与恶臭,以至于难以遏制地感到自责。吉米·克罗斯中尉更是将士兵们的死看作自己的责任,不断忏悔。在“我”幼年时期,九岁的琳达与“我”之间有真挚的爱情,然而在那时“我”却见证了琳达的死亡。但“我”一直相信象征着纯洁、美好、爱情的小女孩与战争中不幸去世的士兵们一样存在于一个死者的世界中。作者不断偷窥着那个晶莹的世界,“我翩翩年少,开心快乐,永远都不会死。我掠过自己历史的表层,迅疾地滑行,蹬着在冰刀下融化的冰面,环绕着、旋转着”。在这个世界中作者找到了能够原谅自己、见到故人的机会,弥补了死亡带来的回忆的裂缝。
在这部小说中,“我”是小说家,也是参战士兵,“我”就是作者本人,“我”是讲故事的自我救赎者。一方面,“我”作为参战士兵出现时是出于讲述战争故事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作为作者本人出现时则是关于越战老兵通过讲故事治疗精神创伤的另一层故事。“请相信:故事可以拯救我们”,作者在《死者的生命》开头就强调。在黑暗的回忆当中难以走出的人是多数,战友诺曼·鲍克就在家乡教会的更衣室里自缢身亡。作者通过写作成为幸运的能够自我治疗的人,正如作者所说:“当我高高跃入暗夜,又在三十年后落下,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就像蒂姆在努力以一个故事来保留蒂米的生命。”尽管回忆充满黑暗,然而讲故事能使一切变得客观化,能使自己暂时脱离战争噩梦的钳制,在讲述回忆的过程中,越战老兵保持了自己与黑暗的距离,也在反思中得以救赎。
四、叙述的艺术
在《士兵的重负》中,作者有其独特的叙述风格,语言犀利、精准、冷静,但同时讲述却柔和与真切,他的叙述成为自传体与散文化两种风格的融合。
使小说充满冷峻色彩的是频频出现的命令性短句。这或许也与作者曾经的军人身份有关,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命令作为动词时,是强制的意思,但作为名词时,其特称不仅仅是强制,也是简短、有效、权威。在《士兵的重负》中,作者常用简短的陈述句来开头或结尾。在描述值得商讨的情节部分与相当复杂的心理状态时,作者却惯用一个简短的陈述句。“他们携带的东西主要是必需品。”“他们被称为步兵。”“他们的负重还由任务决定。”“他们都带着幽灵。”“他们是坚强的人。”“毕竟,他是一名军人。”这些短句自成一段,往往出现在小说情节的开头或结尾。不是缓冲,而是紧张;不是随意,而是强调;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克罗斯中尉是一名将领,属于他的命令是决不松弛、显示力量、避免去爱。他手底下的士兵们收到的命令是带好必需品、克服恐惧、隐藏懦弱。而作为读者,作者给我们下的命令是趴在战场的掩体下,冷眼盯着某个美国步兵负担了什么来经历短暂的一生。
冷峻不是绝对,更多的时候,作者采取散文化的叙述方式舒缓气氛。在讲述战争故事时,作者并不专注于故事本身,相反他加入了太多“我”的插叙与看法,并且他讨论主人公们的想法,讨论战争的意义,判断爱情是否存在,给读者提供设想的空间。在回忆故事时,他将稠密的爱、压碎的爱穿插在吉米·克罗斯中尉行军途中执行任务的每时每刻。他在故事中讨论,这场战争是如何的毫无目的,没有输赢。甚至有时候,他忽然停下来,告诉你他是一个四十三岁的作家,并与你探讨自己所讲故事的真实性。这部小说整体上看似乎成了一部散文化的自叙传,然而作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又使读者的阅读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叙述的时间与空间上,作者运用了复杂的游戏。作为一部可被视为参战士兵回忆录的小说,作者并未刻意隐藏自己的存在,反而将“我”作为大多数篇章中都会出现的人物。有时“我”并非关键人物,仅仅作为引起回忆或讲述回忆的工具,但大多数篇章中作者将我的自述、想象、经历、作者手记单独成篇,这其实对读者造成了一种阅读障碍。“我”的过去并未展示,“我”的现状也并未讲明,但作者将“我”处理为一个有着越战经历的退伍兵作家。只有“我”与美越战争相关的部分才展现出来,这其实造成了节奏的冲击性,不断地将越战故事在不断变幻的时间与空间中进行讲述。小说集中的时间跨越过去、现在、未来,空间包括战场、故乡、远方,人物不停变动但又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庞大的战争故事体系。他运用散文化的笔调来讲述每一件有关战争的小事,在讲述的过程中通过充分调动感官描写、心理描写使人身临其境。叙述视角的跳跃,叙述时间的变换,使读者陷入凌乱而真实可感的战争回忆当中,成为同样深陷战争阴影的越战老兵。时空的变化和叙述视角的多变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而正是在这种破碎的叙述方式中,作者回忆的破碎导致战争的破坏性与毁灭感迎面而来。
对于蒂姆·奥布莱恩的叙述风格的评价,可以用小说中的一句话,当李·斯特伦克抽到危险度极高的探索地道的任务时,“米切尔·桑德斯对其他人说,有时,你只好等下一次。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了。然而,没有人笑”。作者仅仅为我们讲述了美国士兵上战场时携带了什么,他试图用爱情缓冲紧张,用散漫的笔调稀释残忍,用躲避厮杀来减少冲击,他尽量平实和简短地描述,故作轻松。然而,却没有人笑。
五、结语
在蒂姆·奥布莱恩参与过越战,经历了真实的战争后,写作成为原始经验拼命寻求表达的发泄方式。蒂姆·奥布莱恩讨论了什么是真实的战争故事,他的小说未曾修饰地将战争的不道德一股脑说出。残酷的、不道德的、可怖的战争直白地呈现于读者眼前。美国士兵在这样一场让人想要逃离的战争中,成了被迫牺牲的“喂虫子的肉”,他们的回忆里充斥的是恐惧、忧伤、疯狂和刺耳的笑声,他们在暗夜中行走一圈后,心底向往和平的呐喊是给人类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