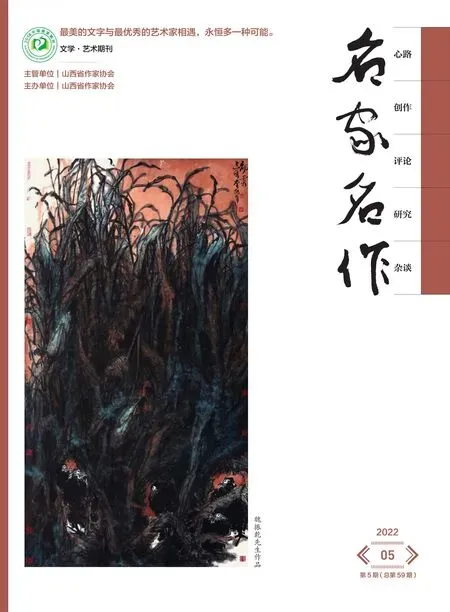论吉本文学中非典型的家庭形态及其特征
何木凤
一、引言
吉本芭娜娜1987年初登文坛,以处女作《厨房》荣获当年的新海燕文学奖,成为文坛新晋之秀。其勤耕细作,之后陆续发表了四十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斩获各类奖项,一度掀起“芭娜娜现象”之热潮,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其作品主题多为讲述一名心灵深受创伤的少女之成长历程,作者通过大量作品反复展示了人物从孤独彷徨到平静坚强的治愈之路。为了描述主人公们的成长,作者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非典型家庭,人物的疗伤之路可以说是从失去旧家庭到被新家庭接纳或组建新家庭的过程。家庭是人物生活成长的场所,是生命的必经之路,他们既因家庭而痛苦,又因家庭而得救。这些形式各异的非典型家庭暗示了在传统家庭以及规范家庭以外家庭形态的其他各种可能,本文欲对非典型家庭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分析,以探讨作品关于家庭的思考和观念,使文学的意义照进现实。
二、非典型的家庭形态
一般而言,家庭形态有两个侧面,其一是家庭构成,即由什么样的人员形成这个家庭;其二是家庭规模,即由多少人形成这个家庭。战前日本家庭的典型构成,一般认为是作为社会生产单位的直系亲属传统大家庭,具体指子女中的某一个结婚后仍然留在原家庭中居住,一般表现为长子作为家庭的继承人与父母共同居住,大都由三代人构成的家庭形式。它的重要特征是家庭成员代代更替,家庭一直延续下去。战后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革,20世纪60年代夫妇型家庭逐渐取代了直系亲属家庭成为主流家庭形式,即所有子女在结婚以后都离开自己生长的家庭,重新组建新家庭。一般表现为由夫妇和其子女构成,具有由结婚而形成、由夫妇的死亡而终止,只限于一代人的特性。从家庭规模看,吉本文学中描绘的无一是三代以上的亲属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全是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小家庭,一般是由二人或三人组成,由四人以上组成的家庭极少,这个一目了然,不必展开论述。从家庭构成方面看,作者一次次刷新“核心家庭”的典型模式,刻画了各种各样非典型的家庭形式。通过归类分析,大概体现如下:
1.不完整的家庭
相对于由父母及其子女构成的完整的家庭形态,吉本作品中出现得最多的是一个家庭解体或终结后的破碎、不完整的形态,其中又以母子家庭的描述为最。例如《厨房》《彩虹》《喂喂下北泽》等作品都讲述了关于母子家庭的故事。著名处女作《厨房》中的男主人公雄一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现在的母亲惠理子原本是他的亲生父亲,原是男性,年轻时与亡妻恋爱时因不被父母接受,两人离家出走、私奔结婚。妻子生下雄一后不久意外离世,但他始终没返回原来的家庭,而是选择通过变性成为一名母亲,独自带着孩子在外以小家庭的形式生活。尽管过程如此复杂,但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母子家庭的形态。在《彩虹》中,主人公“我”11岁时父亲因婚外情与母亲离婚,之后“我”一直和母亲及外婆一起生活,外婆去世后则母女相依,形成一个母女家庭。在《喂喂下北泽》中,“我”的父亲在妻儿毫不知情的状态下,毫无征兆地与情人殉情自杀了。故事以此为开篇,讲述父亲去世后“我”与母亲离开自家大房子搬到出租小屋,开启治疗这段痛苦的母女生活。如是等等,众多作品常常开篇则简略交代父亲这个自始至终不会出现的角色的去向,然后展开一个父亲不在场的母子家庭生活的故事讲述,勾勒了一个个母子家庭的形态。
此外,作品还描写了许多祖孙家庭。《厨房》中女主人公的家庭便是如此,美影年幼时便父母双亡,打小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上中学时,祖父去世,之后便一直与祖母相依为命。《蜜月旅行》中的男主人公宏志自出生起父母不知所踪,被遗弃于祖父家,自小与祖父一起生活。
2.非婚生子家庭
吉本文学中关于家庭的描述远不止是社会规范内的不完整状态,还有脱离社会规范的非婚生子,即私生子家庭。作品《鸫》中就刻画了一个非典型的非婚生子家庭。女主人公名叫玛利亚,父亲已婚,但妻子并不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他的婚外私生女,五岁之前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后来和母亲两人住在一个海边的小镇上,父亲则在遥远的东京生活,只在节假日偶尔来小镇看望母女俩。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她上大学。故事的后来父亲与原妻离婚,与她的母亲成了合法的登记夫妻,但作品主要描述的是他们成为法定夫妻前那个时间段的母女生活。《泡沫》中也刻画了一个私生子家庭,主人公“人鱼”的母亲与父亲也不是一对实行婚姻登记的合法夫妻。父亲是一个“怪人”,从年轻时起便靠着父母留下的财产随心所欲地过日子,他整日游手好闲、不工作、不结婚,在邻街的一座废墟似的房子里生活。母亲是他的恋人,两人并未结婚却生下了孩子人鱼。她自小与母亲两人一起生活,生活费全是父亲给的,但她从未与他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过,偶尔见过几次的父亲留下的是一副即使没有喝酒也醉醺醺的样子,扯着嗓门大声说话的形象。
3.非亲家庭
吉本文学里还描绘了不少非亲家庭,即由非亲属关系、不持有血缘关系的人员组成的家庭。《泡沫》中父亲没有与人鱼母女共同生活,自己一个人住在临街的一个房子里,后来有一天一个朋友将一枚大钻戒和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放在他房子的庭院里,便出国去了,自那时起他便与那个母亲遗弃的孩子一起生活。被遗弃的孩子是岚,他与人鱼父亲并无血缘关系,他自己也知道实情,他们也不是养父养子关系,两人互相称呼对方的名字,在这种状态中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岚长大成人。在《哀愁的预感》中,主人公弥生四五岁时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离世,她被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并非亲属的家庭接纳,共同生活。这两部作品描写的是自幼时起便与无血缘关系的人一起生活的故事,《厨房》与此不同,描写了一个成人后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临时家庭。美影在最后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之后孑然一身,孤独痛苦,生活无法持续之时被陌生人田边雄一的母子家庭所接纳,三人组成了一个“非姻非血缘”的暂时性家庭。在这个临时的家里,她丧失至亲的伤痛以及孤独一人面对未来的不安和彷徨渐渐得到治愈与抚平,在这对陌生母子的帮助下,她得以走出人生的至暗时刻。
三、家庭特征
如上所述,吉本文学中的非典型家庭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其展示的特征也特别鲜明。具体可归纳如下:
1.脆弱易破
首先显而易见的特征是脆弱易碎,貌似都市化生活之理想的核心小家庭是极其不稳固的。前文指出传统大家庭具有家庭成员代代更替、家庭一直延续下去的特性;而现代以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则具有由结婚而形成,由夫妇的死亡而终止,只限于一代人的特性,即稳定是短暂的,破碎分裂是随时的。在作品中家庭解体的直观原因多表现为家庭成员的死亡和外力的冲击,内在原因则是这一家庭结构的特性使然。由一对夫妇或与其子女构成的家庭结构过于单一,一点外来的冲击也很容易使其崩塌,如《哀愁的预感》中的车祸、《厨房》中的疾病、《喂喂下北泽》中的殉情自杀、《蜜月旅行》中的不明邪教团体等,这些意外都直接促使了当事家庭的崩溃、瓦解。另外在作品中家庭功能更重视情感共融倾斜的转变也使其脆弱易碎,因为感情发之于心,人心有坚强的一面但更有其脆弱的一面,吉本文学中描绘的人心尤其如此,他们对未来不确定,认为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即使没有外力的冲击,家也未必就能牢固不破,因为他们对他人的心甚至对自己的心也无法作出不变的保证,感情亦如是。人心易变,那么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易变的,由人组成的家庭自然也是易变的。
作者描绘各种家庭的解体,并不是对现代家庭的易破特性进行批判,而是通过描写其易碎性传递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家庭的完整和安定是短暂的,此时聚在一起,彼此温暖,但不会长久不变,因此要珍惜当下;二是家庭的终结和破裂是常见的,是人不得不面对的,尽管很痛苦,但如果发生了就只能接受它,带着记忆继续往前走。
2.父权失落
其次是父权的失落。如前所述,大量作品都描绘母子家庭的生活,少有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情景,父亲因死亡、自杀、失踪、离婚等原因缺席于家庭,或者从不被提及直接被隐身于家庭,这些广泛存在的“父不在”设定强烈反映了传统家长制的式微,父权被束之高阁,其时代已经远去了。同时,过去父权家庭的“繁衍子孙”这一重要目标也不再重要,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孩子不再是仅属于男方家庭的、继承男方血脉的后嗣,而是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前文提及的非亲家庭中的两个例子,孩子与无血缘的人一起组成新的家庭,也不是为了继承家业或后继有人以“养子”的身份生活的,而是作为一个被尊重被关爱的、独立的生命而存在的。此外,相关情节出处可见。在祖母去世后,向美影伸出援手的除了雄一还有宗八郎,“一个大家庭的长子”,个子高高的,两人站在一起时“我看他总是要仰视他”,同时我也“对无论怎样都难以跟上他的脚步的自己感到厌恶”。其实让她产生“仰视”以及觉得“总是跟不上”心理的不是对方的身高和步伐,而是其作为大家庭长子的身份及其所自带的特性使她感到压抑,所以她没有选择他。渐行渐远的不是宗八郎,而是其代表的父权家长制的生活形式。
另外,父权制把家庭的存续和繁荣作为至上要求,作为后代的子孙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体现家风的祖父母作为家的代表养育和培育孙子女并不是异常现象,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前文所提及的祖孙家庭并非这种情况,它描绘的是只有祖母或祖父与一个孙女或孙子组成的家庭。而且这些祖父母并不对孙子孙女进行道德示范,也不会把孙女看作是继承家庭血统。例如美影奶奶,不管美影夜里多晚回家,她都不会有一句埋怨或训斥,她不规训孙女也不娇惯孙女。她也不把孙女看作是带给祖母快乐的实体,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和精神寄托,是一个尊重孙女、活出自我生命感的祖母形象,这种祖母类型的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父权家长制的暗淡。
3.规范和血缘淡化
最后是社会规范与血缘关系的淡化。社会规范里,一般实行婚姻登记的合法夫妻及其子女构成的家庭才是被认可的。作品里描述的婚外私生子(如《鸫》)以及非婚私生子(如《泡沫》)的这两种家庭体现了弱化社会规范的文学特色。《鸫》中家庭属于婚外不伦,背负社会道德的十字架,母亲看上去似乎都泰然自若、乐观开朗,但玛利亚觉得那是表面现象,认为母亲不是一个天生坚强的人,她只是装出一副没有痛苦的样子,其实内心多有不安。她认为“不管周围的人对妈妈怎样好,看不到未来、寄人篱下的‘第三者’的生活却是无法改变的”,也许正是因为能够理解母亲的心情,玛利亚似乎没经历什么叛逆期就顺利长大成人,并形成了善于体谅且平静温和的性格。作者略过其合法与否的问题,直接将人物置身于该境况中,带着批判探讨在此类家庭中生活的孩子的成长。《泡沫》中的家庭则稍有不同,父母两人都是单身,是恋人关系,只是他们选择不结婚。他们生下了孩子人鱼,但并没有一起生活,父亲虽没有一起住,但一直负担着母女的生活费,也算是共同养育了孩子。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新的家庭模式,不如说是新的生活方式,作品人物选择了社会规范之外的一种生活方式。
另外,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不再以“血缘关系”作唯一维系,作品中由不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员构成的家庭不在少数,血缘不再是组成、维系家庭这个团体必要的、永久的纽带,这是血缘淡化的最直接表现。它是“子嗣后代、血脉传承”的家长制价值观衰退后必然发生的,同时伴随着情感交流融合的日益强化,即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融合与否成为家庭构建和维系的重要标准。作品中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使存在血缘关系,但如果没有情感方面的交流与共鸣就无法进入同一个“家”。众多父亲被隐形的母子家庭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即使是至亲血脉如父亲,如果没有参与家庭生活,没有和家庭成员建立情感,也不再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了。反之,如果情感融合,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组成一个家。众多作品人物在血缘家庭解体后,常常进入了一个非血缘家庭生活疗伤,并在那里因得到情感上的接纳和共鸣而治愈痛苦,重新达到平静并生出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吉本文学描述了许多非典型的家庭形态,这些都是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家庭形态,并不是作者空想架构出来的,但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歧视,作者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是与标准家庭相左的或者是相悖的例外形式加以严厉批评,而是当作家庭的一种正常的存在方式,“人物”们在其中生活,或喜或悲,这种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家庭的理解是充满包容性的,这种文学上的包容对现实社会观念有极大的正面影响的作用。另外,尽管描述了许多脱离社会规范的家庭形态,流淌着对固有家庭社会观念和范式的批判和反思,但作者并未展现人物对家庭的逃离和抗争,其对家庭的意义始终持肯定态度,主人公们对家庭始终抱有向往、饱含深情,家始终是带给人安定与幸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