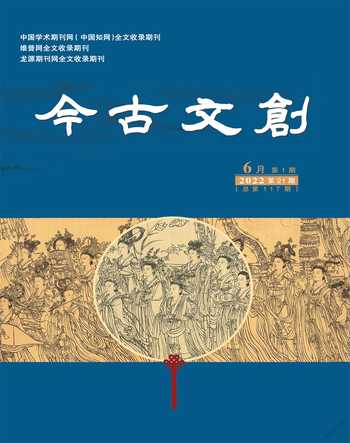《万箭穿心》到《我的姐姐》 : 女性主体意识 构建的流变
【摘要】在我国电影发展的长河中,塑造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创作者观念的转变,从阮玲玉到李宝莉、从英子到安然,电影中女性角色的视角逐渐扩展,主体意识逐渐转变。但女性意识存在“自我”与“他者”两种眼光,“他者”的眼光是女性自我意识建构的重要参照物[1]。在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中对女性意识的表现与存在受到深度集体心理、主体自我认知行为和身体美学消费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使女性自我意识的凸显更加自觉化[1]。
【关键词】女性主体意识;理想女性;受众需求;独立自主 家庭关系
【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8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27
在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很多的经典女性角色塑造与主体意识建构都深受当时社会环境、受众心理与创作思路影响,她们身上承载的是整个时代“理想女性”的标签。《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受到中国封建家庭的迫害与影响变成了深宅大院中钩心斗角的四姨太;《归来》中的冯婉喻,在那个特殊时代痛苦的挣扎在亲情与爱情之间,最终与爱人相见不相识;《甜蜜蜜》中的李翘,从大陆到香港追寻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但她仍然纠缠在黎小军和豹哥之间,依靠豹哥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在黎小军身上获得情感的满足。在影视剧和当时的现实,女性都是依附者,表面上她们为了大爱,为了追求心中的爱情,但实际上她们是为了男人而活,她们是男权社会的弱者,必须要牺牲[2]。她们是社会陋习与阴暗面的承受者,根深蒂固的女人是“第二性”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女性只能依照着其构建出的“理想女性”来塑造自己,成为一种具有“社会代表性”和“社会刻板印象”的符号。电影中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被桎梏。
《万箭穿心》与《我的姐姐》两部影片是以女性角度来讲述中国家庭关系。从李宝莉到安然,在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上存在着递进关系,她们都是对大众认知中传统女性角色的挑战。虽然她们最后走向了妥协,但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女性主体意识的流变,安然相较于李宝莉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权的束缚。
一、《万箭穿心》中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
电影《万箭穿心》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武汉的一个普通家庭,丈夫马学武是一家国企的厂办主任,妻子李宝莉是汉正街的一名小贩,二人有一个儿子小宝。李宝莉性格强势泼辣,管理着家中的大小事务,马学武性格懦弱,虽看不惯李宝莉的行事作风却一直隐忍。男女性格和家庭权利地位的颠倒是导致这个家庭以悲剧收场的主要原因。
(一)女权主义色彩的女性角色
影片中男性角色的篇幅较少,着重塑造了文化水平不高、性格强势的李宝莉;仗义理性、性格泼辣的万晓景;贤惠温柔、大方得体的周芬等女性角色,讲述了她们在家庭、婚姻、社会中的挣扎。
李宝莉是城市蔬菜小贩的女儿,下岗后在批发市场卖袜子。从影片开场的主动求爱和与搬家师傅的争吵中可以看出她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她勇于表达自己的需求与观点。当初马学武因她泼辣的性格喜欢上她,但是人到中年,当两人的爱情在柴米油盐中消耗殆尽时,她强势的性格间接造成了丈夫马学武的出轨与自杀。面对丈夫提出离婚,她对闺蜜哭诉、讨好丈夫、举报丈夫出轨尽力维持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李宝莉只是用强势的性格来掩饰自己因没有文化而产生的自卑,她的生活依旧依托在男性话语权下。丈夫自杀后,她婉拒了闺蜜的帮助,做起了扁担,她身上背负了母亲、儿媳的身份。当高考结束后,婆婆和儿子因丈夫自杀对她的怨恨在饭桌上彻底爆发,她因儿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委屈而难过,还有自己辛苦十年却换来被赶出家门的不甘心,可当她在江边看到欢声笑语的孩子们后,因为没有给儿子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而愧疚,所以她最终选择了离开。
李宝莉这一角色身上有着与不公命运对抗的决心,她想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她的一切努力都没能逃开男权话语,这就使她又陷入传统女性的宿命。剧中“他者”的视角也以传统女性的标准来要求她,儿子小宝认为她与健健的感情不道德,婆婆认为她的付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影响下,她倔强与拼搏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人生,是为了丈夫、为了儿子、为了家庭。影片最后,她坐上了健健的面包车将自己又陷入新的家庭关系中。虽然,李宝莉在形象塑造与性格表现上对于传统女性角色的塑造是有突破的,但在她的主体意识构建方面还是非常的符合当时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定义。
万晓景是李宝莉的好朋友,她性格泼辣对于丈夫的毒打会予以还击,对丈夫的出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她的认知中,情感需求次于物质需求。影片中,她的出场全部围绕李宝莉扮演着“导师”的角色,在李宝莉嫌弃马学武是乡下人时,提醒她婚姻里不分高低贵贱;在李宝莉落泊时想要帮助她。她的婚姻同样是不幸的,但她在婚姻里的选择让她走上了和李宝莉截然相反的道路。她在劝导李宝莉时表达的婚姻中男女平等的观念、不屑于关心丈夫,只管过自己的逍遙日子、尽力帮助遇到困难的李宝莉等都表现了她对于生活有着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就此来看她的主体意识是那个时代所少有的。但她做这一切的资本来源却是在依托丈夫获得的。
周芬是国营工厂工会成员,她戏份不多,属于传统意义上温婉大方的女人,她的出现让马学武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李宝莉婆婆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有着文化人的清高看不起没有文化的李宝莉。她以传统婆婆的形象出场,无条件地偏向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她的出现彻底激化了家庭矛盾。马学武自杀后,她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李宝莉态度冷漠,将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李宝莉,这种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宝。周芬与李宝莉婆婆这两个角色的塑造,符合大众认知中温柔贤惠的女人、无私奉献的母亲、和蔼可亲的奶奶、恶毒伪善的婆婆,对于她们的形象塑造和她们以家庭为主的主体意识的构建,完全符合当时社会受众对于女性的角色设定。
(二)男权话语下的女性主体意识构建
影片中对于每一位女性角色的塑造都是成功的,她们贴近生活,立体丰满。主人公李宝莉身上具有传统女性特征,如坚韧、热心、对朋友有情有义,另一方面她身上具有传统女性形象所不常有的性格特点:脾气暴躁、泼辣、强势、强横无理[3]。虽然她性格强势、泼辣惹人讨厌,但在发现丈夫出轨时仍选择委屈自己保全家庭,宁可在不幸的婚姻中挣扎,仍然要将这段婚姻维持下去。何嫂子和李宝莉婆婆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将家庭、孩子、丈夫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这些角色的构建反映着社会“他者”对女性的认知。《万箭穿心》虽然塑造了一个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女性角色,但却是在男权话语下对女权主义者进行了构建[3]。影视剧中构建的女性形象是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固化,最后深化了女性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影响着自我意识缺乏的女性,让她们有着只要家人幸福、家庭和睦便心满意足的贤妻良母的主体意识。
二、《我的姐姐》中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
电影《我的姐姐》围绕失去父母的姐姐安然,在面对追求个人独立生活还是抚养弟弟安子恒的问题上展开了一段细腻感人的亲情故事。
影片以姐姐安然的视角展开叙事。在安然小时候,父母为了要一个男孩,謊报她身有残疾。高考时,安然填报的志愿是北京临床医学专业,被父母以“女孩要早点赚钱养家”为由,偷偷改成了家乡的护理专业。大学四年,因为弟弟安子恒的出生,安然与父母的关系愈渐疏远,考研去北京成为她摆脱父母的光明出路。但父母不幸车祸身亡,给她留下了年仅六岁的弟弟安子恒。原本已经明确人生规划的安然,面临着要抚养关系冷漠疏离的弟弟,还是追求个人理想的艰难抉择。影片将一个家族中所有的人物都设定为姐弟关系:安然与安子恒、姑妈与安然父亲、安然妈妈与舅舅、表姐与表弟。影片通过几对姐弟关系的变化,交代了时代更迭下,社会对于“理想女性”标准的变化。
(一)“母一代”与“子一代”
影片中女性主体意识构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姑妈为代表的一直遵循着“长姐如母”观念,牺牲自己的人生去成就弟弟的“母一代”女性和以安然为代表的寻求实现“女性自我价值”观念,独立自主、追求自由的“子一代”女性的冲突中。
安然从小就承受着“男尊女卑”观念带来的影响,她因为穿裙子在阳台挨打时喊出的那句“我不是瘸子”是对父权的第一次反抗,这为她在大学期间与家里几乎断绝联系做了铺垫,也从侧面展现了她倔强、独立的一面,让她在父母过世后,面对家里一众亲戚对于弟弟抚养问题的争论时,能够果敢的提出送养弟弟的意见有了性格依据。除了家庭中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压迫,在情感上,面对懦弱的“妈宝”男友,在他一次又一次地向长辈和社会现实妥协时,安然虽有不舍,但仍会选择与他分手。在工作中,安然面对有权阶级的压力,虽然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应有的公允对待,但她还是会勇敢的反抗。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姑妈这一角色一直站在安然的对立面。她从小就被教育“长姐如母”,母亲背着她给弟弟偷偷吃西瓜、因为弟弟要上中专,而让考上大学的姑妈做出让步、刚到俄罗斯创业却被叫回来帮弟弟带孩子。姑妈受到传统思想的教育下所构建起来的主体意识让她认为自己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影片中对于安然妈妈这个姐姐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从安然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于丈夫想要生儿子的做法一直都是默认的。舅舅游手好闲的性格从侧面展现了安然妈妈是和姑妈一样的存在。
影片中还有一个较为出彩的男性角色是舅舅,肖央将这个本来有点讨人厌的角色演绎的有几分讨喜。与安然和姑妈不同,舅舅武东风是“男卑女尊”观念的受益者,但从他身上表现出的对于“重男轻女”观念的情绪却是最弱的。在一众亲戚因讨论弟弟归属问题与安然发生冲突时,舅舅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安然。女儿可可因为他爱打牌与他关系不好,他厚着脸皮去舞蹈教室看女儿被轰出来也不生气只有无奈。在与安然的聊天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女儿的愧疚,女儿结婚时,拜托安然送上礼金,这所有的一切都表现了他对女儿的爱。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安然会说出:“希望舅舅是她的爸爸”的原因。安然也渴望从舅舅身上寻求从小就缺失的父爱。在这整个家族里,姐姐都是牺牲品,但一事无成的舅舅又何尝不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受害者。
(二)两代女性主体意识的交融
影片中,安然与姑妈两个人的矛盾是两种观念的碰撞,是两个时代中“理想女性”标准的交锋。安然排斥弟弟,根本上是排斥扭曲的“香火”观。在面对为了生儿子不顾惜妻子生命、执意将妻子转院生产的家属,安然绝望地喊出了“你都生了两个女儿了,为什么还要生啊?儿子就那么好吗……你们这是谋杀!”身处21世纪,有人还为了生养儿子可以牺牲妻子为代价,而妻子又如此心甘情愿,这是对人和整个时代的嘲讽[4]?
姑妈的形象是“扶弟”女性的代表,她身上有着中国式家庭的凝聚力。但她的主体意识也不是完全丧失的。她也会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感叹:“我那会多年轻啊”,在安然说:“我不想成为下一个你。”时也会被触动。最后她说:“套娃不是非要装在一个套子里。”与安然达成了和解,同意了将弟弟送养的计划。两个人在吃西瓜的那场戏以安然给姑妈鞠躬结束,暗示着两人达成了和解。两个人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了变化与融合。至此,安然与姑妈完成了的相互救赎。安然在姑妈身上感受到了不可摧毁的家庭力量和责任,姑妈也在安然身上看到了女性的更多可能。影片结尾,安然拒绝签字,从领养家庭将弟弟带走,这一具有争议性的开放式结局引起观众热议,部分观众认为安然被姑妈同化。这并不是安然对于独立生活的放弃,而是从姑妈身上看到了家庭的责任,相较于以前,她更加“人性”,从这个并不熟悉的家人身上汲取到了温暖,有了家庭的情感羁绊。她的情绪伴随着理性与感性交融,所以安然最后的选择符合她的主体意识,当代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形成了从全然为了家庭、为了男权转变为实现自身价值属性的构建。影片对于安然的角色塑造,完全是迎合了大家对于当代女性的固有认知“独立自由”,基于当代社会“理想女性”的新标准,这样更能够让观众产生共情。
三、李宝莉到安然:女性主体意识构建的流变
从李宝莉到安然,女性角色的主体意识构建有着较大的变化。如果将安然与李宝莉的选择互换,那么两部电影都很难引起观众共情。李宝莉所处的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缺乏,外加深受影视剧和大众传媒广告中塑造的女性“为家庭、为丈夫、为儿女”的贤妻良母形象影响。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出现偏差,转而学习传媒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打造自己,进而丧失了对于自己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考。“李宝莉”也就成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代表。
在时代变化下,社会环境和创作观念发生了转变。影视剧中,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和主體意识的构建发生了较大变化,像《妈阁是座城》 《送我上青云》 《少年的你》中的“独立女性”所做的选择更多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离开了与传统直接对话的场域,展现了她们颇具现代性的一面,也获得了大多数观众的谅解与共情[5]。
影视剧中塑造的安迪、曲筱绡等女强人形象是社会对于女性的重新定义。安然这一角色的出现是必然的,当下时代所热捧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影视剧就会为迎合受众塑造什么样的女性,进而推动这一女性形象在社会的影响力,让女性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学习,最后实现“理想女性”到“女性理想”的转变,也就是“李宝莉”到“安然”的转变。
四、总结
随着时代的更迭发展,影视剧中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更突出女性主体意识和独立个性。影视剧中对于女性的塑造虽由“理想女性”发展到“女性理想”,但其本质没有变化,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还是依托社会“他者”对于女性角色的需求,不论是《渴望》中传统奉献的刘慧芳、《牵手》中自我矛盾的夏晓雪、《蜗居》中现代叛逆的郭海藻、《三十而已》中完美标杆顾佳,还是《我的前半生》中轻易成功的罗子君和完美闺蜜唐晶,都免不了“被看”的命运。影视剧中对于女性角色建构的流变,实际是社会变迁中男本位视觉文化对于女性一次又一次的定义。电视制片方和群体需求在影视剧和广告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是利用女性形象重新规范理想女性的问题,也是重新构造社会秩序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杨焕丽.国产电影中“女性意识”的存在性研究[J].戏剧之家,2019,(24):101+103.
[2]赵格然.浅谈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女性角色塑造[J].大众文艺,2018,(01):172-173.
[3]周怡.男权话语下女性抒写——再议电影《万箭穿心》中性别构建[J].戏剧之家,2020,(31):156-157.
[4]蒲剑.《我的姐姐》:女性议题的戏剧化表达[J].当代电影,2021,(05):15-18+2.
[5]郑炀.电影《我的姐姐》:“独立女性”的理想形象今何在?[N].中国艺术报,2021-04-16(007).
作者简介:
张云婷,女,汉族,甘肃定西人,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