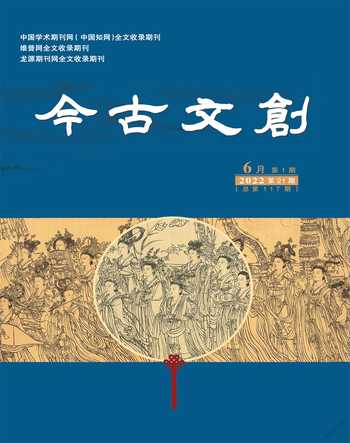十七年文学批评模式下的英雄情结 与性别表达的考察
【摘要】因处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十七年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上体现了显著的英雄书写范式。十七年是一个特别需要英雄的时代,十七年文学也是“英雄”形象丰产的年代。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特质,作家在英雄形象塑造过程中将人物“神”化和“去性别”化,同时英雄的情感特别是情爱的表达被压制到边缘状态,这成为英雄书写的一个弊端,使英雄形象成为高大却干瘪的“符号”,造成了人的异化。本文对十七年文学批评话语模式下的英雄情结的考察,目的在于研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英雄形象塑造特点,以便更清醒地关注“英雄”书写的未来。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批评;英雄形象;塑造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05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话语模式与英雄情结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显现了求新的、多元化的现代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局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1949年作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时间分界,从1949年到1966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这十七年,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的建设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于意识形态领域而言,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期通常会有政治强势话语对国家的各个领域的直接干预,正如福柯所说:“权力即话语”,这十七年,政治的强势话语也毫无例外的干预到了文学领域,通过在《文艺报》《文汇报》等党办刊物和各种文艺会议上展开大规模的文学批评活动,实现了对十七年文学创作的领导。正如葛兰西所说:“政治家的任务在于把人们发动起来,摆脱现今的际遇,成为有能力通过集体的行动达到既定目标的人,就是说,推动他们‘顺应’未来的目标。”[1]虽然文学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的创作以及文学的艺术性审美需求也与政治的强势话语进行了反拨,但最后都服膺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学批评形成了自身批评话语的关键词汇,如“两结合”“歌颂与暴露”“香花,毒草”“正面人物”“三突出”等。①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影响颇深的是“英雄人物”的创作讨论,十七年文学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形象,事实上,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要求写“新人物的新世界”,在1948年冬季召开的东北文代会上,就明确地提出了创作“新的英雄人物的口号”,同年在《东北文艺》上开展了“如何创造正面人物”的讨论,
有人认为新的英雄人物则是“一种完美的工人阶级活生生的英雄典型”,“应该是十全十美的”[2]。当时的川北军政治委员胡耀邦同志明确指出“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3],同时,在《文艺报》等文学刊物上也持续地开展大规模的关于“英雄人物”创作的讨论。参与批评的人员也由专业理论家扩展到工人领域。总结起来,当时文学批评话语模式下的英雄人物应该具有以下“英雄”特质,即是集无私、英勇、智慧于一身的带领广大群众历尽千难万险,最后成功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的工农兵形象。“英雄”人物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高大全”。在讨论过程中许多文艺理论家如冯雪峰、邵荃麟、康濯等人谈到两个问题:一是该不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二是该不该写英雄人物以外的“中间人物”。这两方面问题提出后都遭到了批判,认为: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的目的“是要向英雄人物脸上抹黑,要把英雄降格为‘不好不坏,亦好亦怀’的‘中间人物’,要把英雄人物‘非英雄’化。这是要抽调文学的革命灵魂。”[4]。
二、英雄“神”化与“去性别”化
在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英雄形象,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卢嘉川,《红岩》中的江姐,《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云涛,《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苦菜花》中的娟子,《风云初纪》中的李佩钟等。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十七年是特别需要英雄的时代,要通过“英雄”的“样板”来教育和引领人民。同时又有着历史书写的惯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语境以及深切的民族关怀下,英雄形象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褒扬英雄,矮化敌人也是作家书写的惯性,但在十七年文学中,对英雄形象的表达趋于极端。作家们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以“三突出”为创作原则,谱写了十七年文学“英雄主义”的畅想曲。事实上,由于主流话语:“英雄不应该有品质的缺陷,‘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发生动摇等”这都是革命不相容的[5]。在这种模式下,英雄被“神”化,一方面,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借鑒了传统用“侠”与“义”纵横全文的传奇化书写方法,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仅仅二十二岁,却是一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儒将,杨子荣是一位智勇双全,屡立战功充满传奇色彩的大英雄,特别是深入匪巢与座山雕斗智斗勇的故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中,以刘洪为大队长的“飞虎队”战士更是个个神勇,能自由地穿行在飞驰的火车上,是令人称赞的抗日英雄。另一方面正如李杨所说“现代性革命对个体而言是一种解放力量。革命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的神性色彩,这个层面上,神性体现为对世俗的超越……革命的神性力量使个体突破日常伦理的行为获得了直接通向终极的价值确认,进而使‘人称为神’”。[6]亲情、友情、爱情被这种神性本质所隔离,而似乎只有同志之情才是唯一高尚的情感,《红岩》中成岗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曾经担任市委委员、工运书记的许云峰的交通员,二人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半年后成岗被调离时对许云峰恋恋不舍,而老许很平静,怀着饱满的热情,道:
“不能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某个领导者的私人感情,这是危险的,会使自己迷失政治方向!你懂我的话吗?”
成岗的脸红了,他抬起头来,肯定地说:
“懂得,我一定改正。”
—— 《红岩》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47-48页)
批评话语模式下的英雄形象的另外的特征就是“去性别”化,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有意地隐去对英雄的性别表达,男英雄都是“禁欲主义者”,女英雄则具有了男英雄的雄性特质,如柳青《创业史》中当改霞主动向梁生宝表明心迹,等待梁生宝回应时,梁生宝面对自己心爱的改霞,克制住了情感:
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放纵感情的弱点……考虑到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他没有权力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的社会人!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744-745页)
同时十七年作品中女英雄形象的男性化表现在女英雄的动作,语言接近男性,模仿男性。王汶石的中篇小说《黑凤》是很明显的一例,小说叙述了“大跃进”时期,一位仅有二十岁,“干劲冲天”的黑凤姑娘如何闯入男性世界的故事,通过黑凤身上赶超英美的竞赛意识突出她的“阳刚之气”,语言、动作上带有明显的男性特征,作品中,三福老爹和换朝大叔因无法及时为“大炼钢铁”准备三千金劈柴而发生争吵,黑凤调节两人的矛盾时说:
“咱紧,钢铁上也紧,无论如何,天亮以前,要打法三千斤劈柴上路,十点钟送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不能让土高炉停下来呀!”
——王汶石(《黑凤》选自《王汶石选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当三福老爹提醒黑凤三秋工作也很紧时,黑凤说:
“天塌下来我顶着!”
——王汶石《黑凤》(选自《王汶石选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作者从三福老爹的视角描写黑凤夜里劈柴的动作:
三福老爹不由自主地向黑凤那边望去,月光下,他惊奇地看见黑凤那娇小的身影,拼着全身力气,抡着一把巨大而沉重的长斧,飞快地砍着,铁光闪处,碎屑的木片,爆炸似的向两边迸溅开来。
——王汶石《黑凤》(选自《王汶石选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在小说《苦菜花》中,女英雄娟子也有被男性化的叙述:像乱石中的野草,在苦难的岁月中倔强地成长起来的女英雄,她用“那激动的带着男音的声音”向姜永泉表示参加革命的决心,在一次受到敌人袭击时,她如女侠一样和敌人肉搏起来,最后将他制服,虽然受伤但却赢得了英雄的美誉。
女英雄的“去性别”化还体现出非女性角色的特点,不体现显示生活中母亲、妻子以及女儿的形象特征。将人的情感做冷化处理,如黑凤、娟子、江姐。她们的一切情感源于革命,如陈顺馨所言:“女性在面对家庭角色于革命事业,似乎被女英雄的雄化修辞所解决,事实上只是被简单的‘革命理想’简化或遮盖罢了……”[7]《黑凤》中黑凤在总路线和“大跃进”宣布时感动得流下泪来,人民公社成立兴奋得整晚睡不着,她自告奋勇地担任检察员这一职务,她是铁面无私的,动不动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指姓地批评那些小有缺点的人,或是把受批评者的姓名用大字写在村巷里的墙报上,第一个被她写上去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的妈妈。她在自己妈妈身上,开了第一刀。作者在塑造黑凤时弱化了女儿的角色,《苦菜花》中娟子的形象则弱化了母亲的角色,娟子以超人的毅力,在战地生下了女儿,但当她发现母亲的责任耽误她的革命事业时,她好像完全丧失了母性,要把孩子送人,甚至诅咒道:“都是你这小东西,害得人守在家里,你不早死了好。”并毅然地为刚满三个月的孩子断奶,走向了革命的工作岗位。此时的母亲角色已经完全让位于革命化的社会角色。《红岩》中在叙述江姐惊见丈夫暴死,头颅被挂在城楼上,却方寸不乱,丈夫老彭对于她首先是战友,其次是同志,最后才是丈夫,失去战友的悲痛远远超出了失去丈夫的悲伤。正是因为江姐具有了这种超凡脱俗的意志,她才能迅速地从丧失丈夫的悲痛中站起来,吐出心坎里的声音:“我怎能流着眼泪革命?”这些都隐匿了作为女性角色最敏锐的情感,使女英雄们阳刚有余,柔情不足,人物形象可敬却不可爱。
三、情爱边缘化与人性的异化
十七年文学由于受到政治强势话语的规范,文学创作也趋于表现宏大叙事,五四以来的关注个人的小儿女式的柔情被消解掉了,情爱更是成了稀有物质。与塑造英雄人物相反,当情爱成为英雄的禁区时,反面人物大多淫荡不堪,从《林海雪原》中的反面人物姜三膘子、蝴蝶迷、许大马棒,到《红旗谱》中的冯老兰诸多反面人物的淫乱生活的描写成为提升英雄人物道德标准的垫脚石。在十七年文学中值得一提的是《青春之歌》,作品成功地将“情爱”与“政治”有效地结合,《青春之歌》是以北大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这种情爱的叙事实际上远离了工农兵的时代主角,此中的情爱叙事被看作资产阶级的表现,《青春之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表现资产阶级成长的反面教材。后来,《青春之歌》因“不纯性”被划定为“毒草”,《林海雪原》也因为描写了少剑波与白茹的“情爱”被批判。
实际上,文学创作都会受到时代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作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为时代而写作。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发生期,就一度出现了“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在新文学创作初期作家在写作上的共识,该模式也曾风靡一时,但是到了三四十年代,这种模式便开始消失,确切地说是“恋爱”的消失,特别是在十七年文学中,“恋爱”更是被压制到写作的边缘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有“万恶淫为首”之说。十七年文学将英雄的个人性别表达压制在边缘处,而代之以宏大的集体叙事,英雄是无产阶级立场下的英雄,“情爱”则具有资产阶级倾向。在阶级分野下,情爱表达呈现出违背自然人性的一面。
文学却是人的文学,是要表现人与社会的,人有区别于非人的地方,即“人性”,而在阶级社会里“人性”被异化了,人性的异化指的是阶级社会本质的扭曲和变异。[8]文学作品应该有,对人的情感的表达,对人的关怀,对人生的揭示。十七年英雄人物的塑造虽然满足了为时代树立典型,为人民树立学习的“样板”的作用,但是“英雄”却缺少了“人性”,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的缺失导致了英雄人物的审美价值的缺失,政治强势话语抽掉了英雄的血肉,把英雄变成“高大”却“干瘪”的样板,英雄被異化成了符号,由于在创作中对人性的忽略,导致了英雄缺少了“人性”的丰富内涵。在此同时创作主体的创作个性和真正的审美批评也被压抑,这不能不说是对作家和批评家的伤害。十七年已经越来越远,但是“英雄们”仍留在文学历史的记忆里,他们身上的历史印痕还依稀可见,考察十七文学批评模式下英雄形象的表达,不仅仅是为了回溯历史,更是为了清醒地关注“英雄”书写的未来。
注释:
①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参考文献:
[1]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5-16.
[2][3]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41.
[4]赵锦良.邵荃麟同志为什么反对写理想的英雄人物[J].文艺报,1965,(12).
[5]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48.
[6]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190.
[7]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97.
[8]崔远志.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8.
作者简介:
张海静,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方向:文学批评、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