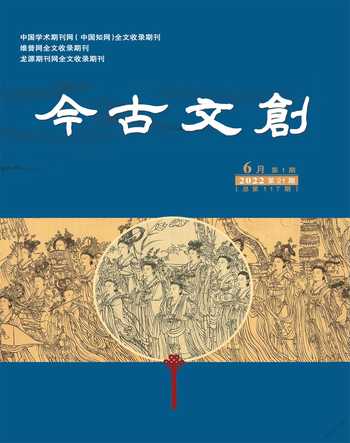论江淹《恨赋》《别赋》的悲怨基调
【摘要】江淹是南朝著名文学家,钱钟书称其文“俯视一代”。《恨赋》和《别赋》是江淹最负盛名的抒情赋代表作,一写赍志而殁之恨,一抒离愁别苦之情,体现出鲜明的悲怨基调。究其原因,既与江淹当时被贬吴兴县令的压抑环境有关,也有自身多愁善感的性格因素,同时离不开佛教苦乐观的影响。《恨赋》《别赋》,情景交融,并通过运用典故和概括典型的方式,将恨、别之情泛化为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从而引起读者共鸣,历经千载而传诵不衰。
【关键词】《恨赋》;《别赋》;悲怨基调;用典;典型;情景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08
江淹一生历经宋、齐、梁三朝,身处江山易代之际,特别在宋末齐初饱受政治打击,将悲怨之情发言为声,从而酿就六朝悲怨文学的惊世之作—— 《恨赋》《别赋》。
本文将结合江淹生平、创作背景、性格因素和佛教影响来研究《恨赋》《别赋》悲怨基调产生的缘由,并具体分析悲怨基调在两篇赋作中的文学体现,探讨如何辩证看待其悲怨基调的文学价值。
一、江淹生平与创作背景
江淹,字文通,宋州济阳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是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梁书》记载江淹“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在魏晋南北朝注重家族门第出身的社会环境中易受歧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江淹出身寒族的辛酸经历,也为以后他忧郁敏感的性格埋下了伏笔。年轻时,他在宋建平王刘景素手下任幕僚,因广陵令郭彦文一案受牵连而下狱。江淹以饱蘸悲愤与真挚之情的笔墨写就《诣建平王书》,感人肺腑,终于得到刘景素的宽慰而被释放。然而好景不长,后来刘景素密谋起兵造反,江淹屡次劝谏无果,在元徽二年被贬为建安吴兴县令。身处荒僻偏远的“江南瘴疠地”,与外界沟通较少更是“逐客无消息”,迁客骚人被贬到偏僻荒凉的南方湿热之地,自然有一腔忧郁亟待抒发。再加上被贬期间丧子别妻的经历,又使得江淹遭遇了生离死别的痛楚,政治失意与亲故零落的双重打击,让他的内心饱受折磨,从而将悲怨之情倾泻于笔端。
从外部客观环境来看,江淹早年的政治生涯屡遭坎坷,甚至经历牢狱之灾,再加上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又与亲人阴阳两隔,更容易激发他内心的愁苦抑郁。《恨赋》《别赋》写于江淹被贬期间,他将内心的愁苦抑郁诉诸文笔,以此消解愁闷。《恨赋》抒发赍志而殁、心愿难以实现便与世长辞的遗憾以及对死亡无法回避的悲恨,《别赋》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人世间不同情景下分离的哀怨无奈,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可见命途多舛、仕途不顺的现实刺激是诱发他悲怨之情的直接原因。
从内部主观因素落笔,江淹多愁善感的性格、忧国忧民的气质,也是他文章多悲愤哀怨的重要原因。《自叙传》记载:“长遂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于文章,所诵咏者,盖二十万言。而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
由此可知,江淹年少学识广博,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他渴望像司马相如一样凭借赋作得到君王赏识乃至名垂青史,钦佩东汉名士梁鸿忧心国事而挥笔写就名作《五噫歌》。这反映出江淹志向远大,深受儒家忠君爱国、匡世济民思想的影响,骨子中沉淀着忧国忧民的文人气质。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纵有鸿鹄之志却在坎坷仕途中被束缚了羽翼,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自然更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忧郁敏感。
除此之外,《恨赋》《别赋》的悲怨色彩也与佛教苦乐观的影响有关。江淹在《自叙传》中说自己“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可见他思想深处笃信佛教,从江淹的诗文也可以窥见他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如《伤爱子赋》的结尾写道:“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愿同升于净刹,与尘习兮永弃”,江淹从丧子之痛中超拔出来,明白今生的果报牵连于前世的因缘,祈求死后与儿子在佛国净土相见,超脱于红尘俗世之外。江淹借佛家的因果轮回观念来自我开导,从而对人生有了较为通透清醒的认知,而往生净土的心愿则反映出他对于生命终极归宿的思考。
佛教认为人生无常,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苦难,比如四集谛中的苦谛包含着人生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恨赋》《别赋》便写尽了其中的死苦和爱别离苦,并对于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加以铺排,可能也是受到佛教经文中多有归类、铺陈的影响。《恨赋》《别赋》对人生面临死别与生离的各种情景进行了铺张渲染,不仅仅是个别人的恨与别,而是站在超拔于人世间的高度俯瞰古往今来的一切恨与别,具有普遍性,更渗透着人世无常的玄思意味。
然而江淹在中年以后平步青云、仕途顺畅之际,“晚节才思微退”。《诗品》记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人生遭际的转折,江淹晚年安于享乐,常云:“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缺乏忧患意识,江淹便很难写出《恨赋》《别赋》这样极尽悲怨之情的惊世骇俗之作,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江郎才尽的结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也侧面反映出《恨赋》《别赋》之所以富有艺术感染力恰恰是“文穷而后工”的体现。
二、悲怨基调在《恨赋》《别赋》的体现
曹道衡先生认为《恨赋》所写的主要是人生短促,有志难伸的痛苦;《别赋》所写的主要是离情别绪和背井离乡的悲伤。当然,两篇赋作都饱含悲愤哀怨之情,极尽悲怨之致。《恨赋》《别赋》的悲怨基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江淹长于运用典故,既有历史人物的事典,也有借鉴前辈诗赋而援引、化用的语典。一方面是由于江淹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对古籍中的典故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长于模仿又能融会贯通,化用典故如自己出。
在《恨赋》中,他引用秦始皇、赵王、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等人的事典,一连串的历史人物层出不穷。秦始皇壮志未酬之恨,赵王国破家亡之恨,李陵含冤受辱之恨,昭君客死他乡之恨,冯衍有志难伸之恨,嵇康世道难容之恨,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所恨之事各异,但是遗恨之情的本质何其相似!字里行间充满着历史兴亡、人世代谢的沧桑之感,作者更吊古伤今,借古人之事抒发自己心中绵绵无尽的悲怨,深化悲情,哀感久绝。《别赋》写“暂游万里,少别千年”运用语典,化用鲍照《代升天行》的名句“暂游越万里,少别数千龄”如自己出,笔墨中一抹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萦绕其间。
江淹不仅在赋中多用典故,他的诗歌中也不乏典故,比如《杂体三十首》。他的三十首杂体诗,每首诗追忆一位历史人物,既有不得君心的边将,又有忧闷抑郁的士子,还有怡情洒脱的文人,人物各不相同。比如《李都尉从军》一诗结尾写道:“袖中有短书,愿从双飞燕”,与《恨赋》“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抒发了不被君王理解的苦闷之情,可见江淹诗、赋中的典故相互关联。
第二,江淹还善于列举典型以概括出不同类别的恨、别之情,并通过典型来表现一般,从而将个人的感情泛化至人类普遍、共同的情感,引起读者共鸣,加深了艺术感染力。
《恨赋》中秦帝、赵王代表了一般帝王诸侯或成功或失败都终归一死的悲叹,其余四者代表了知识分子有志难伸、壮志难酬的满腹愁怨。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李陵假装投降实际上伺机报国,投降只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却被汉武帝误解而满腹冤屈;王昭君不得君王眷顾只能远嫁边塞,从香草美人的传统而言,以男女来比附君臣,影射君臣隔阂而造成知识分子的失意苦闷;冯衍“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埋没乡野,郁郁而终;嵇康清高孤傲却为黑暗的世道所不容,在《广陵散》的凄凉琴声中走向死亡。清代许梿说:“至分段叙事,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见证了古往今来无人能逃脱死亡而终究饮恨而逝的残酷事实,正如《恨赋》的结尾所言:“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恨赋》的姊妹篇《别赋》则从显官达贵、豪侠壮士、从军征夫、去国羁臣、宦游夫妇、方外之士、男女情人等七个典型,极力铺陈描摹离别的各种情景,写尽离别之悲,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然离别之人、事、景各不相同,但是离别的主题却有共通性,所谓“别虽一绪,事乃万族”。离别是人世间的普遍现象,而由分离所生的愁怨苦痛也是离情的本质所在,“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
第三,江淹善于移情于景,情景交融,他筆下的景物浸染着悲怨凄凉的冷色调,客观景物其实也是他内心幽怨悲凉之情的投射。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诗词如此,文章亦然。
比如《恨赋》开篇写景:“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坟墓上荒草枯木的凄凉之景如在目前,渲染了一种萧瑟幽冷、阴森可怖的氛围,使人不觉联想到死亡,从而为后文“仆本汉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埋下情感基调。又如“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极写边塞异域狂风大作的昏暗景象,连大雁都踪迹难寻,更何况人迹罕至!以“陇雁少飞”暗示边塞与中原相距遥远,以雁象征思乡之愁,以哀景写哀情,情景交融,衬托出王昭君久居塞外的孤寂忧伤之情。
再如《别赋》写恋人分别: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春天的景色本是明媚而生机盎然的,然而在即将分离的情人眼中,即使是清澈的湖水也染上一层悲情,即使是青葱的草色也如“记得绿萝裙,处处怜芳草”一般,隐含着少女迢迢不断的思念。此处移情入景,情景交融,刻意勾勒出一幅送别的春色图来渲染情人内心的伤感之情。明月皎洁,露珠莹润,如此良辰美景却不能长相厮守,只能在时光匆逝、岁月流转中坐愁红颜衰老,怎不令人泣下沾襟!此处以乐景衬哀情,倍增其哀,更显出悲怨之深,思念之切。
从春日离别到秋夜思念,春秋轮回间不觉辜负了韶华,憔悴了朱颜,更惹人感伤忧郁。这段文字运用了一连串的颜色和比喻来细致具体地描摹景致,引起丰富的视觉联动,容易触发读者内心的真切感受。王林的《六朝辞赋史》引用明人张文光的“布景淋漓,写情透彻”八字概括江淹辞赋的艺术特色,颇为精妙。
江淹《恨赋》《别赋》将抽象的情感作为描写对象,通过运用典故与概括典型将个体的情感泛化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又以华丽辞藻精细雕镂出尽显悲情的景色,情景交融,从而深刻表现了悲怨基调。
三、辩证看待悲怨基调的文学价值
江淹的《恨赋》《别赋》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情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面临无法避免的死亡与分别时的悲怨之情,容易激起读者心中剧烈的情感起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令人凄神寒骨,久难平复。过度渲染悲观消极的情绪,也不利于读者积极乐观、健康向上思想的培养,这似乎是其白璧微瑕之处。
然而,把这两篇赋作放于六朝时期朝代更迭的战乱背景中,同时联系作者下狱遭贬、亲故凋零的坎坷经历,再加上作者本人敏感多愁的性格,乃至受到佛教苦乐观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其悲怨程度缘何如此之深了。
诚然,《恨赋》《别赋》的悲怨基调,是那个时代文人失意的集中体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朝时期文人的部分精神风貌。
虽然这两篇赋作不是将离愁别恨题材纳入辞赋的首创,早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已有“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感叹,但确实是将悲怨之情发挥到极致的离情赋名作。
以往的汉大赋多以具体事物为描写对象而很少专门刻画情感,《恨赋》以抽象的遗恨之情为描写对象贯穿全文,《别赋》则侧重渲染离别带给人的哀愁之情,二者都体现了对于情感描写的高度重视,是对辞赋题材的拓展。二者都将抽象情感铺展到不同的情景、人物类型之中,将汉大赋的铺叙手法融入抒情小赋的情感渲染之中,并借鉴了《七发》的分类铺写,从而促进辞赋的发展。
《恨赋》《别赋》一扫齐梁绮靡浮艳的文风,注重抒发真情实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齐梁文学在浮辞艳藻之下,尚蕴含着“新变”的因素,也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所影响。《恨赋》《别赋》所表现的死之遗恨与生之伤别,并不是单独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是人类共有的普遍情感和永恒主题。这两篇辞赋通过一个个典型的人物与情境,揭示其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的遗恨与伤别,从而折射出恨与别在人世间的普遍性与共通性,深化了情感意蕴,又渗透着哲理思维。二赋风格华而不靡,以情动人,在南朝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对于《恨赋》《别赋》的悲怨基调,应以辩证的眼光、理性的思考来面对,既要看到其情感过于悲观消沉的不足之处,但也不能拘泥于偏狭一隅,更应重视其在文学史上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看到其所传达的恨、别情感之普遍性,将多方面结合而不失偏颇,才为明智之选。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南史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965.
[2](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6354.
[3](南朝)钟嵘.诗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184.
[4]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6:246.
[5](南朝)江淹著,(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6]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4:44.
[7]王琳.六朝辭赋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238.
作者简介:
贺潇莹,女,汉族,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