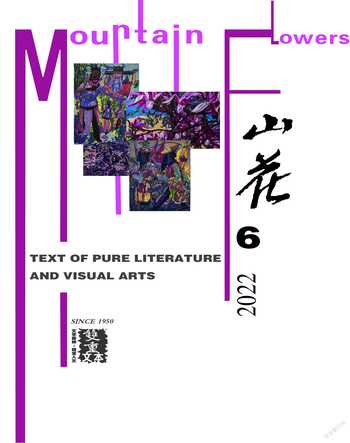时光鲜美
盛慧
我酒量不好,平时却喜欢和朋友们小酌几杯。只要一喝酒,我就立刻变成了一个顽童,总会和妻子打游击,妻子不让我喝太多,我总是趁她转身之际,一口把杯中的酒干掉,又飞快地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潮汕话有句俗语叫:“茶三酒四踢桃二”,意思是茶最好三人同喝,酒最好四人同饮,游玩最好是两个人。同样一瓶酒,一个人喝是苦的,一群人喝却是甜的。喝酒讲究氛围,在所有写酒的古诗中,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最有意趣,最令我向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夜晚在寒风的席卷下款款而至,行将到来的大雪使每一座房都成了孤岛,寒冷的屋子慢慢被热情的炉火烤暖,新酒的香味挑逗着味蕾,喝上几杯之后,便会生出微醺的感觉,这是最美妙不过的事情了。
在我看来,佐酒之物,最好的不是花生米,而是卤菜,卤菜又以潮州为佳。香港美食家蔡澜常用普宁炸豆干来判断一家潮州菜馆的品质,我则用卤菜来衡量。卤菜是硬指标,卤菜不好,其他的菜也就不用再试了。
这或许与我小时候的一段美好记忆有关。 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在镇上卖卤菜的,有一段时间,他家的灶台翻新,便到我家来做卤牛肉,从每天凌晨三点一直忙到五点。我起床做早餐的时候,总会发现汤里有两三块拳头大小的牛肉,这是他故意剩下的。我欣喜若狂,直接用筷子叉着,咬一大口牛肉,喝一口粥。这是极美好的事情。我希望他家的灶台永远不要修好,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吃到卤牛肉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一个星期以后,他家的灶台修好了,我的美好生活也随之结束了。
中国人爱吃卤水,卤水江湖,门派众多,各有所长。川式卤味麻辣辛香,山东卤味咸鲜红亮,我们老家的苏式卤味鲜香回甜,而潮式卤味选材讲究,味甘香软,浓而不咸,清而不浊,馥郁醇香,回味悠长,吃再多也无厌腻之感,堪称“人间至味”。
潮州卤菜令人百吃不厌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卤水,汪曾祺先生对潮州菜的评价甚高,他曾给潮州菜馆题过一幅字——“桂林山水洞,潮菜色味香”。在我看来,潮州卤水就是色香味俱佳的典范,它的制作极其复杂、严苛、精微,堪与香水调制的过程媲美。潮州卤水中的用料皆出自自然造化,一粒味精都不能加,因为这与“清而不浊”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卤水是长情的东西,要日复一日地煮制,如果加入味精,或许可以得一时之鲜,但却会坏了一整锅卤水,得不偿失。在调味品泛滥的时代,这样的坚守极其可贵,甚至还有些悲壮。潮州卤水为什么卖得那么贵,我想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
我的大姑妈,前半辈子走南闯北,风光无限,她平生最恨味精,一说到味精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记得小时她经常对我说,味精是骗嘴巴的东西,还说,如果什么菜都加味精,还要厨师干什么?以前,我对她的观点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她太过偏激,因为,放了味精的菜,就是比不放味精的好吃啊!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发认同她的观点了。你或许会问,怎么才能知道菜里有没有加味精呢?其实很简单,吃完饭之后,你觉得喉咙发干,不停找水喝,那菜的鲜味大抵就是味精调出来的。
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开卤水的第一步是革汤,革的不是一般的高汤,而是顶汤,我把顶汤称为卤水的“身体”。一般人认为,高汤只有一种,而在厨师界,高汤其实是分为三个等级的,分别“顶汤”“上汤”和“二汤”,其中,又以顶汤最为鲜美,最受推崇,被尊称为“龙之睛、鸟之羽”。它的鲜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食材“众筹”而成的,浓郁、醇厚,富有层次感与幽深感,其海鲜味以烤制过的大地鱼和瑶柱带出,风腊味由金华火腿带出,鲜肉味以老母鸡、猪筒骨和梅肉带出,还有猪皮和鸡爪,增加卤水细腻绵滑的胶质。此外,还要加入大量的鹅油,鹅油的作用非常大,它不仅仅可以增香,在卤制的過程中,还可以减少热量散发,使食材更加易熟,保持细嫩脆爽的口感;卤出来的食物,穿着鹅油的薄衣,也会更油亮悦目,清香醇滑。鹅油冷却后,又可以形成一层自然的保护层,使卤水的香味得以封存,不让这些“淘气”的香味到处乱跑。
开卤水的第二步是调香,潮州卤水的风味,与他处迥然不同,其中,最特别的两种香料是南姜、香茅。南姜又叫“潮州姜”,又叫“芦苇姜”,由东南亚传入,在泰国叫“暹罗姜”,是冬阴功汤中必备的材料,它具有桂皮香味,味道辛辣。香茅又称“柠檬菜”,是越南菜、泰国菜中最喜欢添加的香料,法国肝鹅中也会加入,将它加在卤水中,可使香味变得空灵而清新,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此外,还有白豆蔻、干辣椒、八角、砂姜、草果、罗汉果、香叶、黄栀子、白胡椒、桂皮、花椒、蛤蚧、陈皮、甘草、丁香等,每一样香料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或去腥、或增香、或生甘、或调色,个个“才华横溢”,没有一个是“吃闲饭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蛤蚧,它不仅可以防止卤水酸败,还有补肺益肾,定喘止嗽的作用。这些香料品性不一,有些比较内向,需提前炒制,炒出浓郁的焦香;有些性格比较外向,不用炒制,就已香气四溢。这些萍水相逢的香料们,相互提携、相互融合,最后成为引人入胜的幽香,我把这种纯净、迷人而又深邃的幽香称为卤水的“气质”。
开卤水的第三步是调味,这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担当大任的是潮汕本地生晒的生抽和琥珀色的鱼露,还要加蒜头和干葱头,大蒜头不剥壳,红葱头则一定要爆香。鱼露又称“鱼酱油”,是以小鱼虾为原料,经腌制、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极为鲜美的汁液。潮汕地区最早的鱼露,其实是指腌制咸鱼时排出的鱼汁。本地人也将这种鱼汁称为“醢汁”,将腌制的海产品称为“咸醢”。“醢”的意思是用肉、鱼等制成的酱。清光绪《揭阳县正续志》这样记载:“涂虾如水中花……土人以布网滤取之,煮熟色赤,味鲜美,亦可作醢。”鱼露为咸鲜之物,和咸菜、菜脯并称为潮州三宝。凡事有度,过犹不及。鱼露虽美,但切不可贪多,多则发苦,反而弄巧成拙,一般而言,五斤汤中加入半瓶即可。生抽是颜色较浅的酱油,有浓郁的酱香和酯香,潮菜大厨们认为,酱油是卤水的灵魂所在,酱油不好,其他都是白搭。他们一般会选用揭阳当地生产的传统酿造的生抽,这种生抽酱味醇正,醇厚柔和,具体有三香,即“头香”“体香”“尾香”,是配制的酱油远远无法比拟的。几者的结合使卤水味道本真、温和、隽永、持久,我称这种自然朴拙的味道为卤水的“性格”。
最后一步就是调色了,这决定了卤水的“颜值”。很多地方的卤水会直接加入色素,使其色泽艳丽,提升卖相,潮汕厨师则遵循古法,加入冰糖炒制的糖色,也可加黄栀子,但切不能加老抽,因为,老抽中加入了焦糖,熬多几次以后,卤水会又黑又苦,不堪重用。调完色后,天下一绝的潮州卤水便已大功告成,色泽金红,沁人心脾,香得几乎让人忘记了呼吸,让人有喝上一大碗的冲动。
这卤水几乎汇集了天地精华,不管是卤鹅肉、鸭肉、五花肉、猪头皮、大肠、猪嘴、猪耳朵、猪舌、猪脚,还是豆干,甚至是萝卜片、苦瓜,只要在其中洗礼过,都能成为令人垂涎的倾城美味。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把脚上的皮鞋放进去卤上几个小时,都能变成一道美味。
当然,美味永远没有标准答案,卤水的方子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家酒楼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配方是最高机密,对外秘而不宣,而这种口味的差异与变化,正是潮州卤水的魅力所在。
除了配方,卤水桶也有讲究,总的来说宜大不宜小。我的一个朋友新开了间潮菜馆,客人对其他菜式的评价都很高,唯独觉得卤水还差点意思,朋友百思不得其解,四处请教,一无所获,后来,偶遇一高人,天机方被道破,原来就是因为卤水桶太小,香味散发不出来,换上大桶之后,果然非同凡响。
卤过的卤水,称为卤胆,需要小心保管,因为,卤水和白酒一样,也是时间的艺术,越陈卤出来的肉便越加沉厚香醇。卤水的香味是肉养出来的,因此,每天要用肉喂卤水。老卤水滴滴香浓,非常精贵,坊间就有“一桶卤水一桶金”和“千金难换老卤水”的说法,我听说有些鹵水店,怕人偷走,每天晚上都会把卤水桶锁起来。
很多人以为,卤味的制作,就是把所有的食材一股脑儿全放进去,其实不然,要根据食材的特点来确定卤制的程序和时间。比如,卤鸭要先在油锅中煎炸,去其膻味;又比如,卤水豆腐擅长吸味,要先炸至表皮金黄,待冷却后浸入卤汁,一般要放到最后卤,浸十分钟即可,太久,则咸。豆腐的表皮绵软,内里滑嫩。粤菜大师潘英俊说卤水豆腐里有炖蛋的香味,我细细品尝,还真是那么回事。
与其他地方的卤菜相比,潮州卤菜的口感香软,老少咸宜,这是与潮州尊老爱幼的传统密不可分的。有一个潮汕的朋友就告诉我,他们家里每次煮好东西,总会先想着奶奶能不能吃。这份美德,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之中,成了文化的基因,世代相传。
“打冷”这个词,最早起源于香港。20世纪50年代,香港地区有潮汕人卖夜宵和卤味,他们挑着箩筐沿街吆喝“担篮啊”,声音拉得老长老长,外人听不懂潮州话,久而久之,“担篮”就变成了“打冷”。
在打冷的菜品中,最让我留恋的是生腌。潮汕人喜食生腌,并称其为“潮汕毒药”,意思是一吃就会上瘾,一辈子都休想戒掉。有人曾开玩笑说,某人得了痛风,第二天还要拄着拐杖去吃。
潮菜素来讲究食材,生腌则更甚。将食材处理干净后,放入酱油、芫荽、姜、蒜头、白酒等制成的腌料熨之。食材不同,大小各异,腌制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比如,三眼蟹要腌十几个小时,时间太短,不入味,则腥,时间长了,肉质也不佳,当地人称为“涝肉”,软绵绵的,没有弹性,活活糟蹋了好东西。即使端上桌后,味道也是在变化之中的,最好一上桌就吃,时间一久,咸味加重,鲜味会随之消散。
生腌的品种很多,爆膏的三眼蟹和野生红虾是我的最爱。
红虾由白酒和醋腌制,吃的时候有果冻的感觉。入口是极温柔的,如同少女的舌尖,鲜美的味道围住舌头,如涨潮时海水从四面八方漫过小岛。可以直接吃,也可以蘸酸梅汁,潮汕人有生腌游过酸梅汁的说法,我试了一下,的确不同凡响。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到过冻蟹:“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而食。”大多数食物,热的比冷的好吃,但红蟹例外。红蟹壳薄肉甜,但肉质相对松软,含水量大,口感略逊,冰冻后食之,方为佳美。为避免蟹脚脱落,要先冻后蒸,蒸熟之后,自然冷却,再放入冰箱,先冷藏半个小时,再急冻十分钟,迅速锁住蟹肉的鲜味。冰镇的时间尤为重要,它会直接影响蟹肉的口感。本港出产的红蟹美艳动人,身上有十字架印记,极具诱惑力,好像刚从大海里爬上餐桌一般。剥开蟹壳,艳红的蟹膏,光芒四射,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冻过的红蟹,肉质坚实、清甜甘香,有大海的气息,点姜米红醋,肉质更甜,吃上一口,甜美的味道在身体里四处奔跑,令人愉悦。红蟹四季皆有,但以初春时节最为肥硕,大小也适中——并非越大越好,三斤左右的红蟹味道最鲜美。
潮汕人还喜欢腌血蚌,只在滚水中烫半分钟,水中开始冒泡就捞起来,这时,蚌壳微微开启,蚌肉半生不熟,最为鲜甜。他们认为,血蚌的血是最美味的,吃得酣畅淋漓,一个个都成了“血盆大口”,外地人看起来有点恐怖,但他们却觉得滋味无穷,吃得乐不可支。
“鱼饭”也是打冷的妙品。这里的鱼饭,不是鱼加饭,而是以鱼为饭,最初是渔民们在船上的食物——当然,他们只吃最便宜的鱼,精贵的鱼是要到岸上换钱买米的。
潮汕地区以前聚集着大量的疍民,据《潮阳县志》记载:“东晋隆安元年已有人家渡海至达濠,以煮盐捕鱼为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作《蜑户》曾这样写道:“天公分付水生涯,从小教他踏浪花。煮蟹当粮那识米,缉蕉为布不须纱。”
旧时,没有冷藏技术,潮汕地区的渔民对于渔获的处理一般有“一鲜二熟三干四咸五腌”几种方法。“鲜”是趁鲜贩卖;“熟”是煮成鱼饭;“干”是晒成鱼干;“咸”是制成咸鱼;“腌”则是腌成鱼鲑或鱼露。
渔民们最传统的鱼饭做法,是将鱼打捞起来后,不开膛,也不去鳞,直接把这些活蹦乱跳的鱼用盐水煮熟,盐水浸渍的过程,也正是鱼肉甜度渗出的过程。现在,鱼饭做法已经有所改良,开膛,但仍不去鳞。潮州人认为,鳞可以保护鱼肉的鲜味。鱼的鲜味是最珍贵的,但它又像是水中的月亮,是极其脆弱的,一经油炸,便会泄白,只有以盐水煮之,才能存其本真的鲜甜。
和所有的菜式一样,食材的新鲜程度决定了鱼饭的品质,鱼一出水,鲜味就会开始消散。潮州话里就有一个词叫“就涝”,是顺着涨潮刚刚运回来的意思,因此,制作鱼饭是需要和时间赛跑的。现在已经不用海水来煮鱼饭了,而是在打捞之后,立刻冰镇锁鲜。运上岸上,将鱼头尾相交,排列成花环的形状,放入疏眼竹箩之中,再用盐水煮之。煮完之后的盐水不能倒掉,它就像老卤水一样珍贵,盐水越老,煮出来的鱼鲜味越浓郁,越纯正。
鱼饭的品种很多,主要有巴浪鱼、花仙、乌头鱼、秋刀鱼、青鲈鱼、黄墙鱼、红鱼、吊景、阔目鱼、姑鱼、迪仔鱼、那哥鱼、红鱼、红心鱼、竹签、大眼鱼、马面鲀、马鲛、南昌鱼、海鲈、扒皮鱼、乌尖鱼、红方鱼、银鱼仔等……每一种鱼的口感和味道,都是有差别的。巴浪鱼是最常见的,表面青蓝,肉质紧实,久煮之后,特别有嚼劲。秋刀鱼脂肪肥厚,肉质坚实,与巴浪有些相似,但体型比巴浪更加修长。鹦鹉鱼比巴浪鱼、花仙鱼肉质更细腻。红杉鱼鲜甜味美,红花桃(又叫梅童鱼)色泽比红杉鱼艳丽,像化了浓妆,准备去约会的女孩一样,其肉嫩刺软,肉味鲜美,口感更佳。海鳗是海中的运动健将,肉质脆爽,弹韧腴美,香煎最美。乌头鱼,肥美丰腴,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那哥鱼,外表丑陋,肉质细腻甜美,但刺很多,让人又爱又恨。斗仓,又叫白仓,身体银白,呈菱形,肉多脂多,主要活动于近海与深海之间,因此,肉质鲜嫩,甘香无比,它深受推崇,价格也较高。
鱼饭的灵魂是普宁豆酱,潮汕人吃鱼饭,一定是要蘸此物。每一种鱼的口感与味道不尽相同,但相同的一点是,吃完之后,满嘴都是鱼肉本来的鲜甜之味,好像那鱼在嘴里复活了一般,那种不加修饰的纯真鲜美,是最珍贵的,也是最打动人的。
鱼饭可冷可热,我个人觉得,最好还是“打冷”,这时,鱼肉紧致,鲜味凝聚,尤其是撕开鱼皮时带出的那一层晶莹剔透的性感鱼冻,鲜美撩人。以鱼饭佐粥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了,不绝如缕的鲜味的涟漪在粥水中晕开,那种美妙的感觉,如梦似幻,仿佛进入了仙境。
鄉音与小吃,是最能引发游子的思乡之情的。在所有的食物中,没有一种食物比小吃更能让游子们牵肠挂肚,更能抚慰他们漂泊的肺腑了。
因为当了潮州婿仔,成了半个潮州人,所以,对潮州的小吃也就格外关注一些。潮汕地区,小吃众多,最让我眷恋的是猪肠胀糯米、蚝仔烙和普宁豆干。
猪肠胀糯米,有的地方叫猪肠酿糯米,我倒觉得还是“胀”字比较生动、妥帖,刚出锅时,它胖乎乎的,圆滚滚的,像一头头吃饱的小猪崽,懒洋洋地躺在盘中呼呼大睡,甚是可爱。
制作猪肠胀糯米,需取猪大肠中段洗净,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需用白醋反复搓洗,将异味去除殆尽。糯米要先浸五个小时,时间不能太短,当然,也不能太久,否则米会发酸,影响口感。配料中的猪肉,不是一般的猪肉,而是猪脸肉,肥而不腻,久煮之后,能产生黏稠的胶质,产生滑爽的口感。将猪脸肉、香菇、虾、莲子等辅料切碎,炒香拌匀,调入食盐、味精、胡椒粉等调味品,填装入洗好的猪肠中,八成即可,千万不能装得太满,因为糯米煮熟后,会发生膨胀,撑破猪肠,当然也不能太少,太少,则不饱满。吃的时候,一般斜切片,撒花生碎。同在潮汕地区,口味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普宁人喜欢蘸甜酱油,汕头人则更喜欢蘸桔油。
配汤也很有讲究,除了用猪肚、猪小肠等猪内脏熬煮的高汤外,还有当地颇有名气的“猪小肚胀猪脑”,就是把猪脑塞进猪小肚中,两头扎紧,在高汤中煮熟之后再用刀割破猪小肚让猪脑流出,放进碗中加满高汤,咸菜切粒,放于碗底,撒点胡椒粉调味,既爽口又解腻,这汤,本身就是一道绝品。我总觉得,一道小吃用这样的配角,实在过于豪奢了。
潮汕地区的猪肠胀糯米以普宁洪阳最有名,那里就是我妻子的老家。在普宁洪阳又以洪阳新街电影院旁的方春亮出品最为正宗,因方春亮在家中排行老大,因此,洪阳本地人都称“老大家的猪肠胀糯米”。方春亮经营了三十多年,他所用的那把钢刀,刀身只剩原来的一小半了,足见生意之火爆。
如今,档口已由方春亮的儿子和儿媳接手。据他的儿媳介绍,起初,方春亮家很穷,为了改变这种境遇,他便想到恢复这一失传的手艺,他每天买一根肥肠回来试验,不断地改进,最大限度地接近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调制成功,一经推出,便深受欢迎,每天早上十点左右开档,下午一点不到,就可以收档回家了。
猪肠胀糯米口感十分松软,浓郁的米香,若有若无的猪肠味道,香黏可口、糯香四溢,香味缠绕,经久不散,我妻子对此物情有独钟,每次回去,都要一试为快。
对于一般的食物,贪吃那叫馋,而对故乡的食物,贪吃便是深情了。妻子每次回娘家,都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不好好吃饭,因为街上的小吃实在太多了,几乎天天都在开美食节。蚝仔烙是必定要去打卡的。蚝仔烙一定要现点现做,制作起来并不复杂,但要做好,却又十分讲究。其主要食材是蚝仔、鸭蛋和番薯粉。蚝仔要选圆滚滚、胖乎乎的本港珠蚝,以饶平汫洲出产为上,但并不是越大越好,一厘米大小最佳,黑耳白肚,颜色对比越强,越是新鲜,鲜甜、柔软,也越是无渣、易熟。生蚝只要用水稍加冲洗即可,如果反复搓洗,鲜味就流失了。制作蚝仔烙,蛋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地方用鸡蛋,有的用鸭蛋,最传统的还是后者,因为鸭蛋有小小的腥味,反而可以激发出蚝的鲜味。番薯粉最好选用乡下农民自晒的,和水的调和比例大致是一比三,中间绝对不能加入其他粉,否则会影响口感。烙好过之后的番薯粉,呈半透明状,不仅有细滑的口感,还可以让藏在中间的蚝仔若隐若现,它们就像可爱的孩子露出一只只好奇的眼睛。
“冬至到清明,蚝肉肥晶晶”,这说的是吃蚝仔烙的最佳季节。制作蚝仔烙要用平底锅,先煎鼎淋油,再煎蚝仔,后拌薯粉,最后再浇蛋浆,伴随着滋滋作响的美妙声响,香气四散,让人大吞口水。喜欢香口的,可以煎久一点,金黄的脆边,像滚了蕾丝一样,吃的时候,外脆内嫩;喜欢柔软的,煎的时间可以短一点,保持半透明的感觉,撒一点胡椒和香菜,吃的时候点少许鱼露,胡椒和鱼露,(这些都是这道美食最鲜美的伴奏),可以让鲜味更加浓郁、绵长、飞扬。相较而言,我更喜欢脆皮的做法,表皮金黄松脆,像行走在晚秋铺满落叶的小径,蚝带脆爽,蚝肉方熟,肥嫩多汁,滑腻鲜美,每一个都是鲜美的小炸弹,每一口都有爆膏的惊喜,它们在嘴里融化,那种鲜甜久久地萦绕舌尖,肥美如同鹅肝,真叫人没齿难忘。
卖蚝仔烙的档口,总是人满为患,几乎每次去都要排长队,等待的人大多是回家探亲的游子们,这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是他们在异乡日思夜想的美食,对他们来说,不吃一口家乡的蚝仔烙,就等于没回家。
澄海盐鸿坛头村盛产蚝,进入村中,家家户户都在撬生蚝。这里至今还流传着一个“罚贼食蚝烙”的故事,说当地请了一个老先生来教书,乡人都很敬重他,煎了蚝烙给他吃,他吃得太多,吃怕了,一见到就起鸡皮疙瘩。有一天,村里捉到了一个小偷,这是个屡教不改的惯犯,大家问老先生怎么处置,老先生居然说罚他吃蚝烙。众人甚为不解。那小偷开始吃得很开心,吃到肚子滚胀,老先生仍然不准他停下来,让他痛不欲生,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后来,那小偷果然改邪归正了。
除了蚝仔烙,潮汕地区常见的还有九肚鱼蚝烙、秋瓜烙、金瓜烙和厚合烙,各具风味。九肚鱼也叫豆腐鱼,鱼肉极细嫩,制作之前,先要将鱼刺挑尽,烙过之后,口感一流,虽没有蚝仔烙那般有名,味道却毫不逊色。秋瓜,就是水瓜,它有着浓郁的清香,瓜汁十分养颜,在潮汕地区有“美人水”之称。烙之前,要将秋瓜切段,不停搅拌,搅出瓜汁;烙过之后,清鲜软滑,甜滋醇香,金黄透绿,甚是惊艳。金瓜就是南瓜,有咸甜两种做法。甜口的,将金瓜切细条,加入冬瓜糖、白糖,最后放炸香的花生,裹上生粉;咸口的则要用到虾、芹菜、花生,并以鱼露调味,在油锅中炸至金黄,因为南瓜本身就是金黄色,所以,炸出来颜值很高。我喜欢甜口,吃起来,香酥甜沁,口感甚似萨其玛,但甜而不腻,也不粘牙,是南瓜最好吃的一种方式。厚合是一种好意头的菜,潮汕人认为它有“和和美美”的意思,其叶硕大,十分粗生,以前主要用来喂猪,因此被称为猪菜。制作时,先焯水,切细丁,再将花生炒香、捣碎,与厚合菜丁放在一起,加番薯粉调成糊,加入佐料,入油锅炸之,色泽墨绿,外脆内嫩,吃起来,满口皆是原野的清香。
潮汕人爱食豆干,尤爱普宁豆干。普宁豆干和揭阳薯粉豆干、揭西布仔豆干、凤凰浮豆干,被称为潮汕豆干界的“四大天王”。作为潮汕地区最经典的小吃,即使去再小的潮州菜馆,你都会遇见它的身影。
普宁豆干与一般的豆干很是不同,制作时除了黄豆,还会加入薯粉,坊间有“头粉二豆三师傅”的说法。普宁豆干以普宁市燎原镇光南村出产的最为正宗。因在潮汕话中“干”与“官”同音,故每一块豆干中间皆有一个内凹方形小印,以此象征官印,寄寓了一种美好的意头。
炸豆干,讲究大鼎深油,最好用硬柴,火力威猛,伴隨着噼里啪啦的声响,豆干像金鱼一样在其中自由自在游动。起锅时加入黄栀,色泽金黄,让人欲罢不能。由于加入了薯粉,豆干油炸过后,会形成一层酥皮,皮肉自然分离,便会产生一种“金包银”的视觉效果。炸豆干,一定要现点现炸,出锅即食,一旦冷了,就如美人迟暮,不香,也不脆口,不吃也罢。吃的时候,对半切开,外皮酥脆,内肉滑嫩,好似芙蓉蛋,晃晃悠悠,像是要流出来一般。点上韭菜盐水或香葱盐水,滚烫的炸豆干,立刻变得适口,令人满口充盈清新之气。
普宁乃至潮汕地区最有风味的炸豆干,据说在普宁洪阳鸣岗村,那正是我妻子的外嫲家。我妻子从小在外嫲家长大,长得可爱,嘴甜,深受外嫲宠爱。村口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名曰“文溪”,我们每次去看外嫲,她都会带我们到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吃几盘炸豆干,队伍浩浩荡荡,让邻居们羡慕不已。
外嫲是八十一岁那年突然去世的,去世前几个月,她老觉得腰痛,我和妻子回去看她时,她突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回一趟娘家——虽然车程不过一小时,可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在自己的娘家,她脸上始终带着浅笑,与大家打着招呼,离开前,她又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目光里充满了眷恋。外嫲从来不会跟我们提要求,印象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或许,她早已有了预感,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接到噩耗,我们火速赶回。到鸣岗时,天色已晚,夜幕低垂,暗淡的光芒,笼罩着古老的村寨,村口的树木像披上一袭黑色的袍子,凝重而又悲伤。公厅的水晶棺材里,外嫲脸色青黄,神情安详。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远在广西柳州的大舅居然比我们到得还早,一问才知道,外嫲走的那一天,他恰巧回家。他原本是回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的,可没想到,刚下火车,就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大舅后来告诉我,以前,也有老家的朋友孩子结婚,邀请他回来喝喜酒,可路远事多,他一次都没答应,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天,他总觉得胸口发闷,坐立难安,心里有说不出的烦躁,当朋友提出邀请时,他居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就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陪母亲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这或许的确是一个巧合,但我不相信这仅仅只是巧合,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葬礼第二天,妻子抱着小女儿去灵堂跟老嫲做最后的告别。小女儿那时才两岁多,还不知道人间有死亡这回事,一见到灵堂上悬挂的照片,就像平时一样,伸出手,要老嫲来抱自己。她把身子扭得像麻花一样,手臂像鸟的翅膀一样扑动,可老嫲仍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小女儿哇哇大哭起来,她不明白,平日里最喜欢她的老嫲为什么不抱她……
外嫲去世以后,她居住的老厝立刻变得冷清,天井里长出了成片的青苔,寂静的午后,风轻轻地叩响门环,发出寂寥的回响,她养的那只老黑猫还不离不弃,痴痴地等着主人回来。
每次回去,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去老厝坐一坐,喝几泡工夫茶,让孩子们在寂静的房子里尽情地喧闹。外嫲的相片挂在墙上,像平常一样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我们时常会产生一种幻觉,总会隐隐约约听到她轻柔的说话声,总会觉得她会端着水果从厨房里慢腾腾地走出来。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去村口榕树下吃炸豆干,队伍依旧浩浩荡荡,但味道里终究少了一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