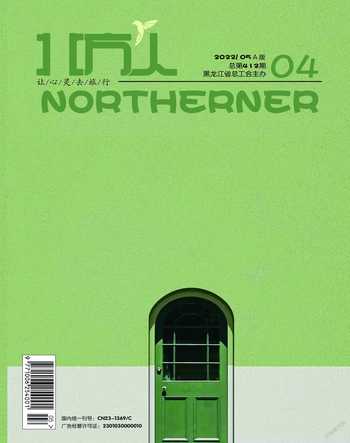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刘心武
北京有两座著名的金刚宝座塔。打个比方,碧云寺好比著名作家,而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
至今还记得19年前深秋到五塔寺写生的情景。那天下午,在空旷的寺庙里,我把对沟通的向往通过画笔铺排在对银杏树的描摹中。雌雄异体,单独存在,人与银杏其实非常相近。个体生命必须与他人、与群体,同处于世。人们都渴望获得友情。那么,什么是友情?友情最浅白的定义是“谈得来”,尽管我们每天都身处他人、群体之中,但真的谈得来的,能有几个?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有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看来看去,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顺手抽出,随便一翻,作者署名王小波。书里是几篇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
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我报上姓名,然后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3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我被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
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我觉得他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自己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并说:“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的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谈伴”吗?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
在餐馆,我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們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完全不同的想法。
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份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看着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11点了!再环顾周围,其他顾客早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被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铺上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着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了起来。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向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这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又打电话约王小波来喝酒,他又来了。我们仍旧有聊不尽的话题。
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太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自称是“王小波的哥们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的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但那竟是事实。他猝死于心肌梗死。
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
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呼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生,何以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