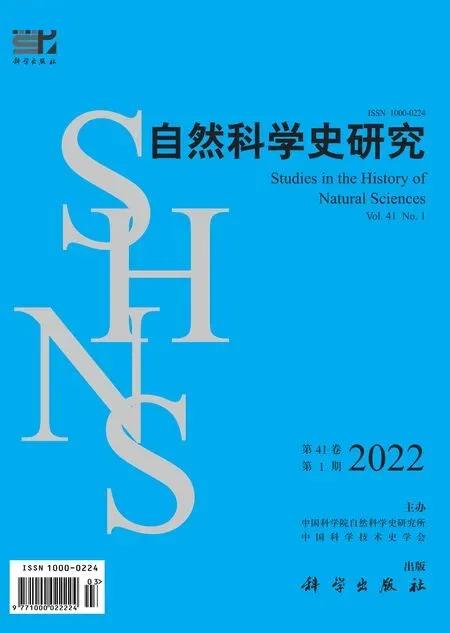从引火到纺织:宋明以来“ 火草”观念的变化
张学渝
(广西民族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南宁 530006)
什么是“ 火草”?对于掌握火草纺织技术的西南少数民族而言有一个明确的回答:火草就是他们认识的一种生长于周围环境中,可用于纺织或引火的植物。这种植物还有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专有名称,植物学家鉴定为菊科植物GerberadelavayiFranch.。
学界研究认为,火草纺织技术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1,2]。今天居住在云南和四川的傣[3]、傈僳[4- 6]、纳西[7- 9]、彝[10- 13]、壮[14]等少数民族的部分支系仍掌握火草纺织技术。与棉麻纤维不同,火草纤维有独特的物理、化学和遗传特点[15,16],它纤维短,无需经过化学处理即可用于纺织。实际上,火草纤维是目前已知唯一从植物叶背剥离后即可用于纺织的天然纤维。这使得火草纺织技术在世界纺织史中独树一帜。有学者还讨论了火草植物人工栽培的可行性[17,18]。此外,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部分彝族人至今还保存着利用火草引火和治病的习俗。西南少数民族利用火草引火、纺织、治病,体现了他们独有的植物利用观。
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形象。人们对某种植物的观念通常可由植物的外形、名称、用途以及产生的联想形成。什么是“ 火草”?问题背后暗含不同人群对火草植物命名、利用与认识的不同观念。“ 火草”是一个汉语名称,熟悉并利用它纺织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对它进行科学命名的是法国植物学家。因此,“ 火草”的观念包含了“ 火草”植物的利用与命名。本文将围绕“ 火草”观念变化,首先考察历史上“ 火草”一词产生的汉语语境,分析它在使用过程中如何被扩大,如何被限制,又如何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纺织技术上;再考证纺织火草(1)为了行文的便利,下文用“ 纺织火草”特指用于纺织的“ 火草”。的学名和民族名的产生与运用,分析不同名称的命名逻辑;最后探讨“ 火草”一词在当下承载的历史意义。
1 汉语史籍中“ 火草”的两种用途
1.1 引 火
“ 火草”的最初用途就是引火。宋代已有文献记录,如《 物类相感志》载:“ 釡底煤可代火草引火”[19]。事实上,宋代以前“ 火草”二字通常与“ 戒”、“ 慎”等字连用,意为辟火之草。宗懔(499—563)《 荆楚岁时记》:“ 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于屋上。”[20]《 荆楚岁时记》是一本记录古代荆楚一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里面讲到当地人春分日在屋顶种“ 戒火草”的习俗,以祈求屋宅不遭火灾。这种辟火之草有很多其他名称,郑樵(1104—1162)《 通志》:“ 景天,曰戒火,曰火母,曰救火,曰据火,曰慎火,今人皆谓之慎火草,植弱而叶嫩,种之阶庭能辟火。”[21]《 中华本草》认为它是八宝Hylotelephiumerythrostictum(Miq.) H. Ohba[22],属景天科八宝属,全国多地有分布。
可以看到,最初“ 火草”二字与其他词合用,表达防止、避开火的草之意,多出现在医药民俗类的文献中。
与辟火之草多名一物的情况不同,用于引火的“ 火草”则是一名多物。例如,王恽(1227—1304)《 秋涧集》说“ 艾,火草也”[23],这里的“ 火草”可能是菊科蒿属艾草ArtemisiaargyiH. Lév. & Vaniot。又如,民国《 息烽县志》载:
有草绒绒白色,顶丛开细黄花,味微甘,嫩时取和米粉少许,作粑食之,呼软曲粑。名清明草,清明时生,以后渐老则不可食。今按:此物诸县多产,亦有呼清明菜或翘耳菜者,乡人摘取入城市叫卖,人争购之。清明以后虽不中食,然采其枯者,抽筋揉制至极软,能引火,人呼“ 火草”,当火柴未盛时远行者必携火镰、火石、火草。自随县之乡老,斯时固有不能忘是风味者。[24]
这里的“ 火草”指菊科鼠曲草属鼠曲草GnaphaliumaffineD. Don。再如,宣统《 续蒙自县志》载:“ 火草,叶背有白绒,土人缉以为衣,晒干揉之引火焚香。”[25]这里的“ 火草”指菊科火石花属火石花GerberadelavayiFranch。再如,有文献表明它是棉花。民国《 重修镇原县志》称:“ 陇东不用外货,但以新棉花渍以硝水晒干即能用,俗谓之火草”。[26]
也就是说,“ 火草”只是诸多引火之草的统称。明代的军事类文献大量记载了这样的“ 火草”。例如,何汝宾(生卒年不详)《 兵录》中提及大鸟铳施放时需用到“ 火草”。[27]戚继光(1528—1588)《 练兵实纪》描述的烽火台设置标准中,有大木梆2架、旗杆3根、发火草60个、火池3座、火绳5条、火镰火石1副、扯旗绳子5副,还规定发火草必须盖住防止被雨淋湿。[28]这些文献中的“ 火草”具体是什么并不清楚。
1.2 纺织
明代,“ 火草”出现了一个新用途:纺织。《 南诏通纪》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 火草布”的文献。李元阳(1497—1580)《 云南通志》卷11载:
杨鼐 太和人,举人。授黄州府通判,以廉明称。致仕归里,四十余年,无老少贤不肖,皆称为长者。所著有《 南诏通纪》。寿百岁乃卒。[29]
据侯冲考证,“ 杨鼐”为误写,《 南诏通纪》作者应为杨鼎,生卒年不详,云南太和(今大理市)人,白族,为明弘治己酉(1489)举人,到嘉靖年间仍健在。[30]《 南诏通纪》1卷,已佚。据王叔武考证,嘉靖十一年(1532)出版的《 南诏源流纪要》一书参考了杨鼎《 南诏通纪》的抄本。[31]
由于目前无法判定杨鼎《 南诏通纪》的成书时间,是否有其他文献可以一窥火草布的早期历史呢?笔者发现,明景泰六年(1455)陈文(1405—1468)修纂的《 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了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境内“ 百夷”织造的布与此有关:
(北胜州)其俗勤生。境内多百夷,与摩些蛮稍异,而其妇人尤勤于耕织之务,所成之布,洗令洁白,而为衣、为巾,率用之。[32]
陈文,字安简,江西庐陵人,明景泰二年(1451)任云南布政司右布政使,在云南为官6年。陈文描述的“ 洗令洁白”符合火草布特征。据笔者传统工艺调查,永胜县境内彝族支系他留人、傈僳族掌握火草麻布纺织技术;他留人和白依人(2)白依人为彝族支系,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六合彝族乡,以掌握火草纺织技术闻名。的洗衣实践证实火草衣会越洗越白,这种特征与棉麻布区别很大。徐晓丹通过科学实验揭示了其中的原因:火草衣在洗涤过程中,一些不太稳定的化学成份(如蜡质)发生降解;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多,一些使火草衣呈现出黄色的化学成份逐渐减少,导致它越洗越白。[16]从技术的地域分布和织物特征来看,《 云南图经志书》中描述的织物应当就是火草布。由此可知,现存文献表明火草纺织技术的历史不晚于1455年(3)目前学界关于最早记载火草布文献的判断有两种观点。观点1:从《 滇略》作者谢肇淛生平出发,以天启元年(1621)为标准,推算出火草布的历史距今约370年。([4],75页) 很显然,这是不准确的,忽略了《 滇略》所记火草布信息来源于杨鼎《 南诏通纪》的事实。观点2:以杨鼎《 南诏通纪》为标准,得出火草布在云南的历史为500年以上的结论。([1],64页)。陈文并没有用“ 火草”去称呼这种植物,火草布有其实,未有其名。
今天人们对杨鼎《 南诏通纪》中火草布的认识依赖谢肇淛(1567—1624)《 滇略》的转引:
兜罗锦,出金齿木邦甸。又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蹋地而生。叶背有绵,取其端而抽之,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以为可以为燧取火,故曰火草。然不知其何所出也。[31]
谢肇淛是福建人,1618年出任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兼佥事,分巡金沧道,辖大理、蒙化、鹤庆、丽江、永宁五郡及五井盐课提举司,三年后离任。[33]杨鼎的记载,让这种植物和织物有了汉语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杨鼎指出火草布“ 不知其何所出也”,而明朝末期谢肇淛并未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照书摘抄。这说明杨鼎提到的“ 火草布”是一种声名在外又较为神秘的布。
明末刘文征(1555—1626)《 滇志》说:
罗婺本武定种,……今俗又称罗午,楚雄、姚安、永宁、罗次皆有之。男子髻束高顶,戴笠披毡,衣火草布。其草得于山中,缉而织之,粗恶而坚致,或市之省城,为囊橐以盛米贝。[34]
罗婺属于古代彝族的一支,他们也掌握火草纺织技术。罗婺分布在武定、楚雄、姚安、永宁、罗次等地,不在杨鼎和谢肇淛的出生和任职地域内。
为什么杨鼎、谢肇淛、刘文征等人会用“ 火草”去称呼云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植物呢?我们从“ 火草”利用方式存在人群差异现象上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康熙《 蒙化府志》和《 云南府志》“ 物产”条分别记载了“ 火草,能取火”[35]、“ 火草,土人绩以为衣”[36]。光绪十年(1885)《 姚州志》卷3亦载:火草“ 用以引燧者,暴干,去表存里,夷人则生取之,缉其里为线……名曰火草布。”[37]从历代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用“ 火草”引火者无人群限制,而用“ 火草”纺织者为特定人群——“ 土人”、“ 夷人”。云南少数民族用来纺织的植物可以引火,正是杨鼎、谢肇淛、刘文征等人用汉语“ 火草”去称呼这种未知纺织植物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云南的官员对这种植物的纺织功能感到好奇,才将之付诸笔墨。他们不但描述了一种新知识——既可以引火又可以纺织的火草,而且还描述了利用它进行引火和纺织的少数民族。在这些文献中,也可以看到“ 火草”的两个用途在地域上的差别:引火用途没有地域限制,纺织用途仅出现在云南省。
明代文献对云南纺织火草的记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让这种植物有了通俗的汉语名,尤其是刘文征《 滇志》清楚记载了纺织火草、火草布、火草纺织技术和使用人群,植物、织物、技术和民族都得以具名。这使得火草纺织技术成为棉麻丝毛大类纺织技术之外的一种“ 新”技术而逐渐被人知晓;火草纺织技术也成为罗婺等云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
在用技术标记民族的过程中,无形中强化了火草用于纺织的观念。其中,清朝中期《 皇清职贡图》的绘制和颁布便是最大的一次强化活动。乾隆时期,清朝版图扩大。为了反映域外各国和域内各族的风俗习惯,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十一日,乾隆皇帝晓谕四川总督策楞(?—1756),命其将所知“ 西番、猡猡男妇形状,并衣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正式拉开了编纂《 皇清职贡图》的序幕。[38]《 皇清职贡图》中出现三个以“ 火草布”为特产的族群:“ 罗婺”(图1)、“ 窝泥”和“ 麦岔”。

图1 《 职贡图》中的罗婺蛮男、妇形象(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罗婺 男子挽发戴笠,短衣披毡衫,佩刀跣足,耕种输税。妇人辫发垂肩,饰以珠石,短衣长裙,皆染皂色。其地产火草,绩而为布,理粗质坚,衣服之余或贸于市。
窝泥 其人居深山中,性朴鲁,面黧黑,编麦秸为帽,以火草布及麻布为衣,男女皆短衫长袴,耕山牧豕纳粮赋,常入市贸易。
麦岔 男挽发,短衣跣足,时负米粮入市。勤于治生,输赋惟谨。妇人装束与男略同。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地产火草,可织为布。[39]
《 皇清职贡图》是清朝主导下的一次大型民族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巡礼。仔细分辨《 皇清职贡图》所记载的这三个族群,它们拥有两个共性:其一,都输赋纳税,有别于其他不输纳税赋的“ 蛮人”,体现了他们的政治身份;其二,都以火草布为衣,有别于其他衣不蔽体的“ 野人”,体现了他们的文化身份。输赋纳税和着火草衣让他们成为受朝廷管理的具有显著标志的“ 蛮夷”。
《 皇清职贡图》有多个版本,早期版本中存在满汉二体兼书形式,是两种不同观念的产物[40]。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 火草”观念的满文视角。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谢遂(生卒年不详)《 皇清职贡图》[41](以下简称“ 台版”)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职贡图》[42](以下简称“ 法版”)为例,考察其中“ 火草”和“ 火草布”的满汉互译情况。(1)“ 火草”:台版的满文书写不统一,罗婺和窝泥的满文拉丁转写同是fulgiyeri orho,麦岔是fulgiyari orho,存在a跟e的差异;法版的满文书写统一,均为fulgiyari orho。(2)“ 火草布”:台版的满文只译出“ 火草”(fulgiyeri orho),省译了“ 布”(boso),与后文“ 麻布”(olo boso)连译(fulgiyeri orho olo boso)后为“ 火草麻布”,改变了汉文意思;法版完整译出“ 火草布”(fulgiyari orho boso),与后文“ 麻布”(olo boso)连译(fulgiyari orho boso olo boso)为“ 火草布、麻布”,符合汉文意思。
《 皇清职贡图》不同版本中的细小翻译差别,暗含了满文对汉语词汇“ 火草”所代表的植物、织物和技术的吸收与认识过程,成为判断版本优劣的一个指标。皇帝勅绘的《 皇清职贡图》记录罗婺、窝泥和麦岔三个族群利用火草织布的历史,有助于将“ 火草”用于纺织的观念传播开来。《 皇清职贡图》的编纂对后世诸多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 滇夷图”产生了重要影响。
2 纺织火草学名的出现
清中期人们可以通过“ 滇夷图”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火草纺织技术,但这个植物具体长什么样,并不是很清楚。明代文献对它的记载相当简单:“ 草叶三四寸,蹋地而生。叶背有绵”。清人檀萃(1725—1801)《 滇海虞衡志》甚至错误认为火草就是火麻。[43]火麻又称大麻、胡麻,是常见的纺织原料。檀萃是安徽望江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云南禄劝知县,在滇20年。该书是他在滇期间所著,完成于嘉庆四年(1799),刊刻于嘉庆九年(1804)。禄劝产火草,檀萃的履历使他有条件弄清纺织火草的真实形态,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概檀萃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需要考究的问题,就根据传闻说火草就是火麻。
清朝中期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才逐渐清晰。同治年间《 会理州志》指出,纺织火草的形态特征是“ 面绿背白”,属于蒿类植物。[44]光绪十年《 姚州志》卷3《 食货志·物产》“ 火草布”条的记载更详细:
火草,叶似芣苢,表青里白,丛生如盘,其用以引燧者,暴干,去表存里,夷人则生取之,缉其里为线,织时用麻线为经,此线为纬,名曰火草布。其轻暖鲜洁,较胜于净麻者。[37]
这里描述了纺织火草的特征:叶子形状像车前草(“ 芣苢”),颜色“ 表青里白”,丛生;叶子晒干揉掉表层留下里层可以用于燧石取火;叶子新鲜时里层可缉线,用此线作纬线、麻线作经线织成的布,称为火草布。这种布轻暖鲜洁,优于纯麻布。光绪《 姚州志》准确描述了纺织火草的形态特征,还详细记载了火草麻布的制作工艺。
对纺织火草进行更详细的植物学描述和分类的是法国植物学家。19世纪下半叶,云南成为西方博物学事业的重要考察地,借助传教士的考察,西方世界得以了解许多东方植物。纺织火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介绍到西方。
1885年起,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 Vial,中文名邓明德,1855—1917)在云南石林定居传教,同时调查彝族撒尼文化。他在文集中记录了撒尼人的火草布:
撒尼人的衣料有四种:棉、毛、麻和火草。前三种是人尽皆知的,但火草是什么呢?我将这种衣料寄给我的同僚德拉维(Delavay),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植物学家,他回信道:“ 该植物的中文名字叫打火草(即火绒草),生长在大理府(Talifou),扁鹊山(Piekio)的倮倮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该植物来取火。这是菊科的杂交新品种,我将它转寄博物馆和植物杂志,并伴有特朗歇(Trnancher)(4)疑为拼写错误,推测应为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A. R. Franchet,1834—1900)。以下行文中用“ 弗朗谢”。先生的描述:正月二月开花,花色白,外沿为玫瑰色,形似款冬。”[45]
这里提到的德拉维(Père Jean Marie Delavay,中文名马伯禄,又称赖神甫,1834—1895)也是法国传教士,1867年来华,在广东和海南传教,1881年回国度假时结识了在华采集生物的传教士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1826—1900),并认识了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A.R.Franchet,1834—1900)。德拉维应佛朗谢之请为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植物标本。他于1882年到达云南,在滇西北建立新传教点,同时在大理与丽江之间、大理西北部采集植物。[46]德拉维提到,这种植物的中文名称叫“ 打火草”,大理的彝族人也用它来取火,但错误地认为这是菊科的杂交新品种。
维亚尔继续描述到:
这种可作纺织的草贴地面而生,叶长,作针形,正面色泽绿亮,背面乳白。白色部分就是纺织原料。[45]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保存了一份标本PE01843420,采集日期为1886年6月3日,采集地在中国云南,海拔1800米。采摘标本时,植物处于有花无果期。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保存了两份标本HUHA00008266(图2)、HUHA00008267,为模式标本,采集日期是1889年1月9日,采集地也在云南。这三份标本的采集人署名为“ J. M. Delavay”,鉴定签上的学名为“GerberadelavayiFranch.”。这应是德拉维在大理采集的纺织火草。

图2 纺织火草的模式标本(1889年) (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藏)
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阿尔佛雷德·李埃达(Alfred Liétard,中文名田德能(5)据郭丽娜考证,Alfred Liétard的汉名为田德能。[47],1872—1912)1913年出版的著作《 云南倮倮泼》(AuYun-NanLesLo-LoP’o)介绍了彝族的纺织火草:
这是另外一种纤维,比麻更白、更坚韧,倮倮妇女也用它织布。这种纤维取自一种被汉人称叫火草的植物,不过在天朝被叫作大火草的植物实在太多了,我们也分不清楚,不过上述提到的这种在当地被叫作ké-mè。龙怀仁神父告诉我,这种草应该是钩苞大丁草。
草长在潮湿的地方,叶片下面有一层白色物质,多少有点像棉花。人们用牙齿咬断草的上部,这样一来,就能把丝拉出来并卷起,从而取下这层白色物质。妇女们借助绑在大腿上的一小块木板来完成这一操作。每根丝一头接着一头,慢慢绕起来。然后,丝卷被堆在一条木尺上,保存在干净的地方。[48]
笔者与此书的中文译者郭丽娜交流了译文中与“ 火草”相关的4个词的译法。我们发现:“ 火草”的法文原文为“hots’ao5”,这是李埃达据汉语音译的结果;“ 大火草”的“ 大”为误译;“ ké-mè”为原词,应为“ 火草”的彝语名称;“ 钩苞大丁草”原文为“GerberaDelavayi”,译法来自《 中国植物志》。
李埃达也发现,在中国叫“ 火草”的植物实在太多。同为法国传教士的龙怀仁(François Ducloux,1864—1945)告诉他,彝族人纺织火草的学名是Gerberadelavayi。该学名由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于1888年发表于法国植物学杂志JournaldeBotanique[49,50],命名遵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开创的双名命名法。
双名命名法的结构为属名+种加词+命名人。“GerberadelavayiFranch.”中的“ Gerbera”是属名,“ delavayi”是种加词,“ Franch.”是命名人。其中,“ Franch.”是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名字的缩写,种加词来自对采集该植物做过贡献的人的名字。结合法国传教士在云南传教与采集植物的历史,以及上述三份植物标本的采集人信息看,纺织火草的种加词“ delavayi”来源于法国传教士德拉维(Delavay),是命名人植物学家弗朗谢将德拉维的名字拉丁化处理的结果(6)在植物学名的命名规则中,所有词都需要经过拉丁化处理。如果被纪念的是单独一人且名字又以除a以外的元音字母或er结尾,则男性直接加缀词尾-i。[51],用以纪念他的植物采集工作。
法国传教士的到来让纺织火草借由法国植物学家之手纳入现代植物分类学谱系中,成为现代植物学的研究对象。
3 纺织火草的民族名
对于掌握火草纺织技术的西南少数民族而言,“ 火草”和“GerberadelavayiFranch.”都是一种外来名称。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纺织火草有着丰富的民族名,用于日常交流。以下列举了纺织火草的不同民族名:
白族:Bairtcet摆册、Hueixcet灰册、Zorxmoxcet皱摸册;
纳西族:Labo痨波、Robo荣波;
傈僳族:叨么、扎曼、扎咩闷;
傣族:闷;
壮族:满尾。
这些民族名代表的是不同民族的使用习惯。不同民族间的民族名有异同,如傈僳族和彝族;同一民族内的民族名也有异同,如彝族白依人叫咂吗,红彝人叫叨么,撒尼人叫扎命。这些民族名来源无从考证。笔者请教彝语专家黄建明,他说撒尼人“ 扎命”中“ 扎”意为叶片,“ 命”意为“ 污垢”,“ 扎命”意为叶子背后的纤维长得像污垢。显然这在理解上存在困难。事实上,民族名大多较随意、直观与自由,是一定人群内的约定俗成。
纺织火草的民族名表明,地方命名传统拥有广泛而强大的使用基础,由长期口传心授式的力量维持,嵌入当地人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生产生活中。
4 “ 火草”植物名称科学化、传播困境与统一问题
4.1 “ 火草”植物名称科学化及传播困境
现代植物科学命名一直遵循1753年林奈《 植物种志》(SpeciesPlantarum)创立的双名命名法。植物获得的这种以“ 种”为基本分类单位和以拉丁语为载体的名称叫做学名(scientific name),其他所有的名称都是俗名(vernacular name),钟观光(1868—1940)称之为邦名。
双名法能有效解决同名异物问题,正如“ 火草”这个俗名所遇到的情况。20世纪60—80年代,为了更好利用植物资源,农林医药相关工作者开展了植物的科学命名工作。笔者对这一时期植物资源普查的不完全统计发现,仅别名为“ 火草”的植物就有13种(见表1),它们还有“ 野火草”、“ 细火草”、“ 羊头火草”、“ 小火草”、“ 大火草”、“ 打火草”、“ 恶背火草”、“ 牛耳朵火草”等其他含火草字样的别名。类似别名还有“ 假火草”(7)小火草Gerbera anandria Schutz-Bip.。、“ 白叶火草”(又名大白叶子火草)(8)白叶火草Senecio nagensium C.B. Clarke。、“ 火草花”(9)野棉花Anemone hupehensis V.Lem.。、“ 小败火草”(10)多枝婆婆纳Veronica persica Poir.,爪哇婆婆纳Veronica javanica BI.。、“ 火草疙瘩”(11)鳍蓟Olgaea leucophylla(Turcz.) Iljin。等植物。

表1 “ 火草”植物名称科学化统计表
资料来源:《 贵州民间药物》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65年)、《 陕西草药》(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革命委员会,1970年)、《 陕西草药》(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革命委员会,1970年)、《 四川常用中草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71年)、《 湖南药物志》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2年)、《 秦岭巴山天然药物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云南中草药》(云南人民出版社,1971年)、《 红河中草药》(红河州卫生局,1971年)、《 广西植物名录》第2册《 双子叶植物》(广西植物研究所,1971)、《 万县中草药》(四川省万县地区卫生局、四川省万县地区科委,1977年)、《 四川常用中草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71年)、《 彝药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华山药物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秦岭巴山天然药物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榆林中医(地方中药分册)》(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大理中药资源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
这些植物的别名是地方命名传统的体现。可以看出,存在于地方的“ 火草”植物数量和分布地域远多于明清史籍记载。这些植物的叶片都有不同程度的毛绒,故有“ 火草”之名。经过名称科学化后,它们获得了学名和中文名,实现了指称唯一,“ 火草”成为别名。
学名是一种超越地域与民族的国际性通约,解决了世界各地植物的同名异物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但从社会价值看,学名的使用局限在高度专业化人群中,会产生传播困境。这种情况下,俗名的价值得到展现。钟观光曾对植物的学名和俗名有过精辟论述:
邦名与学名,如鸟翼车轮,相须并进,不具其一,必兼丧其二……如无学名记录,则义类不明,即与世界文化隔绝,等于薪柴。如无邦名记录,则传达无具,即与国内文化隔绝,等于饰品。[53]
通常植物的俗名很多,需要选择一个被共同体普遍接受、最具传播度的俗名作为普通名(又叫中文名)。普通名之外的所有俗名都称为别名,其使用的广度又再次降低。[54]
4.2 Gerbera delavayi Franch.中文名的两种观点
虽然在20世纪初,中国植物学家就通过植物考据探索植物学名的中文名,但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植物中文名命名法规(12)中国植物学界有识之士已开始积极探索。王锦秀和汤彦承提出要推广普通名,并尽量在旧有名中选用,力避另拟新名。一物定一普通名,其他名称一律称作别名。这需要对中国古代植物学文献进行考证,理清其中有关植物名称的问题。[55,56]。植物学家围绕如何命名GerberadelavayiFranch.的中文名,出现了两种观点,体现在不同时期的植物志书中。
第1种采用“ 钩苞大丁草”为中文名,科属归类为菊科大丁草属。该名最早出现于1975年版《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57]。它有两个相近叫法,“ 钩毛大丁草”(《 云南中草药选》,1970)[58]、“ 钩苞扶郎花”(《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1984)[59]。由于《 中国植物志》(1996)的采用[60],影响深远。
第2种采用“ 火石花”为中文名。植物学家吴征镒(1916—2013)和彭华(1959— )建议采用此名,并将大丁草属分出一个火石花属Gerbera Cass.,将原大丁草属名Gerbera作为火石花属的属名,大丁草属名改为Leibnitzia。[61]《 云南植物志》(2004)和《 中国植物志》的英文版《 Flora of China》(2011)均采用这一名称和归属方式。[62,63]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代表了两种命名思路:“ 钩苞大丁草”遵循了植物苞叶线状钻形的外形特征,也符合音译原则;“ 火石花”是纺织火草在丽江地区的叫法,尊重了该植物利用史。第1种命名思路按植物形态命名,但忽略了植物的利用史。第2种命名思路注意到该植物“ 用以引火,丽江产量大”[61]的事实,也即意识到植物利用史在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但该名称是否具有最大的传播度值得思考。
5 火草:在学名与民族名之间
GerberadelavayiFranch.的中文名该如何定,植物学家提出的新旧两种中文名由于使用习惯和传播效率等原因,将待时间检验。如果我们将目光从科学工作转向社会实践,能够看到另一股力量正在慢慢推广“ 火草”这个名称——这就是国家管理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 非遗”)工作。
21世纪以来,火草纺织技艺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一样被“ 发现”,成为当下社会中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西南地区不同少数民族的火草纺织技艺陆续被纳入国家四级“ 非遗”名录。据不完全统计,涉及的地区和民族有:四川省德昌县傈僳族(2007年省级,2014年国家级)、米易县傈僳族(2011年省级)、盐边县傈僳族(县级),云南省石林县彝族(2005年市级,2013年省级)、马龙县彝族(2009年省级)、丘北县壮族(2005年县级,2009年省级)、永胜县彝族(2009年省级)、鹤庆县彝族(2010年县级,2015年州级)、漾濞县傈僳族(2020年州级)、宾川县傈僳族(2019年县级,2020年州级)、祥云县傈僳族(2020年州级)、南华县彝族(2012年县级,2013年省级)、大姚县傣族(2018年县级,2019年州级)。这些数据会随着“ 非遗”工作的深入而不断变动。
国家的“ 非遗”工作再次推广了火草用于纺织的观念。西南地区的火草纺织技术也随着国家“ 非遗”工作的开展逐渐“ 走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被技术使用地以外的更多人认知。
6 结 论
“ 火草”植物在历史上有引火和纺织两种用途,不同时代、地域与人群对它的认识各异。伴随着国家治理活动、植物科学命名工作、新引火技术的出现等因素影响,“ 火草”用于引火的观念被淡化,用于纺织的观念被强化,让“ 火草”一词由历史上的统称转换为当下一个极具辨识度的专有名词,呈现由引火到纺织观念的转变。对于掌握火草纺织技术的西南少数民族而言,火草纺织技术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
“ 火草”从用于引火到用于纺织观念的转变是不同力量对纺织火草赋义的结果:明代云南官员用汉名“ 火草”、19世纪法国植物学家用拉丁名GerberadelavayiFranch.让它具名;清代和当下的国家治理活动用“ 火草”让它闻名,强调了西南少数民族火草纺织技术的历史;当代中国植物学家的科学命名工作解决了俗名“ 火草”植物的同名异物问题;掌握火草纺织技术的西南少数民族在保持本民族命名传统的同时将客位“ 火草”概念主位化。最终,汉名“ 火草”、拉丁名“GerberadelavayiFranch.”和彝名“ 拜地”、傈僳名“ 叨么”、壮名“ 满尾”等产生了跨越时空与文化的连接。
宋明以来“ 火草”观念的变化体现了植物命名的科学传统、地方传统和历史传统的碰撞与调整,是纺织火草、火草纺织技术和使用人群被外界认识的历史。纯粹的学名和别名在对外交流时都会出现障碍,需要普通名做桥梁。植物的学名、普通名和别名是不同人群对植物命名的约定俗成。面对那些未被人类利用的植物,植物外形特征是科学命名的唯一依据;而面对那些具有利用史的植物,利用者赋予植物的丰富历史与经验信息可能转化为学名、普通名或别名,在植物科学命名时尤需注意。目前纺织火草的中文名存在不同观点,但在科学化浪潮和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 火草”这个名称无形中扮演了普通名的角色,沟通了植物命名的科学传统和地方传统,成为学名和民族名的桥梁,被更多人接受和传播。
致 谢本文先后得到罗桂环研究员、何珵副教授、霍仁龙副研究员、匿名审稿专家、邹大海研究员、本刊编辑老师的指正和宝贵意见,郭丽娜教授、黄丽君副研究员和黄建明教授指导法、满和彝文资料,谨对他们无私的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