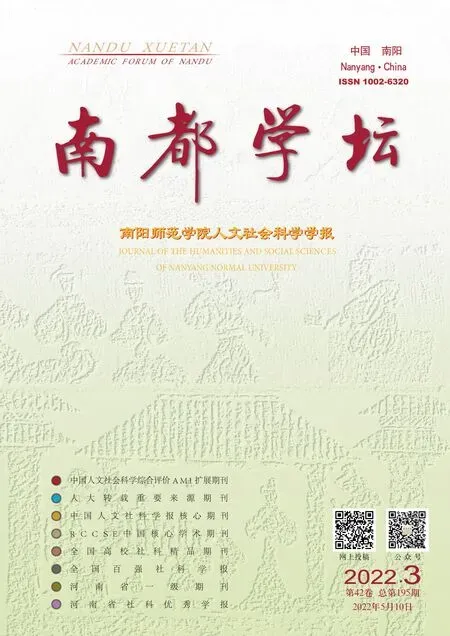吴与弼的“成人”之学与明代中前期士风演变
姜海军, 桂晨昊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吴与弼(1392—1469),号康斋,江西抚州崇仁人,国子司业吴溥之子,明前期名儒,弟子有娄谅、胡居仁、陈献章等,在明代儒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明儒学案》列其《崇仁学案》为第一。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学术归属争议纷纭,从不同角度论述其学术特点,产生了丰富成果(1)古清美《明代前期理学的变化与发展》,《明代理学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钟彩钧《吴康斋的生活与学术》,中国文哲研究所编《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0期,1997年版,第269-316页;邹建锋《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张运华《吴与弼的理学思想》,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姚才刚,张露琳《明初理学中心学思想的萌芽》,载《哲学研究》2019年第10期;盛珂《居敬与洒落之间——吴康斋工夫论的内在张力及其定位》,载《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6期等。。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充分重视吴与弼一直强调的“成人”之志,以及由此延展开的康斋学发展脉络。如从这一方面入手,可审康斋之学所取得的成就,见其不同于明初士风与政治紧密结合,而追求儒家理想从而卓然独立的鲜明特点,并可见其与陈献章精神风格的高度相似处,一窥康斋与白沙之授受,联系士人规模的扩大与价值取向变化,可知明代前中期士风的转变。
一、“期于成人”与康斋学的形成
吴与弼自叙其少年学习经历是“六岁入小学,七岁而习对句,十有六岁而学诗赋,十有八岁而习举子业。十有九岁得《伊洛渊源录》,观周、程、张、邵诸君子出处大概,乃知圣贤之学之美而私心慕之”,受“父兄师友之教”[1]1215。其为学目标乃其父所教“努力进学,期于成人”,当时吴与弼“自谓古人不难到”[1]1212。“成人”正是吴与弼一生的最高追求,也是其思考的核心问题,康斋学正是围绕吴与弼对“成人”的求索与践履形成的。
为求圣贤之道、遂成人之志,吴与弼放弃科举,回到家乡山居读书。但“乡村僻处,无师友之资,兼以多病,家务无可委托,不得大进”[1]1221,由于生活清苦、学问困难、缺乏挚交,他十多年的学习虽有所收获,却并不足以解决其维持生活和境界提升的难题。吴与弼由此多年困顿,不得出路,云:“中道立苦难,学问少勉强。古人岂易期,中宵独惝恍。”[1]956又说:
及年十八九,虽略知读书,志气太锐,自谓古人不难到,每轻前人,忽慢行事……年二十一,回乡,粗涉人事,然后渐知力行之果不为易……茫然不知道路所由,安得而顺乎亲哉?[1]1212
他一再反省当初锐气,感慨“古人”不易到,正说明“成人”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正因为志于“成人”,所以他高度关注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行为与心理,执着于自身境界,有大量“良心贵有养”[1]951、“随处动心兼忍性”[1]977之类的句子,有的学者倾向于以陆学的范畴来理解,有的学者倾向于以朱子敬义夹持工夫来理解,或许就吴与弼本人而言,对自身状态境界的关注以及修养,只是一种必要的践履工夫,并不具有明显的朱学或陆学分野。
吴与弼虽然最尊朱子,但未尝直接高低朱陆之学,而且,他比较广泛、深入地研究宋儒典籍的时间较晚,因此其早年形成并终身践履的修养工夫,或许并无主观上的从朱或从陆的问题。直到永乐十九年(1421),宋儒才较多见于吴与弼诗中,而且其中有偶然因素。该年他本欲迎外祖母返乡,但因与父亲关系微妙,竟船走湖广,游览拜谒,故而作《谒濂溪晦庵二先生祠》二首、《观濂洛关闽诸君子遗像》[1]968-969等诗。钟彩钧认为:“康斋常提及的书只有数种,虽然由于他的方法是致精以学圣贤,但也因为环境的关系。康斋乡居且家贫,书籍的获得当受到限制”,并猜测吴氏获得朱子文集约在父丧之后,可谓有理[2]。直到宣德四年,他还致书友人说:“徽州及各县有何书籍?幸一一惠及为感。”[1]1225可见他早年拥书有限。
吴与弼之父吴溥去世于宣德元年,与弼守丧至宣德三年十月,这是他人生最困难的三年,也是康斋学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三年。吴与弼山中守丧,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虽然较多接触宋儒学说,却并未骤入圣人门庭或解决眼下困境,同时,生活与学问固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为学旷锄犁,事农疏典籍。学弛心性芜,农惰饥冻逼。二者贵兼之,庶几日滋益。奈何疾病缠,蹉跎旦复夕。”[1]985吴与弼不得不正视问题、寻找出路,终于引《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之说开辟路径,其《灯下作》云“日日劳筋骨,心中未免疑。细思贫贱理,素位合如斯”[1]985。仅从谋生或治学看,农、学必相冲突,而从自身看,则农、学皆当从事,将谋生与治学、农民与学者身份对立的问题,统归为自身的安顿与成就问题,如此,为学与事农之间的障壁便破除了。《崇仁县志》言其“中岁,家益贫,衣食不给,风雨不蔽,躬亲稼穑,手足胼胝”[3]172,吴与弼说:“虽暂废书,亦贫贱所当然”,“自是本分事,何愠之有?素贫贱,行乎贫贱”[1]1290-1291。素位而行使劳动成为其践履工夫不可剥离的部分,成为康斋学的重要内容。虽然如此,吴氏生活依然窘迫,叹“贫而乐”之“不易及”,“古人恐未必如吾辈之贫”[1]1291,然而其志坚牢,“大抵学者践履工夫,从至难至危处试验过,方始无往不利”[1]1290,“须素位而行,不必计较”[1]1293。可以说,康斋学躬行实践、笃实奋进的特点有前学影响及吴与弼性格因素,但相当程度上也是生活所逼。
服阕后,吴氏《冬夜枕上作》道:“遥忆当年学立身,兢兢常恐暂埃尘。孤风自许追千古,特操何曾让一人。因病简编寻旷弛,离群践履转逡巡。中宵忽感平生志,回首空过十七春。”[1]986这样彻底的反省,是对自身困境的全面观察、对过去学问内容与路径的彻底检讨。此后不久,吴与弼便迁居小陂,次年真正开始了读书、农耕、授业一体的生活。他说:
予幼承父师之训,尝读先儒释日新之旨,每恨洗涤工夫未闻焉。又读夫子赞《易》洗心之章,圣人妙用,未易窥测也。于是,退而求诸日用之间,从事乎主一无适及整齐严肃之规,与夫利斧之喻,而日孜孜焉。[1]1277-1278
其“退而求诸日用之间”,大约即在永乐末至宣德初,对应于其全面检讨,这是多年摸索和生活逼迫出来的。《明史》说娄谅“少有志绝学。闻吴与弼在临川,往从之。一日,与弼治地,召谅往视,云学者须亲细务。谅素豪迈,由此折节。虽扫除之事,必身亲之”[4]7263。吴与弼教性格豪迈的娄谅从事劳动之“细务”,正基于自己的体知。《明儒学案》说他“一日刈禾,镰伤厥指,先生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欲表其人,其实未必没有农家生活艰难而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求诸日用,与“成人”追求呼应,也扩充了“成人”的内涵,易为广大普通读书人接受和实践。吴与弼于宣德三年的全面检讨可以视为其早年学术与生活,亦即其人生早年阶段的句号,而宣德四年即后世所谓康斋学的开始。“康斋学”旨在“成人”,其形成的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也是围绕自身的安顿与成就展开的。
吴与弼思想的变化也反映于诗歌创作。吴氏好唐诗已为学界注意,钟彩钧说:“康斋对唐诗有一定的熟悉,而成为生活上固定的兴趣。”[2]但实际上,从永乐末到景泰年间,他效法唐诗的作品创作显著减少。现存《康斋集》中,康斋永乐十九年作《除夜次唐人诗韵》,而之后次唐韵者则为《苏州绝句次唐诗韵》(二首),该诗作于景泰四年,竟隔32年。这显非文献佚失所致,或有两种原因:吴在此期间没有创作该类诗歌;有所创作但有意摘除(2)正统元年吴与弼曾作《阅旧稿毕偶成》:“连日频将旧稿披,恍然如梦对当时。知非已晚嗟何及,空使残魂咏小诗。”(《康斋集》卷3,第1004页)可知康斋保存并批阅旧稿,康斋集中的注也可说明这一点,如此,其便有可能删改旧稿。。不论如何,都说明吴与弼在永乐末或宣德初年以后长期有意抑制文学表露。比较前后,康斋在宣德正统年间,诗歌对唐宋作品的化用较少,理学诗的创作处于高峰,而这恰与其着力研究宋儒学问对应。
在《康斋集》第一首诗中,吴与弼道:“吟断难成调,尘编重绎寻。兴亡今古事,精一圣贤心。新月何时满,寒蛩无数吟。夜深双过鸟,犹自恋高林。”[1]945诗作于永乐八年(1410)。裘君弘评曰:“细玩诗中结语,寄托遥深,殊有宅仁而居、置身千仞之意。作诗时自注‘永乐庚寅’,年十九,先生贵公子也。尔时见地便高如此,大儒之兴岂偶然哉。”[5]吴与弼性格中确有高卓坚毅的成分,不然也不会为真正接受“成人”之志、为理想刻苦一生。但吴与弼其人其学,不仅在于吴之个性,还有一定的历史环境使之得以实现,展现出不同于当时的特质,能够引一时瞩目,影响后来学者。
二、吴与弼与明初士风相左
吴与弼“期于成人”,一生躬行践履、讲学授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际上是特殊的。如果考虑到他出生于洪武、长成于永乐,把他的志向和事迹与明初士风相比较,更能看出康斋不同于世,由此可以体会康斋学的价值。
成圣成贤固不少见于诸儒,但叨叨“成人”以此终身者,却不多见。大约与吴与弼同时的大儒曹端、薛瑄,绝少言“成人”,虑及吴与弼“病宋末笺注之繁,故不轻于著述”(3)今《康斋集》所存者不过诗七卷,奏、书一卷,序、记、日录各一卷,跋、赞、铭、启、墓志铭一卷,并无专门学究理论之著。,曹端、薛瑄著述远多于其,吴与弼的特点就更加突出。吴与弼不像曹、薛那样积极参与理气心性话题的讨论,可能也与他不事科举、早年藏书少、与官方意识形态和学术活动存在距离有关。曹、薛皆有功名,曹端长期担任官学学正,薛瑄更官拜侍郎、入阁预事,从交往层次、范围、需要和从事学术的条件来看,吴与弼很长时间内不能与曹、薛相比,他只是在家乡山中刻苦求志。根本上说,康斋“期于成人”的价值追求,有异于曹端、薛瑄,同为儒者,曹、薛倾向于学理化的讨论和借助官府力量有所施为,而吴与弼更重视现实的“人”的状态与成就,具有更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这是他声名著于当时、能与薛瑄齐名的重要原因。
在更广阔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如果说曹端、薛瑄可以视为明初制度渐备之后士大夫从事科举与学术的典型的话,吴与弼则是这种为国家政治笼罩的士风逐渐转变、儒者群体出现分化的一个显例,吴与弼这种大儒的出现,意味着在所谓明中期社会剧烈变迁之前,士大夫群体已经分化。
吴与弼放弃科举、山居自适,如果以明初的士风与价值观念来看,显然是违背主流、甚至是要唾弃的。张佳曾论证多种因素造成的明初士人隐逸风气、士人与明朝的紧张关系以及后者的各种应对措施[6]。为搜罗士人以充国用,明太祖甚至颁布“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例,给士人造成“铁网连山海”的严峻之感。为打击隐逸之风,太祖特作《严光论》曰:
如昔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生民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聘士于朝,加以显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观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报,禀天地而生,颇钟灵秀,故不济人利物……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7]
明太祖毫不顾及他对范仲淹的推崇,痛批获得范文正“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誉的严光,就是要指责不顾朝廷、罔报君恩的士人是“罪人”。而从经过明太祖大力改造过的社会(4)可参考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载《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与士风中成长起来的明初士大夫,怀揣热情和理想,在士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同明太祖高度一致。以靖难殉节名臣茅大方为例,他就沿袭明太祖《严光论》的思想,批评士人隐逸:
山水之乐,士大夫固不可忘情也,然逸游徜徉而流连光景者,又非士论之所许,是故虽有丘壑之胜,林泉之佳,弗敢无事漫游,以旷厥事,乃绘图以为休暇之清玩焉,此画之所由作……窃计山水之间,耕钓之士,其乐固不异于昔也。虽然,士徒知自得其乐,而莫知其乐之所从来,苟人咸溺于山水之乐,则将谁与共治,以致此乐于山水间哉?[8]
茅大方认为士大夫如果流连山水则将无人与君“共治”天下,也就不能再有山水之乐。曹端、薛瑄无疑都是循着这样一股风气,笃实读书科举仕进的(5)薛瑄虽然也认为“道之不明,科举之害也”,但他“主张政府的政治目的和理学家的教育理想是应该在官学教育,乃至科举制度中相结合的。”见许齐雄《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而吴与弼恰恰放弃科举,还每每称赞严光、陶渊明、邵雍这些逸士,谓“慕陶得自然”,“严濑扁舟话举林……细写高山流水心”[1]1047,1069(6)吴与弼研读邵雍作品的直接证据有《夜读康节先生诗后作》(《康斋集》卷1)、《与诸生授康节诗道傍石》(《康斋集》卷4)等,还有其他材料可间接证明。,邹建锋以陶潜诗“隐含着他自己人生价值的归宿,回归自然志趣之意”[9]比吴与弼,可谓正论。克理和甚至推论吴与弼之号“康斋”正得自邵雍之谥“康节”。自称“平生山水心”,“未了平生山水债,寸心遥向七闽飞”[1]1050,1144的康斋,绝不与为国家政治笼罩而重视事功的士风相合。
但是,吴与弼之作为与其说是跟朝廷的对抗,不如说是政治变化的产物。明初搜罗士人是因为士人与朝廷关系紧张、朝廷极缺官吏,而随着社会稳定和科举推行,洪永之际已无须如此,放弃科举虽会影响个人前途,却不会被视为挑衅。如果说永乐帝因吴与弼放弃科举便会疑忌其父吴溥,未免牵强,且正如钟彩钧说,从吴与弼劝父亲将弟弟送到乡下务农的事实看,如果其弃科举是因为抗议靖难,那也不至于将不满扩张到弟弟身上[2]。吴与弼放弃科举时,虽然洪武所遗士风未改,但国家政策已然放宽,明成祖“对热衷仕途者广开门路,有山林之趣者即放之归野”[10]10,吴与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遂求为成人之志、返乡山居读书的。
山居读书是士人求道的通行办法,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特殊意义。明初名臣胡俨说:
余家寓城中,阛阓浩嚷,人事往来,喧嚣尘上无虚日,而余幼从事诗书,日与物接,不得专力肆志,以窥圣贤之阃奥……未尝不嘅想洪崖之幽胜,欲结庐其间以勤所事,然卒牵尘务,不得遂其志也……他日苟得归老故乡,买田筑室于山间,益励余齿,课子孙耕桑读书,为太平之民,日从乡人父老击壤于山林,以咏歌圣天子德化无穷,不亦美哉?[11]

吴与弼执着儒者理想而与明初士风相违,不意味着他全与后者不同。他追求“成人”,依儒家观念,追慕“古人”“圣贤”,隆古称圣,又与明初“恢复中华”的一系列举措或许有所呼应。张佳在《新天下之化》中有专门章节讲述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和部分士人对此的反应(7)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二章《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第52-110页),第五章第一节《士大夫的服饰理念与制度设计》(第217-235页)。。而吴与弼《崔氏默庵偶成》云“旧家文物总诜诜,又喜深衣与幅巾”,《题徐氏村居》云“松篁共听今宵雨,礼乐多存太古风”[1]1023,1066,描述了江西地区一般士人自行追慕古迹的努力,从诗意看,吴与弼对此也是赞许的。天顺年间朝廷征聘吴与弼入京,“中官见先生操古礼屹屹,则群聚而笑之”,李贤解释说“励风俗,使奔竞干求乞哀之徒,观之而有愧也”[13]。吴与弼之父乃国子司业,吴与弼少时曾住南京,与之往来者如梁楘是翰林之子,返乡后与江西地方官员也不乏往来(8)《康斋集》卷5有《赠梁布政》(尊公讳潜,与先君同官翰林):“曾陪崇礼少年游,一隔江湖五十秋。”(第1100页)崇礼是南京街名,梁布政即梁楘。吴与弼与江西地方官员往来,其诗多有记载,此不赘举。,要说不知礼而闹笑话,可能性不大,其特操古礼,即便如李贤所说为励风俗,也未尝不是学术所积。
从吴与弼与明初士风的离与合来看,他并非主动地抗拒或迎合政治塑造的朴素实干的士风,只是他追求儒者成人理想,正好与国家制度渐备、承平日久的历史环境变化相合,所以能够如愿。从这一角度说,吴与弼这种大儒的出现,也是明前期国家变化的产物,他不是唯一的,却是成就最高、名声最大的,他的“成人”之志虽得自其父,有儒者求为圣贤的理想为背景,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却是特殊的。他以自身的性格和生活体验建立发展了康斋学的“成人”,得到广大士人响应,且有娄谅、胡居仁、陈献章等弟子,从而大大影响了明中期儒林,这种情况,也是在一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
三、陈献章与明中期士风转向
吴与弼因科举稳定实行、国家和士人关系缓和得以追求己志,而随着太平日久,科举失意的中下层儒生越来越多,他们需要在国家政治之外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底层儒生需要能够安顿自身、不过于学理化的学说,康斋学正适合他们。
吴与弼门下高徒基本上都是无意科举或科举不如意者,如胡九韶无功名,谢复“弃科举业从之游”,郑伉“为诸生,试有司,不偶,即弃去,师与弼”[4]7241-7242。胡居仁从学康斋后,一生乡居讲学,不事举业,陈献章则是会试不中而从康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当然是因为吴与弼之学与科举考试内容并不一致、“成人”的理想与备考应试的功利取向互相冲突。吴与弼教导陈献章时“于古圣贤书无所不讲”,鞭策陈献章用功时说:“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可见吴与弼不将科举功名作为教育目标。而从弟子们等科举失意后再从学于康斋来看,他们显然也知道康斋之学有别于官方学术、科举内容。白沙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粃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然后益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14]127他是受康斋启迪而恍觉寻常之学不足道、科举之学不足用力。可见以成人为志的康斋学使吴与弼名著当时,吸引了很多人。
从吴氏门人的情况还可见,由于社会稳定、科举常规举行,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底层知识分子和科举失意者。就《壁沼以御獭诸生咸用力焉诗以纪其成》[1]1043、《诸生助移门楼诗以劳之》[1]1088等诗来看,吴与弼门下有许多科举成就不高、家境一般而习于劳作的儒生。吴与弼不止一次给胡九韶写诗,说“故人隐居萝溪曲,残书破砚甘寂寥……躬耕低头秋谷熟,击壤皞皞歌唐尧”,“绿萝溪上旧儒家,修竹乔松去市赊。南亩秋风多熟黍,东园夜雨总肥瓜”[1]962,978-979,胡九韶的家境当与吴氏相近,需要亲事农亩维持生活。陈宝良认为:“通观明代的士风……大体以成化、弘治为界,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5]388,而成弘以后“蓝袍大王”的出现,已经是基层士人泛滥恶化的表现(9)参见赵毅、武霞《明代基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传统士人精神的背叛者》,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吴与弼时代稍早于此,正当基层儒生膨胀之初、士习尚未堕落之时,他的“成人”之学不过分讲求高深的学理讨论,富有理想性和生活性,正适合这些需要安顿自身、在国家政治之外别有追求基层士人,因而得到广泛响应。
娄谅、陈献章、胡居仁等,在为康斋学吸引后,又不满足师说,一个显证是他们思想的学理化程度大大超过康斋。陈献章说:“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14]233所谓“未知入处”,即陈献章通过吴与弼所讲无由可入期望之境,而后白沙自述经过数年独自静坐用功才知“作圣之功”。相对娄谅、胡居仁,陈白沙离康斋生活化的一面最远,理想化的一面最近,影响也最大,康斋白沙师徒的风格遭遇异同,显著体现了明代士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
有关吴与弼和陈献章之间的传授,盛珂提出,吴与弼既学伊川之居敬,又学明道之洒脱,其工夫本就内含张力,而陈献章在读书、居敬、境界上皆有得于康斋,正是康斋工夫中的张力使白沙开出新路[16]。这一观点的确精到,如果结合康斋学“成人”的理想来看,则不仅康斋工夫具有两面性,更重要、根本的是吴与弼本人有这样的两面性,如前文说,他推重严光、陶潜、邵雍,极好山水之乐,但也有“五更枕上汗流泪下”的一面。他晚年的诗作,一面感慨修养不足;一面又颇显从容,显著体现了其紧张与淡然交织纠缠的复杂情感。
吴与弼其人其学的两面性,与明初士风的离与合,使他虽与典型的明初士大夫显著不同,但与明中期以后士人相比,又具有鲜明的过渡性。在陈献章看来,吴与弼既具明前期几朝的风格,又开启了之后的学术,他评价康斋:“其当皇明一代元气之淳乎!始焉知圣人之可学而至也,则因纯公之言而发轫;既而信师道之必尊而立也,则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奋起之勇,担当之力,而自况于豪杰之伦也。”[14]199这应当能代表白沙认为康斋最重要的贡献,即以巨大的勇气和信念,重新焕发了“圣人之可学而至也”的理想。康斋说“成人”,相对成圣成贤而言较缓,白沙则径言“作圣之功”,又将高度提升上来,但“成人”是共同追求,因此二人精神风度也有颇相似。
左东岭从人格心态的角度论述白沙受到康斋的重大影响,并说“吴氏的隐者风范与求乐倾向,引爆了他对人生价值认真思考的念头”[10]112-113,此语实切成人之要。但在《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左先生建立从白沙到阳明的精神脉络,却不纳入康斋。其实,如果更细致地比较康斋与白沙,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更多的相似处。左东岭说:“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常常用诗歌来描述其人生感受与人生理想……出现最多并构成其诗歌主要意象的则有两个人,这便是陶潜与邵雍。”[10]91-92正如前文所说,吴与弼轻于著述,主要也是通过诗歌抒怀,陶潜、邵雍也是他崇慕者。左先生又举例说白沙与康节将所欣赏的乐之境界同喻之为羲皇上人之乐,并推测是受陶潜影响,而康斋说:“北窗一觉羲皇梦,又喜雍容事讲帷。”[10]1071这种相似处固不排除陶潜作为一种象征而具有的普遍意义,但在当时的环境和师承关系中,如此相似的精神和表达,则不能不说有授受之因。
康斋、白沙风格显著相似,但白沙学术成就远过康斋,这与二人家境时遇不同有关系。康斋、白沙共同欣赏的陶潜因《乞食》诗大受王维讥讽,而康斋正如陶潜之窘迫,尝谓:“近晚往邻仓借谷,因思旧债未还,新债又重,此生将何如也?”[11]1293白沙则无此忧,他可以筑台静坐,不理会谋生糊口,讲的道理远比乃师康斋甚至同门胡居仁高深玄远,黄宗羲谓“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白沙之学也符合当时学术发展的要求,毕竟康斋之学理想价值著于一时,在学术尚未发达的明前期尚可应付,但到成化、弘治年间,已不能满足儒林之秀者,也不能有效指导士人修养、与勃发丛出的各种意见争鸣,不足以应对现实社会的变化,结合娄谅、胡居仁、陈献章等弟子都已经不满足师说的情况,这完全可以理解。

同这一情况相应,与康斋门下多科举失意、基层儒生相对照的是,白沙门下不乏科举得意者,王光松统计得出:“在135名事迹可考的门人中,举人40人(不含后来考取进士的那部分举人),进士16人,二者相加56人,白沙门下拥有功名者占事迹可考人数的41.5%。此外,白沙门下另有生员34人,由于举人、进士皆由生员而来,我们可将举人、进士之数计入生员之内,如此,白沙门下的生员达89人,占事迹可考人数的66%。”[17]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因为官方价值再度笼罩了儒生,而是因为儒士大夫价值取向、思想学说多样化,不同风格、思想的儒者成为了体制选拔的精英。

白沙悼先师之文固是褒赞,从旁观者而言,也是一种告别,吴康斋这样大儒怀志负节与官方学者分埒称名的时代已经过去,士大夫张扬奔竞、思想旁斜歧出而与朝廷政治出入纠缠的时代即将来临。与同时代学者对比,康斋无疑是明前期儒者变化的典型,而与后来比对,康斋又像是过渡人物。陈献章引领一时风流,但庙堂之变亦仅初见萌蘖。弘治正德以后,士大夫自身变化与社会现实变动嵌合互动,遂致天下翻然一新世界,世风士行之变,令人咋舌。吴与弼时代成长的陈献章等学者开出成弘之局面,陈献章时代成长的湛若水、王阳明等学者则开出正嘉之新风,社会与儒者变化之迅速,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社会的活力与儒学的生命力、创造力。明史的分期、明儒的地位,正是在回顾与重新审视中建立的,无论是吴与弼还是陈献章,他们历史意义与地位的评价总与后来者联系,在阳明学倾动天下、绚烂神奇的晚明时代展开以前,他们既是节点,也是端绪。
四、结语
吴与弼躬行践履、讲学授业,以“成人”为志的康斋学名著于世,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儒家固有的成就圣贤的理想与国家政治、政策变化结合的产物,早于明中期以后社会的剧烈变化。不过吴与弼生长于洪永,学成于宣德以后,身上明初之风尚未脱尽,学术较为粗疏,由于家境艰难,其康斋学实践工夫的生活化特点也非常明显。康斋在体制之外重振成人理想、与明初士风的离合,正适于明中叶剧变之初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儒生,同时也开出陈献章一路。从康斋到白沙的转变,鲜明体现了明代儒学的深化和儒士大夫群体与社会的多元化转变,康斋学和白沙学是这一转变的开端和过程中的典型,对儒士大夫群体的转变与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从朝廷放松控制士人、无法容纳大量士人,儒者追寻国家政治之外的价值理想,到思想学说多元化的士大夫进入国家政治,儒者并非是一完全被动的群体,儒者的变化早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依赖儒者、选拔儒士大夫的国家政治由此也不可能不发生改变,在明初严密控制的体制破开之后,客观上其主动作用愈来愈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治的变化和社会面貌的塑造。儒者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坚持成人的理想,研究学理,应对现实,大大拓宽了学说实践与政治施为的空间,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思想学说,虽因革损益,各有得失,但终皆彰显了儒学本身的潜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