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词与李清照词花意象之比较
黄于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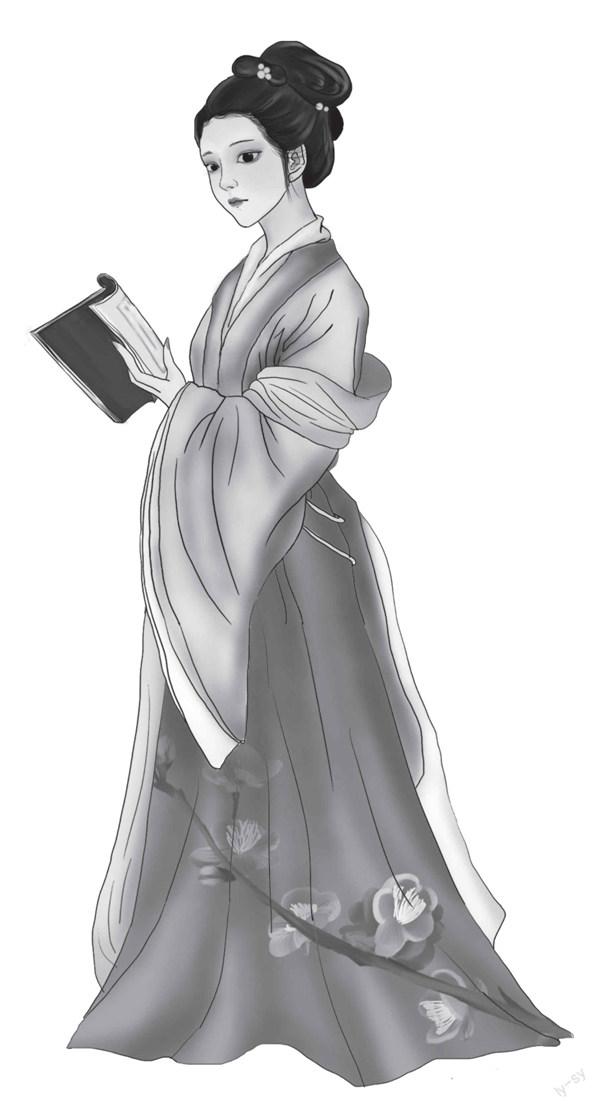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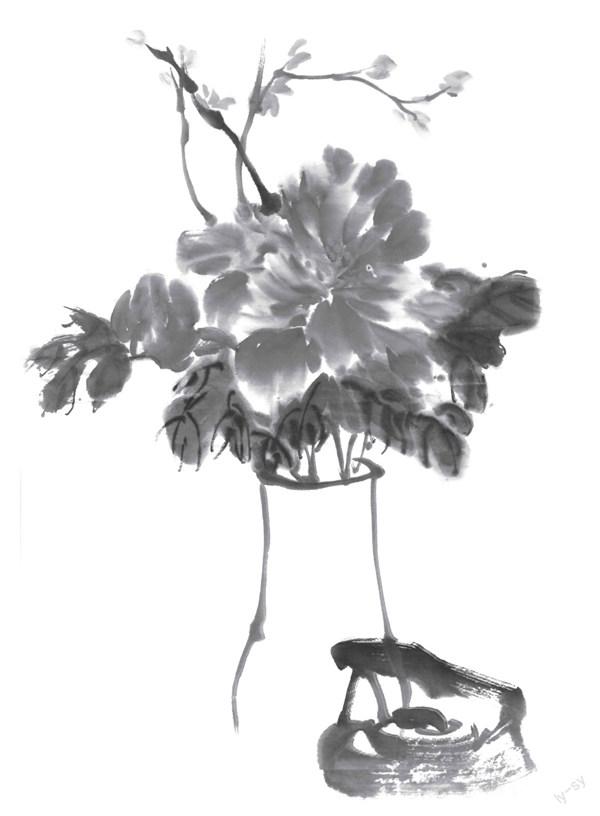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通过分析作家作品中的常见意象,可以为我们搭建起深入作家人格个性与情感体验的桥梁。秦观与李清照是宋代词坛上“婉约”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都喜欢选用自然界中的意象来营造清幽深婉的意境。其中,花意象是秦、李二人词作中贯穿始终的意象。据笔者初步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秦观词集》收秦观词九十六首,有五十二首涉及花意象;王仲闻的《李清照集校注》收李清照词六十首,有四十一首涉及花意象。由此可见,花意象是秦、李二人笔下最为重要的审美意象之一,本文拟从表现形态、抒情特点、题材内容等角度对二人词作中花意象的差异进行探讨。
一、表现形态差异:无名花与有名花
秦观选用的花意象种类丰富,形态多样,但少有大量吟咏同一种花的情况。在统计的五十二首涉及花意象的词作中,有近三十首出现的为无名之花,多为“飞花”“落花”“残花”“乱花”等。譬如,“自在飞花轻似梦”“红成阵、飞鸳甃”“飞红万点愁如海”“落红铺径水平池”“回首落英无限”“满目落花飞絮”“满庭芳草衬残花”“乱红如雨”。秦观写花,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偏爱的品种,他最为关注的大多是花枯萎凋谢、随风飘落的状态。同样是花的凋残,秦观却能以落花承载各式愁思,描绘出无名落花的千姿百态,使其具有一种清冷孤寂的美感。
与秦观不同的是,李清照喜欢在词作中表明所用花意象的品种,用来描写的词句也多与此类花的特点相配合。在统计的四十首涉及花意象的词作中,有十四首词出现梅花意象,四首词出现菊花意象,另有咏荷花、海棠、梨花、桂花等各二或三首。由此可见,在李清照选用的花意象中,梅花是她最喜欢吟咏的对象,同时,她在菊花、荷花、海棠、梨花、桂花等对象上亦倾注了较多的情感。
李清照喜作咏梅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玉楼春·红梅》《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清平乐·年年雪里》《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临江仙·梅》。此外,她还喜欢吟咏东篱之菊,如《多丽·咏白菊》《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另有佳作咏桂花如《鹧鸪天·桂花》,咏荷花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咏海棠花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相较于秦观而言,李清照喜欢且擅长吟咏名花,在她笔下的,寒梅、瘦菊、金桂、红棠等花意象既没有脱离原本的特点,又被充分赋予了个人特色,咏花即是咏人,花意象与词人的形象高度重合。
二、抒情特点差异:婉中有曲与婉中见直
秦观与李清照虽同为婉约派代表,但二人的抒情特点却不完全相同。透过词作中的花意象,我们可以感受到:秦观婉中有曲,含蓄婉转,显露细腻幽微的“女儿情”;李清照婉中见直,大胆抒怀,表现率真爽朗的“丈夫气”。
秦观成长于温柔多情的江南,早年的生活环境使他形成了细腻纤弱的性格,后来仕途又遭多重坎坷,更是让他变得敏感脆弱。金人元好问曾指出秦观作诗乃“女郎诗”,词亦然,秦观的词往往比其他男性词人更多了几分柔婉哀怨的情思。他最喜使用的各种花意象,正是那份“女儿情”频频流露的重要标志,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词中的点点落红与憔悴的杏园,无不透露着词人的失意与伤感。词中数次提到花,地上凋落的花、园中憔悴的花、手里轻捻的花枝,那份忧愁与落寞在花与花之间流转,词人如女子一般委婉细腻的情思也随之传递到了读者眼前。前人从以婉约为主的传统观念出发,以秦词为“词家正音”。宋人张炎认为:“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秦观词真实地反映了秦观个人的情感体验与生活经历,清丽的语言下流动着婉曲细腻的情思,然而过于纤细柔弱也成为了秦词的一处弊病,那些见于词作中的消极颓丧的心理难免折损了丈夫本色。秦观词作中的花意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尤其是那多次被提及的“落花”,无不是词人消极心曲的象征。
李清照自幼生长在一个自由开明的书香之家,她大胆奔放、自视甚高,为人处世颇有男子气概。近人沈曾植曾赞美李清照“倜傥有丈夫气”,并认为她“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由此将她与秦观的气质区分开来。李清照爱酒,与酒有关的意象在她的作品中频频出现,充分体现了她身上那一股洒脱不羁的男儿豪情。而她使用更为频繁的花意象,实则也透露着她“大丈夫”般的气节与胸襟。李清照将酒意象与花意象结合,造就了不少经典之作,其中的名篇如作于李清照出嫁未久之时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词人与丈夫分隔两地,佳节已至,思念倍浓。下片却融入陶渊明之意旨,“东篱把酒”“黄花比瘦”,莫不道出其自比于陶渊明的高洁傲岸与飘然超逸之态。可見李清照在思念丈夫之时,全无寻常女儿家的柔弱之态。她晚年所作的《声声慢》中,仍有“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哪怕经历了亡国之恨、丧夫之痛与孀居之苦的接连打击,她胸中的那份清高与飒爽也从未被磨灭。“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自古以来颇多名士借以自喻,李清照身为一名女子,借此君子意象抒发内心胸怀,可见其思想与情感皆有男儿风姿。
三、题材内容差异:专抒个人情志与另具家国之忧
秦观的前半生对应着词创作的前期,这一阶段以写艳情为主,多为表现伤春悲秋或相思离别之作,风格清丽柔婉,词中所咏花意象大多蒙着一层淡淡的悲伤和浅浅的哀愁。他以落花写男女欢会后的相思别离之情,如《八六子·倚危亭》《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也借落花表现对春光已逝的伤感与年华老去的无奈之情,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有时,他还写细腻幽微的闲愁,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直至旧党被彻底打击,秦观被一贬再贬,心境随之走向低沉,羁愁逐渐被他巧妙地融于艳情之中,作品转为传达政治失意之苦和贬谪流放之悲,其咏花之语亦凝愁含恨,如《千秋岁·水边沙外》,他将漫天飞舞的落花比作大海,以海之深广喻其哀愁之深广,道出了今不如昔的哀愁。贬居郴州时,他创作了两首《如梦令》来抒写自身与命运抗争的无力,词中均有对落花的描写,“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满目落花飞絮。孤馆悄无人,梦断月堤归路”,由春归到人归,平常词句却见感伤无限。
李清照少女时期的词作中尽显她天真烂漫的少女情怀,如分别咏荷花与海棠的两首《如梦令》,充分展现出了其少女时期的生活画面与思想情趣。待到少妇时期,家庭的变故使得李清照与丈夫常常分隔两地,令她饱尝相思之苦,因此创作了数首词来抒发与丈夫分别的苦楚、独居的寂寞以及对丈夫深切的思念之情,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正象征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词人借此道出了寂寞心曲。此前两个阶段所描写的花意象与词作整体风格相洽,多表现伤春、惜春之情与她的闺思闲愁。直至“靖康之变”,李清照的美好生活彻底破灭,山河破碎,家园不再,夫妻二人阴阳相隔,磨难接踵而至。她词作中的情感也由抒写孤寂与思念转为对亡夫的深切悼念,表现出未亡人处境的孤苦凄凉,更有部分词作体现了浸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故国之思与忧国之情。以咏梅词中佳作为例,如《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此时的李清照已经历了“靖康之变”,在南方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鬓上残破的梅花和着早春的乍暖还寒,勾起了她对故国的思念,这鬓上残梅既是她漂泊零落的化身,又是愁苦离恨的积淀。此外,李清照词中还有许多梅意象见于《玉楼春·红梅》《满庭芳·小阁藏春》《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清平乐·年年雪里》等作品。这些梅意象的情感内涵随着李清照的生活遭际不断变化,从早期的清高孤傲、不屑与世俗合流到南渡后对故土的深深思念,再到丈夫亡故后道不尽的缅怀,最后到晚年寡居漂泊的苦闷凄凉,更有甚者,还糅合着对个人身世的感叹和国家命运的忧虑。
总而言之,李清照的出身高于秦观,家境上的优越带给了她自信大方的气度,这是秦观所不及的。秦观的一生中,只短暂度过了一段安定生活,在其余的时光里,他不是在四处漫游就是因贬谪而流落凄凉之地,正如所咏“落花”之飘零。秦观又是幸运的,他虽不曾拥有李清照前半生那样的安定幸福,却也没有像李清照那样经历国家的山河破碎,经历与爱侣的阴阳相隔,这也是秦观咏花词较李清照咏花词少几分内蕴的原因。然而,秦观咏花词中所渗透出来的悲痛有时却更甚于李清照的咏花词。王国维曾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被视为“古之伤心人”的秦观总是在词作中努力呈现自身近乎极致的痛苦,却又不能畅快直言,只好发出一声声凄厉隐忍的哀号,这表明他抒写个人情志已达平常人所不及的境界。
从词自身的发展阶段来看,秦观在前,李清照在后。秦观词多承柳永词而来,虽取境造语雅于柳词,其婉约纤柔之态却难减半分。李清照经历“靖康之变”后,国破家亡、漂泊流落的巨大打击使得她词作的内容和风格也随之改变。这种变化不为李清照所独有,在词坛上,民族危机使得众词人的创作无法封闭在个人情志和男女爱情的狭小空间里,而必须直面苦难与现实,传统的婉约词风不再适合当下的时代,豪放詞风因此渗入“婉约”一派。后期的李清照词正是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生发出了更为苍凉大气的情感,其中的花意象亦承载起了厚重深沉的家国之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