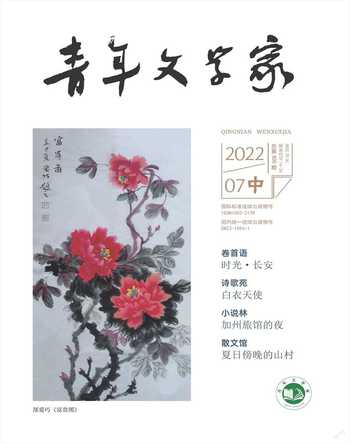东东与丑丑
焦辰东
一
白云在睫毛间,耳听车喧,偶感春风拂面,这里的她和她是寂静的。
东东是奶奶在家唤她的乳名。约定俗成,每周五,东东的奶奶蹬着铁皮三轮车来接幼儿园里的她回老家。车斗子里铺了一塊红色主调的卡通褥子,略为长方形,东东躺上去总觉得小。角落有个盘活了的小木凳,东东总是攥着它,怕它滑向自己,却从没坐过。她躺在那儿,小脑瓜儿一定在想些什么,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碧云天、黄花地。偶尔同一辆自行车并行,俯仰间横生亲切,东东的笑还没落下,那人便向前去了。“奶奶快点儿超过他。”没等来应和她便又想别的去了。
说来奇怪,路两旁树木郁郁,却鲜少听得到鸟儿欢腾。想来或许是它们在高处飞着,又或是掩在了参差的链条和轱辘声里。翻来覆去累了,便平躺着,蓝色的底片和悠然的白云在一起,似乎有天然的催眠感。奶奶蹬车像在上发条,将云朵连同余光里的树拨转流动,便使她抵不住困意。路上有座桥,东东每次都是在桥上睡着,好似有什么自然的魔力。过了桥便是属于东东和奶奶的呼应。“东东。”“诶。”这大概是怕路上颠簸丢了。“东东。”东东扯扯她的衣角或碰碰她,睡意沉沉,没有气力出声。再骑一段路奶奶索性回头看一眼。再一声“东东”便到家了,这句在耳边听来的,有一股清凉气和沉木香,这大概是东东没有起床气的缘由。奶奶一路除了三声“东东”再没有开口说过话,似乎在铆足了劲儿蹬车,东东也习以为常地自顾自。偶然醒来,东东眯着眼透过略显湿润的睫毛,那种蒙眬的穿透感被阳光拿捏着,红彤彤又明晃晃。
上小学的第一个周五,奶奶去幼儿园接东东,等到放学也没见到,不知怎的想起来上了小学,便找去了。东东是在那儿等着的,自个儿找了处显眼的地方,看样子小家伙没有着急,她应是觉得奶奶一定会来接,只不过今天慢些罢了。不知道的是,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路,奶奶耐着性子奔得汗流如雨。一如往常,云朵追不上躺在车里的东东,想了个把她哄睡着的法子。
“一度春来,一番花褪”,没有谁的告知,奶奶再没骑三轮车来过城里。三轮车也当老物件在门筒搁置着,成了东东回老家迎着“别弄坏,鼓捣个别的”的叫停声中也要蹬两下的玩具。也是没什么预告,三轮车的铁皮生了锈,链子坏掉了,然后是车带,岁月慢慢爬满了它的身体。在可视的空间里,悄悄然消失不见。奶奶,应该和东东一样,时常想起它吧。不,应该是很怀念,那是她年轻的时光,和东东在一起的。但她不太擅长讲从前,东东也没想着打听,只是学着奶奶当初的沉默式陪伴,可用什么载她呢,东东觉得,得放在心上好好想想了。
流水年华春去渺,东东学会了自己坐大巴车,她说车身总是斜的,像奶奶的身骨。奶奶大多时候是拎水桶往瓮里储水,单臂得力故患于不均。每逢周末,东东总爱把有的没的书都装回去给奶奶看,很沉,所以她总坐车身翘起来的一边。
车里有一些钱味儿,让人既混沌又清醒,在路上的东东再没睡着过。
二
满身星月的光,众人宣讲,常是聚在过道,这里的她和她们是热烈的。
丑丑是姥姥家喊的小名。丑丑的姥姥房子临着街道,那时候还没铺路,门前就是土地,冒着几棵花草,白天的烈阳下显得颇有生气。到了晚上左邻右舍都来,多是姥姥辈的,还有孩子和妇女。丑丑的姥爷常在人群外坐着,像暗影守护者。他有自己的椅子,宽大而老旧,可以让人半躺着,丑丑没有上去过。丑丑奔跑的时候总趁机摸一把,在姥爷缓缓抬手间跑开了,却跑不出姥爷铺陈的目光。姥姥提前铺好毯子,几个自带的板凳,圈定了一个热络的生活场面。大人们和孩子们有一样的活力,白天各为生存找活儿干,丑丑猜她们的身体是疲惫的,但她没猜透这段晚间活动有什么魔力,使她们饶有兴致。
丑丑在乡下住得少,大多不认识谁是谁,好在这些人认得她,她想那些说她变好看的,一定是在哄她,不然怎么还认得出呢。她和这些长辈在一起,她是满心欢喜的。他们笼络着整个村子的琐事闲杂,即使在她长大后,也觉得话里话外有世俗的风趣,更何况那时的她,对这浓烈的烟火气,有听不懂也抹不掉的好奇。
听得累了,也插不上话,丑丑便在几个小伙伴间钻个空子,嵌在褥子上。目光在繁杂的碎花汗衫和凉鞋间跳跃,偶尔有车子慢悠悠地骑过,就能听到几声清朗的“干嘛去了?”“回去呀!”“歇会儿啊!”她猜他们霎时间,趁着月光看不清是谁,所以总是在那人走后谈论。丑丑说希望老了下班回来也有一群人这么问她,她一定支上车梯,让众人听听她当天遇到的奇事。美美地胡思乱想着,一个扣掌猛地扣到丑丑身上,丑丑也迅速拍上了那只手,姥姥笑着张手给她看空空的战果,姥姥总是这样,把蚊子吓个半死。
丑丑亮着眼看着天,姥姥拿着蒲扇到处扇着,任乡音在空间里悠扬着。她自顾地想着,闭眼之前天上的这几颗星星,睁眼后一定还在。偷偷地,左眼、右眼一起,再来一次,每一次都暗自窃喜。直到星点慢慢涣散成一个光圈,在睫毛的开合间粘连,直到没气力睁开,星星一直都在,周遭有风徐徐。
丑丑心里想,要熊熊不灭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