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薹
张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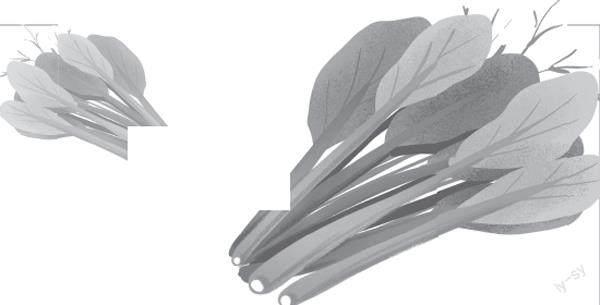
入春后,餐桌上如果菜薹缺席了,那肯定是件很遗憾的事情。菜薹有紫菜薹和青菜薹之分,紫菜薹似乎有些高贵,而平民化的、接地气的还是青菜薹。
刚过完年,阿亮通过微信叫我去吃午饭。我和阿亮是铁哥们。他每天下班后觉得无聊,索性去郊区租了一间房子、一个池塘和一块地,周末或者节假日拖家带口地去一个叫八里桥的地方住,塘里养鱼,地里种菜,在假日里享受归园田居的生活。
那日淫雨霏霏,我也不开车,穿上雨衣,蹬着共享单车就去了阿亮那里。雨下得不大,风也不大,我拼命地蹬着车子,雨衣哗啦啦地响著,像是在给我加油鼓劲。从城北到城南的八里桥,骑单车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细雨中,阿亮坐在塘边的大黑伞下垂钓,他媳妇打着伞,正在打菜薹。
菜农收获蔬菜的时候,其劳作多半是粗动作,比如收获辣椒,曰“摘辣椒”;收获韭菜,曰“割韭菜”……唯有收获菜薹是细得有点高雅的动作,曰“打菜薹”。如果用剪刀剪菜薹,或是镰刀割菜薹,就如同冒失鬼求婚,很粗俗,很唐突。
菜薹最适合细雨绵绵的天气打,打菜薹的人如阿亮媳妇这般,左手举着伞,白嫩的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微触花茎,轻轻合拢,手腕稍微动一下,就能听到花茎“嘎嘣”的断裂声。记得过去听过江南有首歌——《采茶舞曲》。每当收音机播放这首歌时,我脑子里兀自想起少女们那美丽的身影。微雨中打菜薹,要比采茶更有诗意和浪漫。这一带就有一首民歌叫《打菜薹》,表达的是少男少女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
我与阿亮寒暄过后,收杆回去,钓到的鲫鱼和昂刺鱼在塑料桶里蹦跳着,野味里多了一些情趣。
那日桌上的菜不多,都是他家菜地里和池塘里产的。阿亮媳妇没有清炒菜薹,她只是把菜薹清洗一下,过一下开水捞出,像卖菜一样整齐地码放在白瓷盘里,撒点盐,浇几滴芝麻香油,就端上餐桌了。酒酣之后,阿亮问我:“啥菜最合你的意?”我说:“都不错,不过若非要选出最佳的,当然要数菜薹!”
阿亮以为我喝多了,因为那盘鱼是他费了一番工夫做的,我却没有选。他骂了句:“你小子这辈子就只知道‘菜薹了。”也许是我过年吃多了鱼肉,想用蔬菜来刮走肠胃里的油脂,确实更喜欢阿亮媳妇做的菜薹。
初春的菜薹,花蕾鼓胀着而未破,叶翠绿,茎脆嫩,那正是菜薹的“花样年华”。初春是吃菜薹的最佳时机:早了,无薹;晚了,花一开,茎就老了,味同嚼蜡。凡果蔬,宜时食,过了季节本味去远。元代苏州昆山诗人吕诚,一到初春之时,一日买一把菜薹乐而食之!他在《谢惠菜》一诗中写道:“江乡正月尾,菜薹味胜肉。茎同牛奶腴,叶映翠纹绿。每辱邻家赠,颇慰老夫腹。囊中留百钱,一日买一束。”
春天,大地馈赠给人们很多食材,而菜薹,无疑占据了主角的位置。
编辑|郭绪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