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劲儿!
[英] 莎莉·特纳

生孩子这事让我着迷。虽然十六年前看电视剧里的女演员生孩子曾给我带来了小小的阴影,但怀孕时我无比期待将来给别人讲我的生产经历。分娩是成为母亲最正式的仪式,我迫不及待地要赢得“我生了孩子”这枚奖章。
当别人问我“生孩子是怎么样的”或者“真的很痛吗”时,我给他们最坦诚的回答就是:这取决于你问我的是哪一次。如果在亨利出生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会是个很正能量的故事。而如果在祖德出生后写,故事则会非常短。
亨利的预产期是2月13日,但我是在预产期的第二天开始分娩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詹姆斯用他手机上的子宫收缩计时软件监测我宫缩的规律,我则坐在健身球上随着球弹跳。我们在卧室里没完没了地聊着要带到医院去的东西是不是装全了。接着,我有了我自己的“嘻哈秀”——小便失禁,听起来似乎有趣,但其实挺恶心的。就在那时候,我的羊水破了。很快,我开始狂吐。詹姆斯赶紧把呕吐物从新沙发上擦掉,而我用恨不得杀了他的眼神盯着他:“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沙发?我马上要死去活来地生出一个3公斤的孩子了!”这好像还不够乱,更奇葩的是,通过看我身体里分泌出来的东西的颜色,我判断:“这孩子在我的羊水里拉屎了!老师在课上讲过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马上收拾东西去医院。路上,除了这个脏兮兮的娃在我子宫里抗议之外,我的血压正在飙升。我在医院做第一次检查的时候,被证实患有先兆子痫,一堆医务人员在产房里双眉紧锁。不过,除了宫缩加剧让我不能好好地和詹姆斯聊聊他在医院随行包里都装了哪些零食之外,我感觉还挺好的。我发现分娩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以忍受,而且,经过了不太疼的几个小时后(感谢无痛分娩针),当我错认为我要拉屎时,亨利不大费劲地自然降生了。“你真棒,宝贝儿!”詹姆斯对我说。
我确实不错。生理上,我没在生孩子的时候大便,精神上也没有过度紧张。在生祖德之前,我一直对好奇的朋友们说:“生孩子真的没那么糟糕!”
两年零七个月之后,我第二次生孩子。如果第一次生孩子我因为淡定获得过奖章,那这一次奖章肯定会被收回。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为这一次我什么事儿也没有,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先兆子痫,因此医院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轻松。人人都说生二胎更容易,我也完全信了,我毫不怀疑这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回想起来,这真是个愚蠢的想法。
事实是,我生祖德几乎花了比生亨利多一倍的时间,而且要痛苦得多。第一次分娩中那个镇定从容的女人,在第二次并没有出现。詹姆斯对于我生祖德的评价是:“你像个神经病。我从来都没见过你这样。”分娩过程中,我扑通一下跳进分娩池,希望能在水下安静地分娩,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从水里狼狈地冒出来,大叫着: “快想个有用的办法!”詹姆斯竟建议我在水里再坚持一会儿,我恼怒地对他吼道:“我需要的不是在一个巨大的澡盆里泡澡!”我想要来个无痛分娩,然而我被劝说不要用无痛分娩。助产士对我解释说婴儿在一两个小时内就会降生了,使用无痛分娩反而可能耽误时间。詹姆斯同意了——他認为我可能刚好到了那道坎儿,孩子大概马上就出来。此前我已经二十四小时没睡觉了,筋疲力尽的我在宫缩的间歇坐着睡着了,像只受伤的动物一样呻吟着。詹姆斯后来告诉我,有几个小时我都拒绝说话,在床上静静地坐着摇摆身子,偶尔瞪他和可怜的助产士一眼。我当时真的在想我是不是疼得快死了,死了就解脱了。
接着是整个分娩过程中我的不合作:当子宫口已经扩张到差不多十厘米的时候,我开始了我平生最无意义的罢工——我拒绝使劲儿。“我要无痛分娩!”我哀号着,并不是针对谁,所以也无人理睬。“我要剖!”“我想死!”每个人都开始担忧了。我假装在使劲儿,嘟囔着:“我在使劲儿!”其实完全没有努力。不过我最后还是走上正轨,开始真使劲了。三个小时后,当我感受到那熟悉的想要拉出一个炮弹的感觉时,祖德终于出生了。
终于解脱了。我记得我把裹着小毛巾被的祖德抱在怀里的情景:他看起来很可爱,粉嘟嘟的。一切都结束了,我太高兴了。可是接着,胎盘卡住了。我甚至不知道还会有这种可能性。电视上人们生孩子的时候胎盘从来就不会卡住,不是吗?可是,说什么也没用,我的就卡住了。有位医生谈到脊柱麻醉和手术室,还有医生几次尝试移动它,詹姆斯用来描述这个场景的形容词是“残忍”。
胎盘出来以后,是真的都结束了。我和詹姆斯美美地吃了一顿下午茶,然后我出院了。我以为事后我会对生祖德时的混乱开玩笑,比如:“这真是个噩梦!”“相信我,我有个卡住的胎盘!哈哈!”可事实是这经历让我心有余悸,以至于时至今日我提都不想提。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听过太多关于生产的故事了,从痛苦吓人的紧急剖宫产,到快得不可思议地在医院停车场分娩。读得越多,我越坚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怀孕分娩经历是相同的。每一次分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女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都可能不一样。不过仔细想想,我毫不怀疑助产士们什么都见过,所以如果我们当时确实十分崩溃,大概没必要太埋怨自己。
(摘自《我是新手妈妈》,出版:中信出版社)
《成为母亲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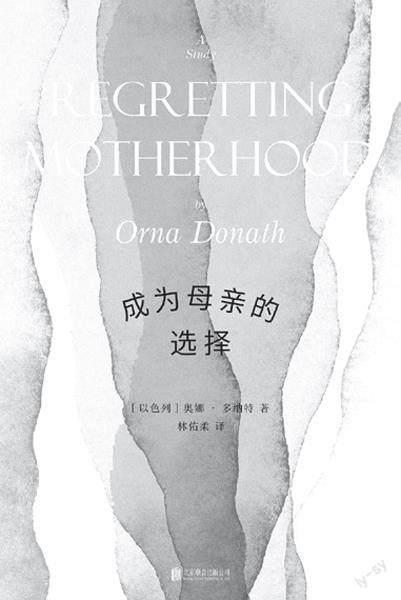
作者:[以] 奥娜·多纳特
译者:林佑柔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如果能带着现在所拥有的认知和经验重返过去,你还会让自己成为母亲吗?”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聚焦“后悔生育”的话题,采访23位已为人母的以色列女性,追溯了这些女性成为母亲的历程,分析她们在孩子诞生前后的情感世界,调查她们如何认知和化解生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后悔并非不存在,只是不被允许言说。本书用女性自己的声音,展现了立体、复杂的母亲形象。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作者:[美] 凯特琳·柯林斯
译者:汪洋 周长天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一名职业女性成为妈妈,她必然要面临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冲突,这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本书告诉我们:不!
本书以美国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选取了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其中的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的社会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