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之歌》的悲剧空间与伦理困境
陈依
摘要:法国新锐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代表作《温柔之歌》立足于空间的延展性,通过多层次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展现权力对象的痛苦如何被生产;以空间为主体来构建伦理困境,又以伦理为视角考察空间形态,经由住宅的微观空间观照当代法国社会问题的现状,利用空间叙事深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意义探究,为阶级矛盾更新表现视角,拓宽表现场域,呼吁空间中的人文关怀,解读小说故事背后所传达的社会和人文价值。
关键词:《温柔之歌》;空间叙事;伦理困境;阶级矛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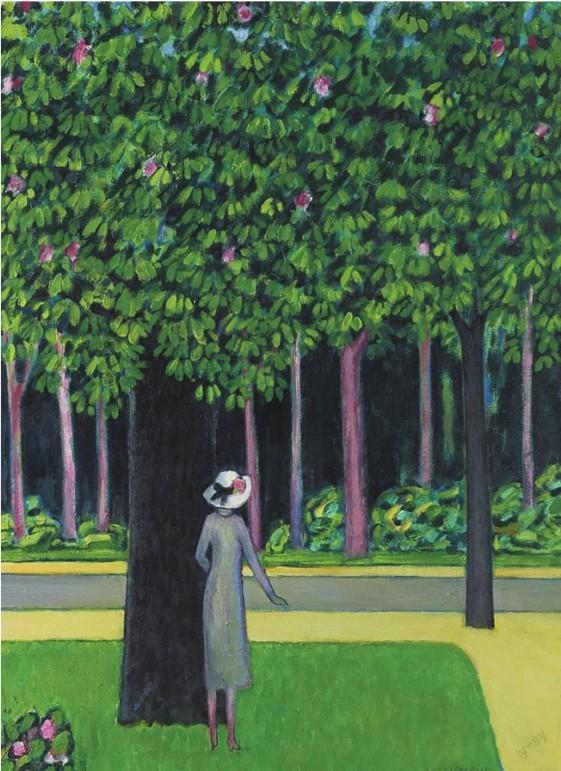
《溫柔之歌》的作者蕾拉·斯利马尼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一个富裕之家,自幼热爱文学且涉猎广泛,曾追随茨威格的足迹横跨东欧,对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是情有独钟。她17岁到巴黎求学,开始认识到女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存状况的巨大差异,并逐渐运用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和反思法国的阶级问题、贫困问题、性别不平等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
曾经是职业记者的经历,使得蕾拉·斯利玛尼擅长从真实事件中获取写作的灵感,《温柔之歌》取材于美国的一则真实社会新闻。事情发生于2012年10月,在纽约的一个波多黎各裔家庭中,保姆亲手杀死了她看护的孩子,而保姆对杀人动机却讳莫如深。蕾拉清楚地记得报道中有一张保姆与全家人的合影和这家雇主的一句话:“她是我们家的一分子。”[1]这深深触动着蕾拉,并促使她创作《温柔之歌》。
《温柔之歌》是一部描写人性悲剧,反映当今法国社会深层阶级矛盾的小说,讲述了一位“仙女保姆”是怎样在精神危机的推动下谋杀了雇主的两个孩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小说中刻意打破时间线性的传统叙事,空间化特征十分凸显,尤其是开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个去处”的引用,足以证明斯利玛尼在小说中有目的地采用了空间书写策略。
随着人类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空间性问题和空间化趋势日益凸显,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受着后现代空间概念的挑战。本文尝试以亨利·列斐伏尔等人的理论为依据,探究《温柔之歌》中多层次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揭示出在空间等级秩序的暴力逼迫下,权力对象的痛苦如何被生产,又如何整合其伦理表达,以期对小说的现有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一、空间引发的身份危机
“小男孩死了。只用了几秒钟”“小姑娘……喉咙里全是血”[2]。《温柔之歌》以倒叙开头,两个孩子的死亡已成定局,没有给故事结局留下悬念,而是把悬念赋予了保姆的杀人动机。保姆露易丝进入雇主马塞夫妇的家庭,帮助他们照顾大女儿米拉与小儿子亚当,她被夫妇俩赞为“仙女”“天使”,“好到不真实,像从童话书里冒出来的一样”[3]。然而,露易丝心底的阴暗,却在日常琐碎中一点点地发酵,正如影视剧《甄嬛传》中曾说:“温柔刀,刀刀割人性命。”等马塞夫妇有所觉察时,为时已晚,他们的一双子女最终成为变质关系的牺牲品。露易丝的犯罪动机自始至终未在文本中得到确凿地呈现,读者需根据字里行间的细节自行拼凑想象。
在雇主家里,露易丝业务精熟,任劳任怨,甚至主动承担分外的家务事,其优异表现也换来了雇主的高度赞扬,“虑事周密,心地仁厚。”然而,在私人生活中,露易丝却表现出大相径庭的另一面。她热衷于勾起丈夫的怒火,讨取他的羞辱与殴打,她也会对女儿斯蒂芬妮施以暴力。“她打在她眼睛上,辱骂她,把她抓出血来。等斯蒂芬妮不再动弹时,露易丝啐在她脸上。”[4]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她(露易丝)打开入户的小门,把门在背后关上”[5]。被门所分隔的独立空间也创造出了泾渭分明的叙事空间,伴随空间的转换,体贴而温柔的“仙女”保姆化身为带有被虐与虐待狂倾向的心理病人。对立的空间结构也建立起对立的人格,个体被空间进行了颠覆性地重构与改写。
《温柔之歌》中露易丝的双重人格,可以说与她生存体验中的阈限空间息息相关。从物理空间上来说,露易丝始终在她工作的中产阶级社区与她居住的贫民窟之间生活,这种生存状态导致她呈现出强烈的边缘品质与混杂意识。
正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所指出的那样:“人从本质上就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6]不同空间的区隔制造出了一种生产机制,会影响、改变甚至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无论是生活空间的设置还是地理空间的位移,都将直接影响人的身份意识与主体诉求。
在伦理空间中,露易丝同样带有由两种社会身份所引发的异质感、错位感。中东剧变后,大批难民持续涌入欧洲,法国作为北非穆斯林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先后对移民进行了同化、融合和归化的努力,但结果并不理想,法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移民沦为无产或贫困阶层,露易丝的保姆同行们大都是移民或少数族裔。露易丝身为白种人,瞧不起这些“纸面上的法国人”,但这些人也一样对露易丝嗤之以鼻,“(她)装得好像是宫廷嬷嬷、大总管、英国女护士似的。”[7]露易丝虽颇具种族优越感,但她低下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使她生活在现代法国的“平行社会”“折叠空间”里,常常备受歧视。在露易丝的女儿斯蒂芬妮的视角中,母亲总是卑躬屈膝,甚至会在她与雇主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叮嘱她不许出声,“你要是玩得太过,人家会不高兴的。”
社会阶级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上,还表现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一直生活相对优渥的马塞一家,与贫困拮据的路易丝之间在消费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丈夫留下的巨额债务,银行将房子作为抵押偿还债务,路易丝不得不住在出租屋里,所以,经济窘迫的她无意识地将自己节俭的生活方式带到了雇主家里。路易丝会要求孩子们将食物吃得一点儿也不剩,也会骄傲地向米莉亚姆推荐她收集的促销券,然而保姆的这些行为在雇主马塞夫妇眼里看起来是十分愚蠢可笑的。总之,露易丝既鄙视边缘人,自身却又处在主流社会视角的边缘地位,被双方双向视为“他者”,难以在社会中找到合适的自我位置。
露易丝智识低下,也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升通道完全被堵死,丝毫看不到改善生活的希望,只能够通过偶尔的梦幻去超越现实。“她款步慢行,细瞧着来往的女人和展示橱窗。她什么都想要。”“她幻想着一种应有尽有的生活。她可以对某个谄媚的柜姐指点她中意的那些商品。”[8]可当她的雇主米莉亚姆撞见露易丝在橱窗前的身影时,产生的感觉却是:“(露易丝)像一个弄错了故事的人物,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世界,注定要永远地流浪下去。”露易丝和现代社会的商业街道是如此格格不入,对她而言,“巴黎就是一面巨型橱窗。”斯利玛尼笔下的“橱窗”重现了福楼拜笔下的“窗户”,《包法利夫人》中贯穿文本的“窗户”的意象,就象征着爱玛能够观看却永远无法触碰的一切,而这一空间的体验,也为露易丝带来了与爱玛相同的伦理困境,她们存在于“窗户”的异质空间中。福柯认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根本相关,毫无疑问,它比时间带来的焦虑更甚。”[9]露易丝日益加剧的焦虑就在于,她始终无法在某一固定的空间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且由此造成了精神上的危机。社会阶级差距给路易丝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冲击和碰撞,为路易丝的伦理困境埋下了种子。
二、住宅空间导致的伦理性缺席
从一开始,使露易丝与雇主马塞夫妇间的关系得到确认和加深的,正是露易丝突破空间、改造空间的能力。马塞夫妇并不属于富裕阶层,甚至在中产阶级里都处于下游。“想要在紧急情况下申请补助的话,他们太有钱了,但想要宽裕请一个保姆,他们又太穷了。”[10]他们位于巴黎十区的公寓并不宽敞,尤其在有了两个孩子后,更显狭窄。露易丝初次进入这所公寓时,“她观察着每一间房,如一位将领在即将被自己征服的领土之前那样沉着”[11]。很快,马塞夫妇就感受到了露易丝对空间非凡的掌控力。“她肯定是有魔法,才能把这一间拥滞、窄小的公寓变成一个宁静敞亮的地方。露易丝把墙推开了。她把壁橱变深,抽屉变大。她让光照了进来。”[12]马塞夫妇获得了久违的幸福感,露易丝也从中得到了成就感,“沉默的公寓已如一名仿佛在恳求她宽恕的敌人,尽在她的掌握中。”[13]住宅空间不再是毫无知觉的死物,外在于叙事,只充当节点和背景,空间本身成为具有生命力、互动感的生物性存在,它来到了舞台中央,作为内部的动力来塑造叙事。
马塞夫妇坚信“人人平等”,米莉亚姆为了保护露易丝的自尊心,将新买的衣物藏在旧布包里,保罗会将露易丝作为家中一员介绍给朋友们,“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露易丝”[14],他们带露易丝去海边度假,邀请她一起吃晚餐,表达自己对露易丝的付出十分重视。他们的善良并不虚伪,但却具有不自知的残忍,因为他们缺乏对伦理下位者欲望的管控意识,而给了绝望之人以错误的信号,令其产生虚幻的越界期望。
因此,生平第一次,露易丝看到森严的阶级壁垒出现了裂缝,“她现在有了一种隐秘的信念,炽热的、疼痛的信念,那就是她的幸福取决于他们,那就是她属于他们,而他们属于她。”[15]露易丝渴望突破零度空间,在现实与心理上都找到属于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她把这一切都寄托于马塞夫妇。
三、由空间暴力催生出的伦理暴力——“工具化”的人
玛瑞林在其空间研究中特别谈道:“住宅是性别政治和阶级斗争上演的舞台。” [16]马塞夫妇虽只是小中产者,但与生活困难的露易丝相比,依旧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阶级。前者对后者表现出的友好,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教养,另一方面是他们深知自己“多么需要露易丝”。他们对露易丝承诺:“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分子”,但他们对她的接纳是基于自身需求,而非真正地欣赏和喜爱。米莉亚姆嘲笑露易丝对孩子们过分重视,保罗也瞧不上“她那堆可怜的教育理论和她祖母级的教育方式”[17]。在日常的交往中,阶级的差异与鸿沟逐渐显露出来。
露易丝的亡夫雅克欠下巨债,露易丝无力偿还,只好一再逃避债务,但催款单却被直接寄给了马塞夫妇。随着催款单的到来,露易丝的工资被没收以抵债,房东威胁要赶走她,叙事从此围绕边缘身份力图对抗中心力量和对生存空间进行争夺的悲剧而展开。
作为空间暴力的受害者,露易丝被无家可归的恐惧压垮。“很快就是她了。她会流落街头。哪怕这么一间污秽的小房子,她也保不住,她将在街上拉屎,像个动物。”[18]卑亢的心理使露易丝的行为日渐扭曲,露易丝的心中涌动着仇恨,她憎恨雇主在无意间窥探到自己身负巨债的污点,也憎恨他们在一贫如洗的自己面前依旧漫不经心地浪费一切。米莉亚姆和保罗开始考虑解雇露易丝,“她是我们的雇员,不是我们的朋友。” [19]
在《温柔之歌》中,人呈现明显的“物”的特征。为了留在马塞家,露易丝异想天开地盼望米莉亚姆怀孕。她自掏腰包把孩子们带出去吃晚饭,以便夫妇俩单独相处,但当她回家时,却发现米莉亚姆因工作太过疲乏而先行独眠,露易丝失望至极,露易丝明确地感知到自己即将被辞退,这极大地刺激了她,露易丝挣扎着谋求空间和话语权的行动一再受挫,她预见到即将来临的一系列窘境——被房东驱逐,被马塞夫妇解雇,肉体上无处安放,精神上无所寄托。“没有住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20]露易丝一直没有一个可以庇护她、为她服务的家,她对那么多家庭的全心奉献、卑微付出,也没能换来被世界平等以待的机会,她被抽离了情感性质,只剩下冰冷的物质联系,甚至露易丝本身都被异化成了可被使用的工具和可被消耗的商品,就连保留一点点隐私也做不到。
现实的步步紧逼,令露易丝迅速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破碎的心理空间也导致露易丝无法重构自己曾经的理想身份,回忆和现实充满了侮辱与羞耻。“她必须承认她再也不会爱了。她把心里的温柔全耗光了,再也没什么可供她的双手去轻抚。”[21]这一双曾如天使般呵护孩子们的手,在一个平常的下午,放满了洗澡水,接着拿起凶器。露易丝不但向两个孩子下手,而且也把刀子插入了自己的咽喉。“谋杀,自戕,杀婴是反抗心理的核心表现。”[22]负责案件的警官试图找出“完美保姆”杀人的真相,却屡陷入迷雾中。露易丝是被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生产出的暴力彻底击垮,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四、总结
斯利玛尼在《温柔之歌》中的空间叙事建构,没有停留在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而是在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社会意识和身份认知之后,在现代多元文化共生背景下努力就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寻根究底。通過多角度的空间书写,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暴力由空间向伦理的演变。保姆露易丝作为弱势群体的存在,在不可见的暴力中遭受压榨,其生存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一再倒塌,引发其心理空间的崩溃,最终在伦理空间的动荡和冲突中得以爆发。她杀害两个孩子后自杀的极端手段,与其说是她个人的伦理选择,不如说是当代法国社会阶级冲突问题的隐喻。
在斯利玛尼笔下,“空间意象”蕴涵着尖锐的“空间冲突”。这种“空间冲突”不仅揭示了人物关系冲突,还暗含着对现代社会文明冲突、制度冲突、阶级冲突的反思和拷问,呼吁着空间中的人文关怀。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 (项目号:gxun-chxs2021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周思.《温柔之歌》:生命暗湖中的真实[N].文汇报,2017-08-21(05).
[2][3][4][5][7][8][10][11][12][13][14][15][17][18][19][21]蕾拉·斯利玛尼.温柔之歌[M].袁筱一,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13,69,41,57,83,60,81,25,37,38,71,88,133,165,198,230.
[6]爱德华·W·苏贾.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64.
[9]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0.
[16]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56.
[20]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78.
[22]龙迪勇.主持人语: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9(9):56.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