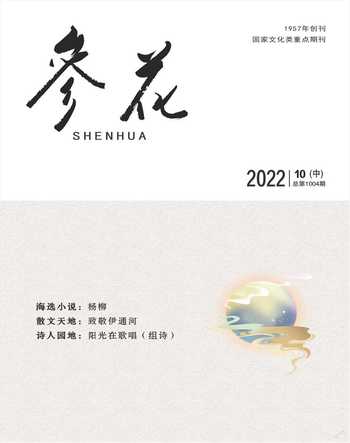论小说《什卡斯塔》的互文性
一、科幻小说由传统过渡到现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将大部分的创作时间用于对科幻小说的创作。对于这一转型,批评界和大部分读者既惊呼不解,又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莱辛的作品是一个强有力的寓言。这样的转型是怎样为作家利用科幻小说这一文体进行契合时代的创作的,需要先对科幻小说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过程进行一番梳理。
在科幻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的蜕变过程中,人们对科幻小说的认识也在进一步深化。“美国著名的批評者詹姆斯·冈恩对科幻小说下的定义为: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描述变革对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科幻小说可以描写过去或未来,也可以描写遥远的地方。在问及莱辛对科幻小说的创作时,她这样回答:‘在写作这些幻境的书时,科幻小说之类的想法一直没有在我的头脑里驻足。直到有人把我的小说当作科幻小说来评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涉足了这个神秘的领域。”[1]由此可以看出,科幻小说借星际探索等外衣,实际上,其承载着人类对自身和未来发展的思索。这种使命感和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直接影响了科幻小说从创造手法到主题思想的转变。在现代小说创新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冲击下,科幻小说作为小说题材的一个分类,也经历了由传统叙事性科幻小说向现代元科幻小说的过渡。传统科幻小说注重外部空间,或太空世界对人类现实世界的模拟功能,情节曲折动人,遵循线性叙事的标准。元科幻小说也注重对外部未知世界和空间的探索,但在探索过程中,外部空间和世界只是主人公进行真正的虚构性话语的背景空间。[2]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现实主义的关系变化中,科幻小说也经历了从个人的神思妙想到关怀全体人类命运的过渡,这种过渡不是退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而是依循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用更富技巧的创作手法进行创作,因此,科幻小说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后现代时期的一朵奇葩。
科幻小说的发展也有其社会原因:作者所选择性地采用的创作手法,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借鉴,也有对科幻小说形式的创新。作者把这种创作手法和科幻这一小说样式进行整合,使科幻小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最大限度地展示她后现代创新者身份的同时,也使《什卡斯塔》《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和《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等作品成为后现代科幻小说中的范例。
二、《什卡斯塔》的写作技巧
在具体创作中,莱辛重构了小说的开头,以重新组织文化和社会发端。正如杜布莱丝所说:“重写开端以及对结局的悬而未决都是权威和权威授予的行为,都是重新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尝试”。[3]在小说《什卡斯塔》的未开始处,作者就以题名点出了玄机。文章开头,在给人们呈现出一个面目全非的星球后,作者重绘了一个无忧无虑、充满希望的星球。而在文章的结尾,乔荷已然变成星球中的一分子,他还要为保卫星球、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战,只是这种使命早已结束,而在冰冷的安第斯山脉上,他的妻儿、家人还在寒冷饥饿中慢慢地等待,这种等待是否还有意义?营中的凯斯姆前去寻找乔荷,乔荷告诉他:这里,我们将建一座新的城市。在这样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带给人们以感动。撇开小说内部的互文性,这一系列的小说创作在西方现代传统中可谓经久不衰:从《恋爱中的女人》到《冷山》等作品,《什卡斯塔》更进一步,作者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不仅一开始就摆脱了在人类情感中徘徊,以求出路的圈数,更在人类命运的高度上,对更深层的思想、习俗、公众与个人关系等进行相应描写,充分展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大气和眼界。
在具体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力排众议,也跳脱出传统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的束缚。纵观全文,读者不知道主要人物的样貌、服饰,也不知道哪些是主要人物,哪些又要被当作次要人物。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具有鲜明的个性,而是变成作家用以表达个人观点的工具。比如在《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中,在第八星球生活着的居民,不具有任何鲜明的个性特征,甚至没有名字,读者只能根据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对其进行区分,教师、医疗者、看果园的人、讲述故事的人、唱歌的人,等等。
这样的描写在传统文学中是无法想象的。依照经典的小说定义,寓言形小说叙事中的人物称不上圆形人物塑造,而是各类平面人物。作者在心中往往已经有一个观念或答案了,因而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投射对这一观念、答案的求索和求索过程。杜布莱丝将科幻小说中出现的这种人物类型,称之为多角色主人公们或群聚形主人公们。这种人物创作类型的好处是,集团型主人公能够代表一个集体性的自我,而非个人的我,其所提出的价值能够与集体利益相辅相成。在莱辛的多部小说中,带有强烈探索式性质的人物十分突出,甚至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如其在后期创作的《简·萨默斯的日记》中的萨默斯和她的邻居。
在科幻小说《什卡斯塔》中,同样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以贯之的主人公,而是以各种文本和档案记录的形式,记录下老人星的观察者乔荷、其他观察者和居住者的通信。从什卡斯塔星球上人们安居乐业、一片祥的景象,一直记述到灾难来临,人们惊慌四散,再到整个星球了无生机、陷入灭绝的困顿之地——正是由于对这样的多角色主人公们的塑造,人们对什卡斯塔星球的命运才能够感同身受,才能够真正起到后科幻小说所具有的训诫和启示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正是由于成功地运用了多角色主人公,才能避免在现代小说中被反复探讨,而不得其解的视角、隐含作者、隐含读者等问题,由于文类的庞杂、记叙的多角度,对于视角的探讨就会不攻自破。
三、互文性与文本解构
互文性最早由法国的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笼统说来,指一文本与另一文本的互涉关系(intertexuality)。在罗兰·巴特所著的著名的解构主义文本《恋人絮语》中,通过对歌德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单纯解读,使其自身构成了一部饶有趣味、堪称经典的解构主义文本。既是对歌德作品的解读,也是一部融合心理自白、书信体、古今融合、视角融合的独立小说。互文性的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了关于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概而言之,互文性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具体说来,文本互涉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1.文本不同于传统‘作品,文本是语言创造活动的一种体验。2.文本是对能指的放纵,没有汇拢点和明显的收口,而所指后移。3.文本构建在文间引语,属事用典,回声和各种文化语义上,文本的意义呈多义状。4.作者不等于文本源头,作者的解释也非文本的终极,作者也只能造访文本。总而言之,文本向读者开放”。[4]
四、《什卡斯塔》报告间的互文
由于沙马特星球在什卡斯塔星球上的活动,导致什卡斯塔星球赖以为生的物质——我们感觉的根本正日益减少,当乔荷来到什卡斯塔星球时,整个星球上人们的惶恐,不仅与前期的和乐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让乔荷吃惊的是,人们也在历经整个灾难的过程中,失去了與老人星的联系,失去了与赖以维系自己生命物质的联系。此时,在什卡斯塔上,仍然是巨人族负责保护和维系当地人的生活的。巨人族的主要工作在于脑力劳动,即维系与老人星的通信,同时,巨人星内部的女人除哺育孩子之外,与男人们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的寿命也延长至千年。当我(乔荷)到达罗汉达时,看见巨人族和本地人并排行走,“我”遇到了叫作杰瑟姆(Jasum)的巨人,并在巨人的大房间里召开会议,通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历史结束了,他们在罗汉达领域上的演进任务结束了。然而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还可以存活。他们可以像以前被送往这里一样,被送去其他星球。虽然在老人星内部,所有物种也被告知只有与老人星的长远发展计划和谐共存时,人们才有价值和意义。但是在此时此刻,那些本地人没有任何存活或发展的希望,除非在数年以后,演进计划又可以重新开始。面对如此晴天霹雳的消息,巨人族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他们提出,他们需要时间进一步商讨可以将此事告诉本地族群的最好方法。
对于这一点,当乔荷刚刚来到什卡斯塔时就应该有所领悟。虽然罗汉达和老人星之间的联系称为锁(the Lock),罗汉达领域上的物种将这种联系看成是某种沟通的方式,[5]但是当乔荷拿出印章给巨人族看时,巨人族竟毫无反应,命令各类人只有穿过平原才能逃脱灾难时,人们也是不知所措的。更有甚者,人们不知道敌人的存在。当被告知从老人星前来营救的飞船时间和地点时,巨人族仍然迟疑不定,在灾难即将到来之际,不管是老是少、或高或低,都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和鉴别力。从这一点上看,文本在形式上虽然处于解构和分裂的状态,但在小说人物的心中并非如此,他们仍然存有对美好家园,对群体的依恋和完整度的保存的期待。于是,出现了以下情节,当本地人离开家园时:
这一小群人,从树林和草地中走来,被一群睁着闪着智慧的眼睛的动物看着,仿佛又回到了亿万年以前,他们刚学会用后腿直立,是那样的无助。[6]
在什卡斯塔经历灾难的所有历程中,乔荷的报告占大多数,其他任务员的报告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出现在文中109至122页,题为“什卡斯塔的历史:摧毁的时代与陶菲克等人的报告”,这一具有相当篇幅的报告与来自老人星的乔荷访问经历灾难的什卡斯塔任务报告形成了互文。
五、结语
多丽丝·莱辛的科幻小说《什卡斯塔》通过大量互文的艺术手法,重构了属于整个人类的记忆和经验,使作品充满了生命力。通过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形成了互文性关系,为文本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通过互文性关系,人们可以更好地探索文本的主题意蕴及其特色。通过打破相继性、平面性,从而获得一种非相继性和立体感,让文本的存在依靠于一种广泛的联系,并且时时强调这种联系的偶然性和丰富性。
参考文献:
[1]邓中良,华菁.《巴黎评论》莱辛访谈录[J].外国文艺,2008(01):34.
[2]Ebert Teresa L.The Convergence of Postmodern Innovative Fiction and Science Fiction:An Encounter with Samuel R.Delany's Technotopia[J].Poetics Today 1.4,Narratology II:The Fictional Text and the Reader(Summer, 1980):91.
[3]DuPlessis,Rachel Blau.The Feminist Apologues of Lessing,Piercy and Russ[J].Frontiers 1979:2.
[4][法]罗兰·巴特.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M].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7.
[5][6]Doris Lessing.Shikasta[M].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39;174.
(作者简介:朱海棠,女,博士研究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科研秘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高等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