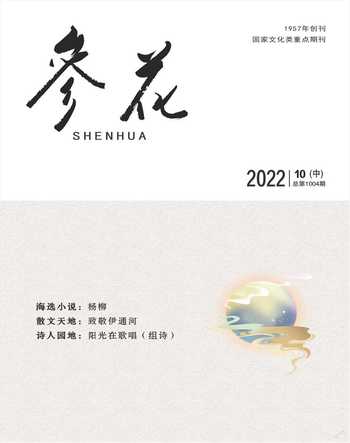茨威格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他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俄国作家高尔基评价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善于描绘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歌颂纯粹、唯美的精神力量,通过高超的写作技巧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人类命运的思索与关注。他的诸多短篇小说犹如一颗颗珍珠,在文学的海洋里,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闪烁着熠熠光辉。
一、独特的叙述视角
在西方文学中,常用的叙述视角包括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还包括全知全能视角和限知视角。茨威格在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中所使用的叙述视角,有着多样性。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说过:“在一篇叙事中使用单词‘我的作者(author)经常似乎不同于作者(writer)——可以被描绘在书的封面上的那个人”。在茨威格的作品中,他仿佛总是以作者“我”出现,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就是茨威格本人。例如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书中主人公“我”的身份是一个作家,接下来的整个故事都与“我”有关,我是故事情节的主要参与者。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了《巧识新艺》中,“我”依旧是作家,是故事的叙述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成了故事的主要参与者,成为整个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作者“我”完完全全地参与到了故事中。而在《看不见的珍藏》中,作者“我”依旧在其中出现,但“我”并不是故事的叙述者,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另有其人,他向“我”转述他所经历的故事成为整部作品的主要内容,那么转述者就以“我”出现在了引号中,整部作品写的都是转述的内容,而作者之“我”便隐身了。
茨威格也并不总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有时他也使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或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来创作。甚至在一部作品中使用多种视角。例如在《夜色朦胧》中,作者在开篇交代他要讲述一个故事,之后,作者隐身而去,而真正的主人公——男孩出现了,男孩成了小说的主人公,整个故事是围绕他而展开的。作者运用的是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故事只涉及男孩的所思所想,故事的发展也只通过男孩的视角去展现。在故事结尾,隐含作者又从幕后走出来,站在全知全能的视角交代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结局,评说整个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悟。这种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巧妙互换,体现了茨威格纯熟的写作技巧。茨威格时而使用第一人称,时而使用第三人称限知或全知视角,为小说增添了可信度,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正如华莱士·马丁所说,“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作品绝对分开是与我们的直觉相违背的”。无论使用哪种人称,作为读者的人们都未曾怀疑过故事的真实性,这也许是因为人们都默认了故事的叙述者是知识渊博、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的存在。
二、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
对于作者而言,不同作者会有自己所喜爱的描绘人物的方式。正如谭君强所说,描绘人物的基本方式包括直接形容与间接表现这两种方式。间接表现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较为常见的方式是通过行动、语言、外貌,以及对环境的描绘等,间接地表现人物性格。茨威格在其作品中,就擅长用间接表现这种表达方式。例如在《巧识新艺》中,作者“我”就对文中的主人公——穿黄外套的扒手(起初叙述者并不知道他是扒手)进行了细致描绘——他的身体干瘪瘦弱,裹在一件不合身的鲜黄色外套里,显然并非为他量身剪裁,因为他的整双手都消失在过长的衣袖里……老鼠般尖尖的消瘦脸庞,他的嘴唇苍白,嘴唇上方一撇金色的小胡子仿佛在害怕地颤抖……歪着肩膀,一双腿细瘦犹如小丑,表情惶惶不安,从人潮漩涡里溜出来,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像一只小兔子在偷吃燕麦似的,胆怯地四下窥探,随后再度消失在人群中。这段人物描写,使一个落魄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着力刻画他消失的双手,就是在为下文发现他是一个扒手而做铺垫。茨威格对这个人物的外在描写贯穿了整部作品,通过一步步渐进地描绘,使这个人物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和丰满,读者由此也会越来越接近真相。叙述者继续描写:他一脸瞌睡,像在做梦似的,然而他总是会睁开松垮的眼皮,就像一具相机按下快门时发出闪光,将目光投掷出去,宛如投掷一支标枪。读到这里,读者们可能就会心领神会了,原来这是一个善于伪装的、手段高明的扒手。在下文的描绘中,读者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测——他是个扒手,一个地地道道、受过训练、如假包换的专业扒手,在这里试图捞到皮夹、怀表、女士的钱包及其他战利品。采用这种间接表现的方法来刻画人物,使茨威格作品中的人物仿佛从故事中“走”了出来,使读者一目了然。
在《看不见的珍藏》中,茨威格也通过间接表现的方法,刻畫了一个饱经沧桑、深受战乱之苦,但依旧对生活充满期望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花尽毕生的积蓄,收藏了上百幅价值连城的名画,战后,老人失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迫于生计,其家人不得不把老人视为生命的所有收藏品以低价卖出,而老人却被蒙在鼓里。一位慕名而来的收藏家在老人家人的恳求下,不得不用善意的谎言保护老人和他对艺术的热爱之情。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但在茨威格笔下,对老人神态、语言、动作的描写,却鲜活地把老人那种纯粹的热情和完全投注艺术的那种狂喜表现了出来,使人们感受到艺术照亮了人的心灵的力量。失明的老人对慕名而来的“我”倍感欣喜:他小心翼翼地从画册里拿出一张纸板,就像一般人平常碰触易碎物品一样,用指尖细心呵护地去碰触纸板上框着的一张已经泛黄的空白纸张,他赞叹着把那张毫无价值的废纸举在眼前。他看着它好几分钟,但其实并未真的看见,整张脸奇妙地流露出一个正在注视之人的专注神情,他的瞳孔里出现一道反射的光亮,一种智慧的光芒。六十多年来,老人不喝酒、不抽烟、不旅行、不上剧院、不买书,总是节省再节省,就是为了省下钱买这些画。老人温柔地抚摸那些早已清空的画册,像在抚摸某种有生命的东西,就像喝了葡萄酒一样快乐忘形、如痴如醉。当叙述者准备离开时,老人站在阳台上,坚持要用他盲了的双眼目送“我”,他挥动手帕,用小男孩儿般快乐、清亮的声音喊道:“祝您一路顺风!”老人天真幸福的喜悦之情在细腻的神态、动作、语言描写中展现了出来,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这个白发老人喜悦的面容,在上头的窗边,高悬在街道上那些闷闷不乐、仓促奔忙的人们之上,超脱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之上。老人对艺术的热爱深深地感染了读者,这种描绘人物的方法让读者不再只是肤浅地谴责老人的家人,而将这一切归咎于战乱等因素,从而升华了作品的主题。
三、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
在茨威格的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非其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莫属。这些心理描写能够更加直接地揭示人物的所思所想,让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从而与其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茨威格对这一技巧的运用可谓是炉火纯青,其在作品中,往往会以“我想”或直接用“他想”描绘,或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我”发表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些大段的心理独白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成为情感宣泄的闸门,展现了无比动人的精神力量,并与小说的主题遥相呼应。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一个女人以“我”的口吻叙述了她对小说家R那刻骨铭心的爱。女孩与邻居R先生在公寓门口相遇,女孩迷恋上了这位先生,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从这一秒钟我就爱上了你……那犹如奴隶一般,卑躬屈膝、舍身忘己地爱着你……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中,就像掉进一座深渊。对女孩而言,这个对她并不熟悉的男人竟然成了她的全部,她的整个生命。她的一切只有跟他发生联系才有意义。女子如泣如诉地向小说家描述她是怎样爱上他,怎样谋生,怎样与他重逢,怎样为了他过没有生气的日子,放弃别人的追求,甚至是伤害爱她的人的。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描写一个对象,使它的细枝末节都变得鲜明,它的语言和情节都能够触动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让读者随着女人的思绪或悲伤,或欣喜,或哀愁,从而一步步把故事推向高潮。
茨威格善于揭示人们行为的隐秘根源,他可以或简明扼要,或长篇大论,视故事中不同部分的需要而定。在《一颗心的沦亡》中,茨威格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叙述主人公所罗门松的思想脉络,用了很多诸如“他想”“他大声呻吟”“他喃喃地说道”的语句。华莱士·马丁把这种表现手法称之为“进入意识”。“进入意识”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可以看进人物的内心,也可以通过其内心来看。在第一种情况中,叙述者是观看者,人物的内心被观看。在第二种情形中,人物是观看者,世界被观看。这时,“我想”就变成了“他想”,“我意识到”就变成了“他意识到”。《一颗心的沦亡》讲述了一个赚钱养家、辛苦一辈子的老人在与家人度假时,偶然发现自己不满十九岁的女儿竟然与人偷偷幽会,这让老人的整个精神世界轰然垮塌,从此郁郁寡欢、封闭自我,走向死亡的故事。在文中,作者忽而钻进老人的身体,用老人的眼光去观察,忽而从老人身上抽离出来,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述说老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老人在偶然发现女儿的秘密之后,他绝望地想着:昨天我可以算作幸福的人,我为美丽开朗的女儿感到喜悦,为了她的喜悦而喜悦,可如今她却被人夺走了……我将时时刻刻活在恐惧中,一个人没法这样活下去……没法这样活下去。老人对女儿的爱胜过一切,女儿的纯洁不容他人玷污,女儿在老人的心中是如此完美,而当这一切突然消失时,老人顿时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四、启迪人生的主题
茨威格用一个一个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故事,表达了他对伟大人格、崇高精神的赞美。这些作品涉及了不同的主题,反映了他对爱情、亲情的渴望与赞美,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穷苦大众的怜悯与同情。《夜色朦胧》讲述了一个与男孩有关的忧伤的爱情故事,茨威格在小说中设置层层悬念,制造了戏剧冲突,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展现了极强的叙事张力,促进了小说高潮的到来。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同样讲述了一个与女人有关的,爱而不得的、凄婉的爱情故事,堪称是此类题材的顶峰之作。茨威格还擅长写亲情,如展现父女关系的《一颗心的沦亡》,展现母子之间从猜疑、气愤、释怀到和解过程的小说《灼人的秘密》。同时,在这些作品中,他也流露出对穷人凄惨生活的同情,对遭受战乱的家庭的怜悯,对战争的厌恶与思索。在《巧识新艺》中,一个扒手试图对作者行窃,作者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讽刺的对象和遭人唾弃的小偷。当作者看到他坐在餐厅喝着一杯白色牛奶的时候,他不再是作者眼中的小偷——他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穷人、病人、可怜人、流离之人中的一个。借此,茨威格又借用叙述者“我”之口,阐述了人与人生来平等,即便是小偷也有尊严的看法。作者还展现了对他的同情,想到了他住所的肮脏,也许一个脸盆、一个皮箱就是他的全部家當。此处,作品的立意立刻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与认同。在另一部作品《看不见的珍藏》中,尽管生活如此困顿,老人对艺术的热爱,那纯粹的幸福感却深深感染了叙述者、他的家人以及所有读者,这部作品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超脱的人生境界,让读者受益匪浅。
总而言之,茨威格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运用独特的叙述视角、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给读者呈现了一席精神上的饕餮盛宴,但无论其技巧多么高超,都是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而服务的。他的作品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仿佛让人们的精神也受到了洗礼。茨威格崇高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存在于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人物中,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也许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在。
参考文献:
[1] [奥]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M].姬健梅,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
[2]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斯蒂芬·茨威格中短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项目编号:JJKH20221279SK)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爱华,女,硕士研究生,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