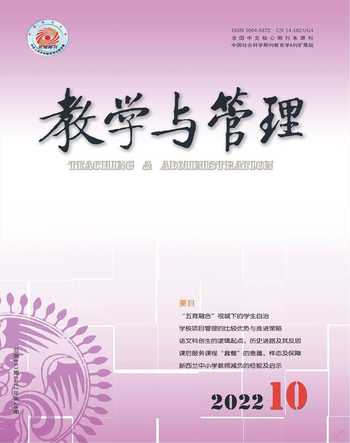语文科创生的逻辑起点、历史进路及其反思
摘 要
百余年来,语文科似乎总是在批评与改进、问难与求索中艰难前行,时人在不断地提出药方的同时,直到今天,语文科成效依然微弱。而梳理和透视语文科创生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进路,我们会发现,由于受制于“一般”“浅易”等水平要求,近代以来语文科的内容创设则是“迁就”的思维模式下重构要素表达。如此一来,因“取法其中,得乎其下”的因果逻辑,语文科从一开始就有先天不足的历史底味。因此,反思语文科创生的逻辑起点和歷史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本身解决语文科的现实问题。
关 键 词 语文 逻辑起点 迁就教育 普及教育 语文科创生
引用格式 韩再彬.语文科创生的逻辑起点、历史进路及其反思[J].教学与管理,2022(28):36-40.
纵观百年语文教育发展史,从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慨叹、1943年文学批评史家罗根泽发出的“抢救国文”的呼吁,到1978年吕叔湘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少、慢、差、费”问题等,以及201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的《语文病象令人忧》一文,指出1951年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中提到的一些语文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减少”,同时又说道:“随意翻阅今天的报纸、杂志、书籍,用词不当和语法、逻辑方面的问题经常能碰到。电视上、网络上,这种现象也同样严重。”[1]回顾我国语文科发展的艰难历程,语文教育似乎从未有令人满意的时候,以致于“语文专家在批评它,作家们在批评它,老百姓在批评它,学生们在反抗它,就是国家教育机关领导也不满意”[2]。
从整个语文科的问题史来看,社会对语文科的批评与问难一直都存在,人们一边在寻找语文科症候的同时,一边也在不断地寻找药方。如五四时期,为了改变当时国文教学落后的局面,邰爽秋针对当时中学入学考试几百份语意不通的文章,对其常用汉字和常用句式等做了调查和统计,从而提倡建立“科学化的国文教授法”;黎锦熙将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改造为三段六步法,为学科教学的规范化建立了操作体系;陈启天倡导“因文而异”的程序性教学法,把国文教材分为“模范文”“问题文”和“自修文”,试图以科学的程序开展语文教学。之后,陈望道、阮真、叶圣陶、吕叔湘等人也提出了很多具有创见性的方法来解决当时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但效果似乎都不太理想。进入新时期以来,无论以语文教育流派(如三度语文、青春语文、绿色语文等等)的兴起,还是致力于“言语”“情境”“语感”等教学范式的创新,抑或借鉴国外先进教学思想来革新教学手段,语文教育的成效似乎依然没有多少起色。特别是当我们提出了一种观念、思想、措施,而这些观念、思想、措施还没有来得及去证明和求实时,一种新的概念和方法又提出来了,这不仅扰乱了学科研究的现有秩序,消解了研究本身的推力,也让语文科因缺乏历史大眼光而陷入持续的折腾和内耗之中,从而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语文科创生的历史大背景中来讨论,才能从一种全真的图示中窥见语文科由来已久的症候。
一、“普及”“实用”与“兴趣”:语文科创生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中回答基本问题的关键概念,或者说是对基本问题进行解答的起点。”[3]晚清以降,出于启迪民智和开蒙大众的目的,晚清社会变革者赋予语言文字以崇高的功能和地位。他们认为,言文不一致是影响开启民智主要障碍之一。黄遵宪在1887年的《日本国志》中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4]梁启超也说:“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5]陈子褒更是疾呼:“开民智,而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革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6]
那么,如何改善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呢?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口号。他希望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7]的新文体,其目的在于“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8],从而开启了言文一致的先声,为后来的言文一致打开了切口。裘廷梁更是旗帜鲜明地说道:“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9]在他看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10]。民族要想富强图存,必须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从而使人人都能通晓事理。因此,晚清知识分子寄寓了言文一致崇高的地位。
言文一致是晚清改革者变革表达形式最直接的手段,虽然在具体措施上言人人殊,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普及教育。在救亡与启蒙的时代序曲面前,提倡白话文,从而实现言文一致下的普及教育才是当时最急切性的目的。裘廷梁认为,白话文可以“省目力”“保圣教”“便幼学”“便贫民”等等[11]。劳泽人也说道:“白话文直接是平民教育的基础,宣传文化的利器……要普及教育,要社会改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倡白话文。”[12]蔡元培后来回忆提倡白话文的原因时说:“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13]言下之意,主张言文一致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普及教育。后经过各界学人的不懈努力,到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令第七号》要求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从而达到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教育部继续发布公告,要求逐渐废除之前的旧国文教材,使用新审定的白话文教材。至此,可以说白话文在语文科中的合法地位得到了事实上的承认。到了1922年“新学制”颁布,也将普及教育的宗旨写在了学制章程里面,如其中的“发扬平民教育精神”和“使教育易于普及”[14]。
晚清变革者在致力于“普及教育”的同时,也深感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撬开了国门后,激进改革者对时人整日从事章句之学提出了猛烈的批评,认为他们在面对“天算、动物、形声、格致之学皆茫然无知”[15]。自然而然,“实用”也成为了当时继普及之后理解语文科创生背景的又一关键词。如沈颐在1909年发表的《论小学校之国文教授》一文,批评旧时文人不能“作记事文与寻常家信”,从而主张国文应“授以布帛菽粟之文字”[16];再如1912年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初等小学应该让儿童在读书、作文等方面学习日用文章,高等小学所选的学习材料如修身、历史、地理等也应该注重生活日常必需事项,表现出明显的实用化倾向。有学人经过研究发现,“清末明初的成人本位实用主义国文、国语教育,其教科书中的课文以实用文章为主,而很少有文学作品”[17]。这为我们理解语文科早期创生的历史语境提供了另一重视角。
透过历史的帷幕不难窥见,以言文一致为急务的语言文字运动扫清了普及教育的先天性障碍,而实用教育思想则为普及教育提供了现实处方。这不仅构成了语文科内容表达的逻辑起点,也直接改写了语文科早期的路向。在感情和情绪大于理性的时代面前,“普及”和“实用”虽谈不上是最优选择,但基本上也算是最捷径的举措。“普及”意味着内容更简单,而“实用”不仅意味着内容简单,而且也应该接地气。这两者的勾连制约了语文科的创生内容,使其必须在简单、容易、实际的范畴上下炼制课程内容。再加上五四以后欧美教育思想的的引入(如儿童中心论、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德克乐利教学法等),也直接地影响了语文科内容的创生。
虽然语文科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科学、人文、生态等思想不断地影响早期语文科的路向,但在创生之初,“普及”“实用”“兴趣”因更贴近时代主题而被采用。这几者并不协和的融合焕然分化出一条与传统语文教育迥异的表达范式,那就是以“浅易”“一般”“平易”等话语模式为主从而形塑了我国语文科的内容。因为“浅易”“一般”“平易”等话语形式也是在普及、实用和儿童兴趣论之间找到了一条能容纳各自情感意图的最大公约数。
二、在“迁就”的尺度之间:语文科创生的历史进路
以“普及”“实用”和“兴趣”为逻辑起点的语文科,由于受制于“浅易”“一般”“平易”的水平要求和逻辑规则,近代语文科的创生总是围绕“浅易”“一般”“平易”等核心范畴作相似性的表达,似乎始终未能向高标格的尺度或位格上进一步突围。而这其中,普及教育更是语文科最大的急务。简而言之,语文科创生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实现普及教育和救亡图存,但这是否遵循了语文科本身发展的规律,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紧迫的现实面前,或许并没有多少心力顾及语文科自身的周全。对他们来说,学科发展的内在状态和未来愿景在“救亡大于启蒙”悲情的氛围下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借助语言文字实现开蒙民众,从而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鉴于此,语文科的一切核心要素表达都必须在“浅易““一般”“平易”等近似维度上下进行创设,而任何复杂或有深度的语义表达在这里都似乎变得不合时宜,因为要快速地普及文化知识,就需要革除传统,推倒重建,放逐以文言文为主的精微式的教育形式,从而构建以口语、大众语等为主的白话文学习范式。
语文科独立设科前夕,近代文言选文已经开始趋向选择所谓“易懂”“平易”“浅近”的内容,同时也注重学生的兴趣等,如1902年俞复、丁宝书等人编写的《蒙学读本》中“祝我国,固金汤。长欧美,雄东洋……”之类。教材注重选排浅显的文字让儿童能快速地识字写字。而在此期间,小学教科书还有《识字贯通》《文话便读》等,如《文话便读》采用分课编写模式,每课先列单字,次列句子。如第一课:鸟、狗、儿、飞、叫、追、逃、小。小鸟飞。小狗叫。小儿追。小狗逃[18]。选文内容的浅显易懂性体现出语文独立设科前后教材选文较之传统语文教材的明显变化。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小学分为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在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中,儿童必须学习包括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在内的8门必修课程。从中国文学一科设置的目的来看,“中国文字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19]。其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阅读、写作技能的实用人才。同时对读经讲经一科也有规定:“凡讲经者先明章指,次释文义,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20]这种讲究“浅近”“谋生”等理念直接影响了后来语文教科书内容的选编。如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新国文》,开篇的课文为“人、手、刀、尺”,特别符合“浅近”“平易”“一般”的特征。因此,近代语文科在强调实用、平易、学生个人程度上为语文科的要素表达提供了方向。
从1904年《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第1课“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开始,到民国初年初等小学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1册第一课的“人”,以及1923年初等小学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1册第1课为“狗,大狗,小狗”的内容选排,都将“浅易““一般”“平易”等话语范畴深深地浸润在语文科的形态之中,深度影响了近代以来小学语文科教材选文的编写,现行的统编本小学低段的语文教科书也一以贯之地践行着“浅近”“平易”“一般”的思路,如一年级上识字单元,以“天地人”“金木水火土”“口耳目”等板块开启了学生识字学涯。对比传统启蒙教材“三百千”和《性理字训》《小学》等,近代以来的语文科内容浅显明了。因此,有学人批评五四以后的小学国语教学,认为那些优美的文言诗文几乎被“诛杀殆尽”,而代之以“小猫”“小狗”这类浅显通俗的白话文,这种“一味迁就儿童的学习兴趣的做法其实并不明智”[21]。从课程标准来看,“1912年至1949年,教育部颁发的7个初级中学课程标准均提出了阅读‘浅易文言文的教学要求”[22]。而现行的语文课程标准对文言文教学的要求也不过是“了解一般的文言文的能力”或能“阅读浅易文言文”等等。
将“浅易““一般”“平易”等话语范畴作为语文的设计思路,一直伴随着语文科始终。邰爽秋针对学生没有过多时间来阅读的问题,认为多读熟读是最不经济的方法,因此要精选范文。“教国文的方法,不在教学生多读,而在教他们精读。精读的结果,是少花时间,可将国文弄通。”[23]陈启天认为,国文教授的目的是“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24]。他认为,中学生只要看了现代应用文,了解其意思即可,如需学习古文,可以看点诗歌以涵养性情。
语文科无论是从课程内容的设计,还是课程理念的表达,亦或是语文教育研究者的思想,其历史进路高度吻合了钱穆所定义的“迁就教育”的特征。钱穆从当时中学教育里文字教育说起,批评了我国教育中出现的迁就教育现象,即将学生的兴趣和程度作为“标格”,这实际上不利于学生能力的进步。钱穆把当时的教育定义为“迁就之教育”[25]。钱穆对“迁就教育”的特征举例说道:“唯读《庄子》可解《庄子》,惟读《史记》可解《史记》,若先斥《史记》为难读,先读其浅易者,而文字之阶层亦重重无尽,若取遷就主义,则更有其尤浅尤易者。”[26]简单说来,在钱穆看来,若一开始就接受经典,那么就能够理解经典,如果一开始就拒斥文化经典,认为难懂,那么就一直会难下去,如此这般,就会让学生的智慧与能力弱化。钱穆这番灼见也精准地概括了语文科创生的历史进路的特征,那就是始终在“迁就”的维度上下制约着语文科要素的表达。
语文科进入1949年以后,回望和探寻语文教育的历史进路自然首先会想到叶圣陶。潘新和在《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一书中开篇给予叶圣陶较高的评价:“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他主笔的,这个人就是叶圣陶。”[27]认为“要破解现代语文教育之谜,我们无法回避叶圣陶”[28]。从整个语文科的历史来看,叶圣陶为语文科从创生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实际上,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也承继了1904年以来语文科“浅易”“一般”“平易”等特征。“他的教育思想是平民化的,他的最大的贡献是为语文教育奠定了现实、普及、实用的方向。”[29]实际上,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更多考虑的是大众的普及教育。比如他认为学生不需要学太多高深的知识。在叶圣陶看来,传统语文教育只是让“少数人有了很高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从现代教育的观点说,人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须练习得到家。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30]。因此,为了“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就需要践行“不让一个人掉队”的整体原则,那些走在前面就必须要等等落在后面的人,学习力很强的人也需要停下脚步等学习力偏弱的人,同时,教学内容还应该更简单,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学到知识。
同时,在对待传统文学经典上,叶圣陶认为:“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31]他又说道:“至于老子的思想在我国很重要……若读《老子》原文,势必先听取那些训释考证家的意见,这不是中学生所能担负的。如果有这么一篇普通文字,正确扼要地说明老子的思想,中学生读了也就可以了解老子的了,正不必读《老子》原文。”[32]
不难看出,叶圣陶是在不断压缩语文教育内容。作为现代语文科的主笔人,叶圣陶所持有的迁就语文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语文科的学习范式。纵览语文教育史,不仅是叶圣陶等语文教育名家持相似的看法,而且历来的课程标准同样秉持此理念。如1986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删除了逻辑知识,2000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淡化语文知识教学等等。实际上,如果课标存在淡化知识倾向,那么一线教学就会不讲语文知识,规避语文知识教学,如此一来,学生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都不能了解和掌握,又怎能把句子写好,而将语文核心素养提高?
三、取法其中,得乎其下:语文科创生的进路反思
反思语文科的创生进路,旨在从语文科的源头上分析问题。语文科创生的一百余年来,语文科似乎总是在批评与改进、问难与求索中艰难前行。五四以降的语文科,无论是对学科本身的研究,还是从语文科对社会的作用方面的谈论,其背后似乎有急欲打破传统的情绪使然。因此,建立迥异于传统教育内容似乎更契合时人心意。从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成了普及教育和扫盲的利器。
与此同时,在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后,实用思想、儿童本位思潮与普及教育的集合又钳制了语文科内容的创生。因此,无论是在语文科备受批评的年代,还是深度学习时代的来临,语文科却一直面临着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在起点上“取法其中”,自然在结果上“得乎其下”;另一方面,由于语文科创生的主要目的在于普及教育,而当民众在完成了以识字为目的普及化教育后,如何提高学习者的语文能力,时人却没有再次思索。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语文科由于起步于普及教育,发展于迁就教育,其理路始终实践着两种学习范式:其一,为了人人,未考虑精英的语文教育,简单说来,为了让人人都能识字,人人都能写通顺话,语文科一系列的要求都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夠掌握语文能力,而这往往会让本身学习能力极强的学生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当深度学习时代来临,语文科不仅仅是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最基本的语文能力,而是需要复杂和深度的核心素养,此时,由于践行着普及教育和迁就思想的语文科,便难以回应时代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其二,受制于普及和迁就教育的语文科,仅仅是为了完成开蒙民众的历史责任,其理路并非符合语文科的学科规律。“如果我们从小只学低度的语文,我们长大之后一辈子就只能有低度的语文能力。”[33]如果我们从小开始就让他们学白话文,认为这样简单易懂,那么“这里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风险,如果学生学习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基本平行,甚至还要低于口头语言,就会严重制约学生的语言发展,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34]。
近代以来的语文科其实都存在用口语取代书面语的事实,或者让书面语向口语看齐的意识,这不仅不利于口语的提高,也会制约书面语的高级表达。而近代以来语文科遵循的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序列规律,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如王财贵认为认知能力的发展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好,他将其归纳为“学习能力递增原则”。在他看来,人类还有其他能力,如直觉的能力、记忆的能力、酝酿的能力等,这些能力“反而在年龄愈小的时候愈好,愈长大愈衰退。这种发展的模式,叫做‘学习能力的递减原则”[35]。而且对语文学习来说,“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言语‘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数量无限加大后,才‘奔涌而出”[36]。简单来说,语文科并不完全是遵循简单到复杂的学习理路,语文的学习其实更多是在反复习得、大量濡染的基础上才能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基本的知识镜像。或者说,语文学习更像是一个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一个从有到无、从有到有的过程。学习者只有先积累一定的字词和素材,才有属于自己的言语库,从而在此基础上遣词造句、作文达情,因此,语文学习更多是“举三反一”,而非是“举一反三”的学习过程。在这里,或许伯恩斯坦关于课程结构的分析能够给我们带来启发,他认为,数学学科知识之间是彼此闭锁的,需要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知识的统合。简言之,存在着不理解A就无法学习B这样的顺序性,这是学科的系列顺序使然。但是,社会学科往往更注重经验和活动,学科的内容之间更多是开放的、发散的[37]。在其学习过程中,确实不存在不理解A,就无法学习B这样的学习进路。因此,语文教育并不能严格地等同于数理化等学科的学习模式,数理化等学科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逻辑链和知识学习的先后顺序,而它遵循的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学习进路,其核心要义在于掌握基本的知识是形成复杂思维品质的必要条件。近代以来的学人,由于没有深刻理解语文科自身的规律,导致语文学科本身起点的羸弱,从而制约了一代代语文教学,制约了一代代学生的语文能力。
特别是在今天,当社会各界都要求给学生减负的时候,语文教育研究者却一直在呼吁学生多花课余时间去阅读,去写作,这无可厚非,甚至也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最可靠的举措,然而,有限的语文学习时间的和社会所要求的语文核心素养之间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语文课内的学习质量其实是难以支撑起时代所要求的语文能力。这也和语文科创生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进路有关,由于起点和过程的迁就以及一味地放低要求,导致了学科的后继乏力和低效。语文科的这一现象或许和运动员训练的情境颇为类似。简单来说,运动员在训练时的强度,往往会比正式比赛的强度要求更高,训练强度上去了,正式比赛才会有左右逢源、驾轻就熟之感;反之,则会左支右绌。这也意味着语文科目标要求的“了解一般的文言文的能力”或“阅读浅易文言文”,以及在程度偏好上仅仅注重读懂、大致读懂、能写简单的应用文即可等要求可能会令我们误入歧途。
语文科一直以来在普及和迁就教育的框架中辗转反侧,始终在普及教育的范式下不断重复着旧时的路径,而未能继续再前进一步,在如何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实现语文科的深度学习上作深远考虑,如此便很好地诠释了语文科“取法其中,得乎其下”的百年难题。
参考文献
[1] 王彬彬.语文病象令人忧[N].人民日报,2013-08-09(024).
[2] 王丽.中国语文教学忧思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126.
[3] 周越,徐继红.逻辑起点的概念定义及相关观点诠释[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05):16-20.
[4][7][8][9][10][1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7,117,117,172,172,170.
[5][16][23][24] 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上)[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45,22,58,206.
[6]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45.
[12] 朱麟公.国语问题讨论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47-51.
[13]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17.
[14]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四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87.
[15][17] 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102.
[18] 陈黎明,林化君.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学[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35-36.
[19][20]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304,303.
[21] 胡虹丽.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8-79.
[22] 张秋玲.百年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浅易文言文”[J].课程·教材·教法,2013,33(06):111-118.
[25][26] 钱穆.文话与教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39.
[27][28][29] 潘新和.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2,6.
[30][31][32] 中國教育科学研究院.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45,35,45.
[33][34][35] 王财贵.语文教育新典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5,6,22.
[36] 韩军.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之八大关系(一)[J].内蒙古教育:综合版,2010(15):4-5.
[37] 王荣生.写作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9.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