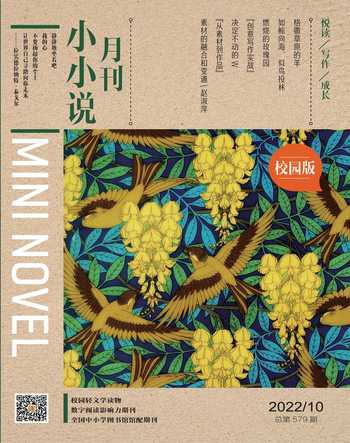成树
王文其
十七岁那年,我成了一棵树。
那天我放学回家,把书包一丢,扑向沙发,陷入深深的叹息。考试失利,朋友背叛,疲惫、懦弱、厌倦的情绪与家中的寂静杂糅在一起。我烦躁地打开电视,电影《泰坦尼克号》男女主角正在上演生离死别。刚下班的母亲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他们家庭背景、三观都不一样,都活下来也很难在一起——你不如多做几张卷子。”
我无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与父母之间有了隔阂,就像基本不同频的两列波。这就是现实,种种烦琐扰人的小事像石子般砸在我身上,细碎的疼痛让人无措。
我在沉默中选择了逃离,悄悄关上家门,漫无目的地走下去,走过无数岔路,直到走进一片森林。参天大树密密匝匝,弯弯曲曲地排列成神秘的弧度,围绕着一块草地。我的眼前仿佛有一片幽绿色的海在翻滚,嫣红的花和洁白的蘑菇漂浮其间,几只灰扑扑的野兔探出头打量着我。
我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发光的它,那棵小小的却挺拔昂扬的树。它对我微笑着,我向它靠近,有种莫名的安心,仿佛与它许久前就相识,而现在又重逢。在触摸到它的一瞬间,我的脚下生出了根,连接着大地,身体抽出了嫩绿的枝芽。我成了它,成了一棵树。
记忆碎片如雨点般落到我的叶片上,它的故事,不,现在是我的故事在倒序播放。破土之前,它一直静默着,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或许是人们随意丢弃的桃核,也许是有心人种下的银杏。它并不关注这些,鼓胀着身子,努力吸收所有能够吸收的养分,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长大。
钻啊,向上啊……小小的种子长出了白白的芽,泥土似乎掩埋得太深,压得它喘不过气来。但它向往着黑暗过后明媚的阳光,于是认定了追寻的方向。那隐隐的光,成了它不言放弃的唯一动力。
午后的森林,一派平和安详,它在微风中颤抖着,它已是一株幼苗,也只能是一株幼苗。它还太过柔弱,身边有太多的诱惑,有看上去很美实则饱含苦痛的危险。周围大树林立,这株树苗显得是那么渺小,食草动物来来去去,它随时都有被吞食的可能。最初的渴望融入这片森林的激情,一旦在现实触底,那种失望会无法释怀的吧?它苦笑。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是家中独女,自小被亲戚夸奖聪颖,但越大越平庸,父母似乎不甘心,寻找各种时机对我进行或严厉或婉转的说教,而我决定以沉默作为无声的抵抗。
直到一只红羽鸟停在了它的,抑或是我的枝头开始歌唱。我睁开了疲惫的双眼,见红羽鸟如此快乐,忍不住问:“这片森林符合你的期许吗?”
红羽鸟笑了,说:“为什么要求森林符合我的期许?森林不是为你而存在,不是森林需要你,而是你需要森林。你们这些年轻的树啊,似乎总是将自己置于对世界失望的状态,这其实是一种懦弱,一种逃避。”
我瞪大双眼,迷惑不解。
“你们在害怕未来。”红羽鸟继续说,“并不是只有沐浴朝阳才会拥有希望。未来不管是好是坏,坚持下去,即使畏惧着又渴望着,这就是成长。”从红羽鸟的口中,我知道自己已经从一棵幼苗长成了一棵树,虽然是年轻的树,但树这个词,真好。我努力地挺直着身躯,做一棵秀美挺拔的树。
几天后,我听到了父母的呼唤,他们和警察一起来找我。我凝视着他们,他们看不到我;我对树微笑,树微笑着看我。
我的双脚突然可以移动了,我向那一声声呼唤飞奔而去,离开前不忘与它——那棵年轻的树挥手告别。
母亲请了一个月的假,留在家中陪我。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一起窝在沙发上打盹,偶尔对视,忍不住扑哧笑起来。出差的父亲回来,为我带了礼物,是一本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那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我开始学着平心静气地面对各种烦扰,终究,是会雨过天晴的。
那片森林依然是我经常回去的地方,融入绿色的海洋,抚摸粗壮的树干,我会获得原始自然而又宝贵的能量滋养。我再没有遇见那棵年轻的树,也许它已经长大了,强壮的枝干不断向上、向上,攀住藍天,浮云成了它的装饰物,它的叶芽应是翠绿色的,那是春天里最耀眼的绿。
后来,我对母亲提起:“妈,其实我早就成树啦。”
母亲笑得灿烂:“成熟啊,是好像成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