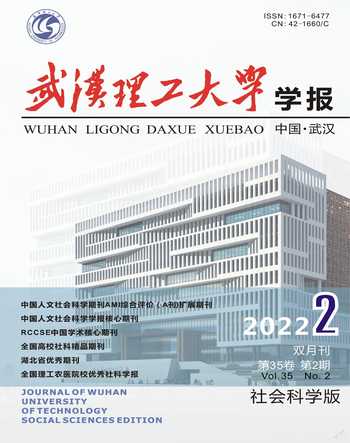论《民法典》视域下虚假基础合同中的有追索权保理
范倜

摘要: 在《民法典》视域下,保理合同在法律定性上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债权让与。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性质则为具有担保功能的债权让与,债务人为第一还款义务人,当债务人没有清偿能力或拒绝支付款项时,债权人才承担此项债务的清偿义务。在债务人、债权人、保理商及保证人四方当事人关系下,因虚假应收账款的出现,在债权届期后保理商可因保理法律关系向债务人、债权人及担保人主张付款权利。即使债务人没有订立虚假基础合同之恶意,只要保理商成功地举证其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则其不仅有权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相应的债权,还有权请求撤销保理合同,同时要求债权转让人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关键词: 虚假合同; 追索权; 保理; 债权让与
中图分类号: DF525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2.013
一、 由案例到问题
(一) 案情简介
原告A系从事国内保理业务的商业银行,2013年,被告B公司将其持有的对债务人C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A,该债权转让得到了C公司认可,并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签章确认。根据所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A行与B公司分别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同日,原告A与保证人D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由保证人D就该保理业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日,A行如约向B公司支付了保理融资款。后由于被告B公司未能如期偿还融资款,并拖欠多家银行贷款利息,原告A将被告B公司、C公司及担保人D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B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并由C公司及担保人D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本案例涉及的各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如图1所示。
被告C公司辩称,被告B公司与其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系伪造,不存在1880万元的应付款义务,因此,原告A受让的债权并非合法有效的,C公司无义务向B公司支付货款;被告D辩称,本案所涉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均为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目的在于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应认定为无效。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C公司偿还原告A《煤炭买卖合同》下的应收账款及利息;被告B公司支付原告回购款及利息,且被告D對上述回购款与被告B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B公司在完成回购义务后,原告A行享有的与之相应的对被告C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被告B公司,免除被告C公司就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向原告A行的偿还责任①。
(二) 各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及案件争议
就保理合同关系来讲,合同当事方仅有保理商与债权人,而不包括债务人[1]。而在保理所涉法律关系上,主要参与者有三方[2]34:
1.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商业保理公司(本案中系A商业银行),在保理合同中成为债权让与后的债权人。
2.债权人,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一般是基础合同的卖方(本案中系叙作保理的B公司)在签订保理合同后,债权进行了转让,成为保理合同中的债务人。
3.债务人,基础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人,一般是买方(本案中系《煤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C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后由B公司的债务人转变为A行的债务人。
实践中,保理商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会另外引入担保方,如本例中的担保人D。这样就有了四个主体:保理商A、债权人B、债务人C和担保人D。其中涉及的合同法律关系包括债务人(基础合同买方)与债权人(基础合同卖方)的商品买卖关系、保理商与债权人的债权转让与融资服务关系、保理商与债务人的继得债权债务关系、保理商与基础合同卖方、第三方担保方的担保关系等。而根据合同相对性的理论,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事实上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直到债务人就保理合同关系进行了确认或追认[3], A基于受让了B的应收账款,对C享有了债权请求权。
由案例引发的问题是,在基础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为虚假的情况下,保理合同是否继续有效,虚假合同中的“无辜”债务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是否要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涉及对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民法典》相关条文的理解。
二、 保理法律关系下的合同性质认定
(一) 保理合同内容的法律实质剖析
就一般的保理合同而言②,其性质属于一种有着突出商业管理特点的债权让与[4]。
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以及现行合同法上关于权利让与的相关法律规定及法理来看,债权让与一般需要:(1)标的债权合法有效;(2)标的债权不存在不得让与之情形;(3)让与人与受让人须达成合意,且不得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4)须有让与通知。在保理实务中,债权人将贸易合同及发票副本一并交付给保理商,一般也会同时将打印或粘贴在发票上的有关债权转让文据及介绍信一并寄与贸易合同中的买方,即应收账款债务人处。同时,保理商在进行应收账款的受让前都要进行尽职调查,确定转让债权的有效性,且在向债务人寄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同时要求债务人对标的债权进行确认,保证债权的真实有效及不存在不得转让之情形等。由此,从业务流程上来看,其符合债权让与的法定条件。
其次,从融资收回的必要性上讲,保理合同的标的所涉及的债权属于产权中的“权利财产”,在这类债权中,绝大多数用作保理标的的债只是纯粹的无形之债而非少数的票据或其他可预付工具,对此类债权的转让无法通过背书和移交来实现[2]63。此时,保理商为实现债的所有权,必须确保对债权的完全转移。这种独占地获得债务人清偿的权利,需要通过移转让与来实现[5]。
再次,从行为效果上看,保理商在支付了约定的款项之后,成为标的债权的所有人,从而替代了原债权人的地位,在应收账款到期之后,根据应收账款的转让协议(即保理合同)及债务人对应收账款转让的确认承诺,行使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之追索。此中,因保理合同的存在,应收账款的买卖行为在保理商与债权人中生效,而债务人经过通知后加入到了转让关系中,成为特殊的第三人③。这种买卖行为在法律效果上与债权让与无异。
最后,从国际公约和惯例上来看,应收账款债权讓与均成为对保理明定或默示的性质认定[6]。如在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保理公约》中分别在总则、当事人各方权利义务、再转让等各章中将应收账款的转让贯穿到底,突出了保理业务的核心为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制定的《国际保理通则》中,虽然是以程序性操作为主要条款,但在许多规定中也默认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为前提,甚至还有“反转让”(reassignment)的术语及规定;在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贸易中的应收款转让公约》中更是将保理业务内容纳入其中重点列举。
综上,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从《民法典》第761条对保理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到,转让应收账款属于债权人接受保理服务的一项前提行为。此外,《民法典》第769条规定,保理合同章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由此,保理合同作为一类有名合同,在法律定性上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债权让与。
(二) 有追索权的保理法律关系下的合同性质
如何界定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的性质?从法律定义的角度看,《民法典》虽然在第766条中对有追索权的保理商就追索权的行使作了规定,但对有追索权的保理并未明确进行定义,根据现行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以下简称《纪要(一)》)中关于有追索权保理的定义④,笔者认为,有追索权保理主要是指在保理商为债权人提供融资服务之时,不论任何原因,在应收账款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的情况下,保理商有权向转让人进行追索,要求其偿还未收回应收账款、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本例中,保理商A与债权人B在《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A为B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提供保理融资额度人民币1500万元,买方/债务人(应收账款的义务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拒绝支付全部或部分的应收账款,或者出现危及或可能危及我行应收账款按时、足额收回的其他事实或行为,A行均有权立即向B公司追索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有权从B在A行开立的账户上扣收其应付的款项。”该约定内容符合《民法典》第766条中关于保理人在追索债权时可主张之对象的规定,因此A行与B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属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不同于无追索权的保理,在有追索权的保理法律关系中,债权人B并没有因为转让了债权而摆脱其在融资服务中与A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作为第二付款人,继续承担应付款的风险。
1.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类型辨析
保理并非一个性质单一的法律概念,它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在《民法典》出台之前保理合同是无名合同,被普遍认为是复合型合同[7],同样地,作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也涉及了多重法律关系,其性质与一般类型的合同有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分。
(1) 与借贷合同的区别。在德国,主流学说上将有追索权的保理归类为贷款合同。因为其风险分配与买卖合同的风险分配并不相适应,而是与贷款合同的风险分配相适应:债权人B在债权不能收回的时候必须偿还该现金预支。在结果上不能最终保有该金额,而只能在特定时间段内保有,除非保理商从债务人C处获得相应的对等价值[8]。然而,有追索权的保理与一般借贷行为仍存在以下区别:其一,保理商提供的资金本质上是预先支付的购买应收账款的代价,而并非纯粹的贷款;其二,保理融资是基于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的保理协议,而不是借款合同;其三,保理所涉及的债权是直接基于基础合同而产生,与融资行为没有直接联系;其四,融资资金转移后,其并非在卖方资产负债表上列为负债,债权仍指向卖方;最后,若因基础合同发生纠纷,债务人拒绝履行债务,保理商可以从剩余款项中冲抵而自行清偿,而贷款合同形成独立债务,不能自行清偿⑤。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保理合同纠纷的意见中也指出:“保理法律关系的实质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涉及到三方主体和两个合同,这与单纯的借款合同有显著区别,故不应将保理合同简单视为借款合同。”⑥
(2) 与债权质押合同的区别。依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担保利益是指以一定财产客体担保给付义务履行的利益,担保客体是指已经设定担保利益的财产,包括已出售的账款在内。担保账款作为担保客体也可以被出售。无论是应收账款担保还是应收账款出售都具有融资功能。债权质押合同的性质可以为有追索权保理的融资功能提供解释,但并不完全符合保理的现实[7]。其一,应收账款质押是一种融资从属的担保方式,在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基础上可以开展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而有追索权的保理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业务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兼具应收账款催收、销售分户账管理、信用风险担保及保理预付款融资等功能;其二,根据《民法典》第445条有关权利质权之规定,应收账款出质以登记作为成立要件,而附追索权的公开型保理只需将债权转让信息通知债务人即可成立,隐蔽型保理中保理双方都不负有通知义务;其三,应收账款的所有权在权利质押合同中没有发生变化,而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其所有权已让与了保理商,且待债务人拒付或无力支付欠款时,原债权人还负有对应收账款的回购义务;最后,请求权的行使对象不同。债权质押中,第一还款人是应收账款债权人,而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第一还款人为应收账款债务人,只有在回购的情况下,保理商具有请求债权人支付回购款的权利。
(3) 与让与担保合同的区别。德国物权法将保理制度规定在了担保性债权让与之下,即指在债权人为了针对其成立的债权进行担保,而向其债权人让与他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情况[8]。二者的共性在于,受让人或者债权人所获得的所有权均是确定,是附有一定条件的,会因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情况而丧失。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性质属于债权让与担保[9]。这在强调担保功能的同时兼顾了债权让与的基本形式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二者的不同亦不容忽视。首先,以主流观点对于让与担保的定义来看[10],债权人在保理融资范围内承担首要清偿责任,而应收账款以质押财产地位存在,债务人实质上仅是以质押债权债务人身份被动加入保理关系,这并不符合保理的实际追索顺序。其次,转移所有权的主从地位不同。让与担保中以其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为主,转移债权是其辅助手段;有追索权的保理中,权利转让的关系为主,附追索的担保为辅,债权的移转不具有担保目的。最后,让与担保强调的是担保为首要目的,强调的是物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11],因此一般不转移占有;而有追索权的保理中,其基本目的还是在于权利转让,因此一般是由买受人占有。
2.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质探究
本案中,B公司将其对C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A行,并向其承诺在C公司拒付或无力支付应付货款时,A行有权立即向B公司追回剩余应收账款。从字面约定来看,虽然A行首要的债权请求权的行使对象是C公司,但只要无法完成应收账款的全部追回,B公司对A行仍有最终的还款责任。由此可见,在保理合同中为A行赋以回购式的追索权利,实际上是将对C的应收账款债权非永久性地让与给A行,用以担保A行对B公司的贷款能够得到清偿。在这里,贷款的发放及其担保处于中心地位,因而有追索权的保理承担着一种保留还款风险的担保功能[3]。
作为保理合同的一种,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其基础仍然是债权转让关系[7],同时,在债务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赋予保理商一个向前追索的权利,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附担保条件的债权让与。有追索权保理的制定来源于保理商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如果他应该对该发票进行支付,他必须能够通过对卖方的追偿而使其支付得到清偿,在一般的保理合同中也会要求卖方提供一定的担保,主要在三个方面:(1)债的有效性。即產生债的目的商品已被交出,该商品与卖方和债务人间的合同相符[2];(2)债的无责性。即债务额度要如发票所述,债务人将接收货物和发票,因此不存在任何争议、扣减、抗辩、反诉要求或抵消。以上两种担保分别与买卖合同中关于物的瑕疵担保以及权利的瑕疵担保相对应⑦。而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保理商得到的担保多了一层;(3)债的可收回性。此处的“债”不仅包括上两种由基础买卖合同而产生的债权,还包括保理商因融资付款行为而对原债权人(即基础合同的卖方)产生的债权。在债务人因履行不能使得保理商无法按期收回债权时,保理商有权请求原债权人承担该项债务的付款责任或者支付融资款。对于第一项请求,其法律性质属于一般保证,这种还款的第一来源是债务人,在其不能偿还时,才得向第二还款人主张承担还款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将债务人不偿还债权的风险从受让人保理商处转移到了债权人自己身上;对于第二项请求即相当于一种债务的偿还,保理商向债权人支付了一笔融资款,在约定期限届满或条件成就时⑧,保理商有权向债权人追索该融资款。也有学者提出了间接给付理论[12],讨论新债与旧债之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将保理合同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更多地看作借贷关系,这并非保理债权让与的根本法律性质,对此不予认同。与一般保理合同内容的根本性不同在于[13],有追索权的保理中,在债务人的意思表示本身没有瑕疵的情况下,要同时担保不因其他原因使得债权或者融资款无法收回,这是一种承担债务人不履行债权的风险担保,即原债权人在转让债权之后买方支付债权的风险没有随之移转⑨。因此,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应为具有担保功能的债权让与。
三、 虚假基础合同对于各法律关系的影响分析
本案中,B公司与C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被认定为虚假交易合同。由此,作为交易基础的应收账款自始不存在,这就必然导致保理交易之下各法律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进而影响各当事人间的风险分配与责任承担。《民法典》第763条中规定,在应收账款为虚构的情况下,除非保理商在交易中知情,否则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作为其支付款项的抗辩,该项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处理虚假基础合同下的保理合同关系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论认识,笔者将在下文就保理商与债权人、保理商与债务人、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及保理商与担保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
(一) 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保理商与债权人间的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在转让债权无效时是否会受到影响呢?笔者认为,首先可以从保理性质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即保理是以债权转让为核心的商业行为,在债权不存在时,并不一定会使保理合同无效。关于合同法上债权转移的依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为普通债权合同说,一种为准物权合同说。前者为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支持,其实质是以意思主义为基础的物权变动模式,认为在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一旦达成意思一致,即发生所有权的移转,只是未经公示或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后者以德国、中国台湾为代表[14],认为债权让与协议为准物权合同,认为转让协议独立于其原因行为,为无因契约,即使原因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或者被撤销,转让协议依然有效[15]。我国主流虽认为债权转让合同系债权行为,但在物权变动上采取债权形式主义[16]。也即,在基础货物买卖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之时,作为准物权合同的保理合同不受影响,应当独立于基础合同来进行判断。也有学者从合同相对性来解释,称虚构、伪造的基础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根本不成立,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事,不应对保理商和债权人订立的保理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17]。此外,在上文提到,债权人负有对债权有效性的瑕疵担保,因此,在债权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约定,债权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保理商有权解除保理合同。
在司法实务中,在基础合同认定为虚假之后,有的判决认为此时的保理合同无效⑩,有的判决则认为“尽管债权人存在虚伪意思表示,但作为保理合同另一方的保理商如果无通谋意思表示,则不应以此为由认定保理合同无效”[18]。如果仅是债权人存在虚伪意思表示,虚构与债务人之间交易文件或是与债务人串通形成虚假的交易文件,抑或骗取、伪造债务人签章形成的交易文件,将这些文件提供给保理商,保理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债权人达成保理合意,保理商不存在与债权人之间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保理合同无效。在这样一种共识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基础交易为虚假的情况下应区分保理商是否善意,区别对待保理合同的效力。这一观点正是考虑到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存在通谋意思表示的可能性,基础合同的无效能否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对此,比较法上有很多立法例,如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都明确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19],这已是公认的法理。另外,在《民法典》出台以前,最高法院有案例也是用法理认定了这个问题,结论是基础交易的虚假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若保理商为善意,则有权请求撤销该合同,并可向债权转让人主张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即便保理商并非善意,亦不当然认定保理合同无效,而是以其实际成立的法律关系适用相关规则决定合同效力。保理商明知虚构基础合同事实的情况下,债权人对此是否享有抗辩权,《民法典》对此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既然保理商明知基础合同性质存在无效、可撤销的事由,则自然不存在保护其信赖利益的必要,法律自然不可赋予其主张撤销合同、并要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权利。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有必要借鉴上述域外法之规定,明确“基础交易的虚假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则。
(二) 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前文案例中,当基础货物买卖合同为虚假时,保理商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务人就此不再承担任何义务,由于债务人在债权让与之前对保理商进行了确认,这便使得债务人产生了另一种法律行为。从实际交易状况来看,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基于货物买卖成立的债权合同之效力,保理商很难知道。其间债权是否因清偿而全部或部分消灭,债务人是否已主张抵消等,对于保理商而言皆很难知情。且如果债权成立和存续中有瑕疵,保理商必须完全承继。若不如此,则對债务人的利益会造成很大损害。也即在转让人与受让人做出与债务人意思无关的债权让与行为时,必须保证债务人的地位不因让与而造成不利。然而,对于作为债权受让方的保理商来讲,其在我国之前的法律制度上受到的保护是有限的。《日本民法典》第468条第1款规定了债务人对债权让与作出无异议承诺时,对原债权人所主张的一切抗辩即被切断,因而受让人取得了无瑕疵的债权。《德国民法典》第405条规定,制作关于债务证书的债务人对善意的无过失的受让人不得主张债务负担行为是虚假的[15]。
有学说认为债务人的承诺与让与通知的法律性质相同,都属于观念通知[17],但笔者认为,在虚假应收账款的转让中,进行债务确认的债务人与收到转让通知的债务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原因在于债权转让通知属于保理商或债权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债务人仅是被告知而不需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但是在本案的法律关系中,债务人对基础合同关系的确认,表明其知晓标的债权转让的事实,对此不持异议并加以承诺,意味着债务人放弃了抗辩权及其他相关权益。这种承诺直接加强了保理商的信心并决定了其对于债权人的贷款行为,且在保理实务中,债务人对基础合同债务的确认承诺通常属于保理融资的必备环节。此时,该承诺实质上具备了一种担保功能,即对债权可收回性的担保。有的学者认为,债务人向保理商作出了单方承诺,认为保理商基于债务人的单方承诺获得了在应收账款范围内向其主张清偿的权利。笔者亦同意其观点。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在我国合同法中借鉴德国、日本的法律规则,增加债务人就债权转让确认承诺时的约束条款,提高对受让人的保护。债务人是否有还款义务,应取决于其在虚假基础合同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债务人自始至终对基础贸易合同都不知情,笔者认为债务人没有过错,且不具有债务人身份;但即使债务人没有订立虚假基础合同之恶意,即便其是在不甚知情的情况下对相关债权进行了确认,且此时保理商在保理申请审查时尽到了审慎义务,则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保理商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当然成立。这一点在《民法典》第763条中得到了体现,对善意保理商采取了与《日本民法典》一样的全面保护。
(三)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原本在保理合同的法律责任承担中,第一还款义务人为债务人,在债务人未支付应收账款债款时,债务支付义务转移至债权人处,继而债权人需对保理合同承担最终清偿义务[20]。从义务承担的关系上二者可以视为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关系,因为二者虽都对应收账款具有还款义务,但还款义务的发生原因不同:债权人是因为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而债务人是基于债权让与后形成的继得债权债务关系。两方主体对共同目的不具有主观关联。当货物买卖合同为虚假且债务人对该虚假应收账款不知情时,两方自始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不具有向债权人还款义务,更不具有向保理商支付债款的义务。然而在本案中,由于债务人虽不知情但其已于保理关系发生时向保理商单方确认承诺还款,即需向其支付允诺金。结果相当于代虚假债权人无条件支付了应付账款,债务人因此利益受损,而债权人相应地逃避了债务获得利益,债权人应当向债务人返还不当得利。与本案不同的是,《民法典》第677条所规定的虚构应收账款是在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以骗取保理商信赖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共同虚假行为,作为责任后果,债务人当然不能以债权不存在为理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四) 保理商与担保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原告A(保理商)与担保人D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就该保理业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担保合同的主合同为该保理合同,其有效性依据保理合同的效力而定,若保理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当然无效。经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保理合同的效力不因基础合同关系虚假而被认定为无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理项下的从合同担保合同应继续有效。
然而,担保合同作为独立的合同,本身即存在无效的可能。如果债权人在请求保理商承担担保责任的过程中,以虚假的事实说明保理关系,从而使得担保人相信并缔结保证契约,则一般视为欺诈,构成第三人欺诈,依据《民法典》第149条之规定,若相对方保理商对于欺诈行为知情或应当知情,则担保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其次,在日本民法中,将担保人由于误信有其他连带债务人或有其他确定的担保而签订担保协议的行为称为作为错误,认为该行为属于认识错误,担保人对债权仍应承担保证责任[15]。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对其借鉴。此外,根据有追索权保理的性质,在保理法律关系中,债务人为第一还款义务人,当债务人没有清偿能力或拒绝支付款项时,债权人才承担此项债务的清偿义务,也即债权人的还款义务是劣后的。这样一来,担保方也就随之获得了一种劣后还款的顺位利益[18],在其预期里,还款义务至少是在债务人之后。这种情况下,如果基础债权为虚假,且保理商自身存在过错而导致债务人免责,则债权人承担了第一还款责任,担保人的顺位利益也因此消失,这时担保人有权主张其不应当再承担担保责任。也即在基础合同为虚假的情况下,因为保理商的过错导致债务人免责,那么担保人亦可主张免除担保责任。
四、 从理论到问题:本案中当事人的责任分配
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并结合上文的分析,在本案中需要承担责任的当事人有保理合同中的债权人B公司、基础合同中的债务人C公司以及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D。各方的责任分配及法律依据如下:
首先,由于债权人B公司制作了虚假的货物买卖合同,导致债权转让交易的目的无法根本实现,因此B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作为准物权合同的保理合同,其中B公司未能如约保证债权质量之时,保理商A行可以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或者另一方面,由于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为具有担保功能的债权让与,A行可以依照合同约定,请求B公司无条件承担债务人付款责任。
其次,对于非真正的债务人C公司而言,由于基础合同的虚假,且在A行递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应收账款核查通知书》时加盖公章进行确认,则不论债务人就虛假应收账款是否知情,在法律上已经具有单方承诺的效力。考虑到对于善意方A行的保护,C公司因其故意或者过失的行为,应当按照确认书中承诺的金额对A行进行支付。
再次,尽管本案的担保人D一直强调本案所涉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均为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目的在于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不符合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笔者在上文分析中提到,在没有充足证据表明保证人的担保行为系因债权人、保理商的恶意欺骗而产生的误信,那么担保人仍负有对保理合同的担保义务。因此,作为连带保证人,担保人D应当承担向保理商A行付款的责任。
综上,在保理合同到期时,保理商A行可以同时向债权人B公司、担保人D主张支付保理合同项下的融资款及约定的利息。对于非真正的债务人C公司,A行也可主张其支付确认书中的承诺款项。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中的法院判决正确。在担保人D支付了融资款项及利息后,“债权人对于主债务人之债权,于其清偿之限度内,移转于保证人。”[21]保证人D可向债权人B公司主张清偿。当C公司向A行如约支付承诺款后,C公司即可向B公司主张该不当得利的返还。以上规则在《民法典》第689条、763条、985条中进行了体现。但是关于在一般保理案件中当应收账款转让人拒不支付款项时,《民法典》仅规定了保理商可以向债权人及债务人主张权利,但对于该主张是否具有先后顺序,并未明确说明,期待相关规定在后续司法解释中予以增补。
五、 结语
司法实践中,保理商起诉的诉求往往不一,有“返还保理融资款”、“支付溢价回购款”、“支付债权回购款”、“偿还融资本金”、“回购应收账款”等,实际上涉及到应收账款转让中“追索权”内涵外延的确定问题[20]。此外,在法院判例中笔者发现,对于同一类型的法律事实法官有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究其根源,仍是在保理定性上认识不清。保理合同章纳入《民法典》后,保理业务从无名合同到记名合同,从引用债权转让的一般规定到遵守具体的法律规定,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是对保理业务的立法确认,为今后保理业务的发展及纠纷的有效处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追索权保理与一般的债权担保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在实际操作中[22],往往是保理商的债权因自应收账款债务人处得到偿付而消灭,而鲜见债权人直接支付本息,即所谓的“由应收账款债务人承担第一还款义务”。理论上只有在应收账款债务人拒绝或没有能力支付款项时,保理商才转而向原债权人要求其承担保理合同项下约定责任。此外,亦需站在不同角度来看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例如所有权是按照利益内容而被分割的,对于保理商是担保功能,对于债权人,资金的融通功能则处于中心地位[10]。
《民法典》中关于保理规则的制定内容仍有不足[23],笔者希望在后续司法解释中予以细化。将商业实践和商业惯例中的保理制度上升为保理法律规范,明确保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但有利于解决前述纠纷裁判中的困惑,最终也将促进保理作为商业交易模式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注释:
①参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山东鑫运达煤业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济商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
②本文所探讨的保理合同,是指以购买应收账款为主要服务内容的保理合同。
③因为债务人的身分比较特殊,日本民法将债权让与的第三人分为债务人和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两种。
④《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款提到:“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商业银行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有追索权保理又称回购型保理。”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中规定:“有追索权保理:指保理商不承担为债务人核定信用额度和提供坏账担保的义务,仅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其他金融服务。无论应收账款因何种原因不能收回,保理商都有权向债权人追索已付融资款项并拒付尚未收回的差额款项,或者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
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其中第七点指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是成立保理的前提,而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则是保理关系的核心。”
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
⑦相关法条见《合同法》第153、155条的规定关于物的瑕疵担保的规定;第150、151、152条的规定关于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
⑧在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中,该约定条件为消极条件,即在任何情况下,保理商不能从债务人处获得应收账款清偿时,条件即成就,此后,保理商得就应收账款未偿还部分向原债权人进行追索。
⑨在一般的保理中,保理商承担债务人支付债权的风险,为此保理商获得一笔风险酬金。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与此相反,支付风险仍在债权人手中。
⑩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赣民二中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指出,由于公安机关对相关当事人所作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购销合同》系虚假合同的客观事实,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保理商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成立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前提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在上述债权并不存在的情形下保理商与债权人签订的保理合同也就失去了事实基础,双方之间未能形成合法有效的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本案所涉保理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参见我国《合同法》第82条,《德国〈民法典〉》第404条,《瑞士债务法》第169条第1款,《日本〈民法典〉》第468条第2项。
日本民法第468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无异议地作出前条之承诺的情况下,不得以可对抗让与人之事由对抗受让人。但债务人为了消灭其债务而向让与人支付财物或承担债务的情况下,不妨碍债务人取回该财物或将该债务视为没有成立。”这就是所谓的“无异议承诺”。
《德国〈民法典〉》第405条规定,对于在出示证书情况下的债权让与,如果受让人信赖由债务人出具的证书,而从该证书中不能够辨识禁止让与的内容,则债务人不得援用第399条第2项的规定主张让与无效。
[参考文献]
[1] William C.Philbrick.The Use of Factoring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 and The Need for Legal Uniformity as Applied to Factoring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Commercial Law Journal,1994(99):141.
[2]弗瑞迪·萨林格.保理法律与实务[M].刘园,叶志壮,译.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5.
[3]李珂丽.国际保理法律机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185.
[4]朱宏文.国际保理法律与实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22.
[5]田浩为.保理法律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5(5):94-100.
[6]黄斌.国际保理:金融创新及法律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3.
[7]谢菁菁.国际保理中应收账款转让问题研究[M].北京:中國检察出版社,2011:76.
[8]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M].申卫星,王洪亮,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52-653.
[9]陈本寒.新类型担保的法律定位 [J].清华法学,2014(2):87-100.
[10]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7.
[11]费安玲.比较担保法:以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和中国担保法为研究对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44.
[12]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19.
[13]Moore,Carroll G.,Elkins,Marshall A.International Factoring:The Practical Advantages[J].24 UNIF.COMM.CODE L.J.,1981(Fall):115-120.
[14]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M].王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59-460.
[15]张谷.论债权让与契约与债务人保护原则 [J].中外法学,2003(1):26.
[16]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J].法学,2003(7):55-61.
[17]李超.保理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137.
[18]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国内保理纠纷相关审判实务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5(10):70-74.
[19]武腾.无效、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与善意第三人保护[J].清华法学,2018(1):152-168.
[20] Joubert.The Nature of Factoring Contract[Z].104 S African L.J.93.(1987).
[21]程啸,王静.论保证人追偿权与代位权之区分及其意义 [J].法学家,2007(2):92-99.
[22]罗欢平.论保理的法律性质:兼论应收账款担保融资的现实需求[J].学海,2009(4):167-171.
[23]黄和新.保理合同:混合合同的首个立法样本[J].清华法学,2020(3):179-190.
(责任编辑文格)
Recourse Factoring in the False Basic Con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Code”
FAN Ti
(School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Abstract:Factoring contrac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Code”,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special creditors right.The nature of the recourse factoring is the assignment with guarantee to repay,and the debtor is the first repayment obligor.When the debtor is unable or refuses to pay,the creditor will resume the obligation to pay off the debt.Amo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btor,the creditor,the factor and the guarantor,due to the occurrence of false accounts receivable,the factor can claim the payment from the debtor,creditor and guarant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ctoring legal relationship at the time the debt is due.Even if the debtor enters into a false basic contract without malicious intent,the factor,if successfully proving that he is not in breach of the duty of care,has the right not only to claim the right to payment owed by the debtor of the accounts receivable,but also to cancel the factoring contract,seek for redresses such as return of property and compensation.
Key words:false contract; right of recourse; factoring; assignment of de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