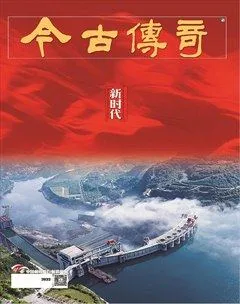没有送出的礼物
杨金娥
母亲一生都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即使是我们成家立业、条件殷实之后,母亲的生日也总是全家大团聚,没有谁用心给母亲送过一件礼物。今年元旦前的一天,母亲得了一场大病仓促离去。这始终是我心底的一处痛,觉得一生愧对母亲。
7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县城读高中。对于一个穷得叮当响且有五女一男的农村家庭,母亲倾其所有供一个幺女读到高中,村子里找不出第二家。
有一天放学,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给谁过生日。我忽然想到,明天是母亲生日。正好明天是周末,我很想给母亲过个生日。
晚上,家住得近的同学都回家了,寝室空荡荡的。我想起母亲树皮般的双手,不苟言笑的面容,想起她每次眼巴巴目送我消失在里弄尽头,心里激动起来,翻身起床到夜市花一元钱给母亲买了一双劳保手套。长年累月的劳作,母亲的手已皲裂变形,有一双手套干活,总该好点吧!
天蒙蒙亮我就出发了。买了手套,我没有钱坐班车,只得抄小路回家。秋后的稻穗金灿灿的,向我点头哈腰。我兴奋地走在田埂上,想着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还有那个连遮风避雨都不能的老屋,心里充满温暖。
一个钟头后我到家了,母亲正早作回来。她吃惊地看着我:“怎么回来了?”我说:“没事,就想回来看您嘛!”母亲突然愤怒地说:“我有什么好看的,没什么事跑回来干嘛,高考在即,不嫌浪费时间吗?”
无端地受到母亲泼冷水,我的心情顿时灰暗下来,那不被理解的屈辱,如同鞋子里掉了泥浆,格外沉重。回家路上脑海里上演的温情画面,如肥皂泡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闷闷地扎进自己的房间。
躺在稻穗铺的床上,懊恼的情绪充斥在我心里。我明白了,在我这样的家庭,过生日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手套仿佛在一旁阴冷地嘲笑,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母亲进来看到书包里的手套,怒火被点燃了,问我:“买手套干嘛,花了多少钱,哪有戴手套干活的,庄稼人不需要这玩意。你看你,忘了自己是谁了?有那么娇气吗?这不是糟蹋钱吗?”
我憋住了委屈的泪水,没有吃饭,扭头就去父亲耕作的地里。过了一会儿,母亲来了,给我带来两张煎饼,让我吃饱了再干活。然后,从兜里掏出那双手套,让我戴上,说女孩子家,别让手打太厚的茧。我埋头干活儿,不接手套。母亲看我生气,讨好地说:“买都买了,就戴上吧!”我赌气地说:“谁说手套是买给我自己的,我有那么金贵吗?”
母亲愣了一下,再没看我,而是盯着脚下,喃喃自语:“哦,原来是买给我的,这又何必呢,等你有出息的那天,再给我买啊!”
顷刻,我泪奔了。
第二天出门,我始终没有勇气告诉母亲,这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想必,母亲早把自己的生日忘记了。我走出里弄时,回过头发现母亲已经在弄口缩小成一个点了。
母亲节这天,我带上母亲最爱吃却又舍不得买的樱桃,一双精致的手套,拎著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从咸宁赶到通城百丈潭,到母亲的坟冢前祭拜。我泪雨滂沱,肝肠寸断,打开手机播放一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上海里弄居住功能更新方式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