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大小·天人
杨世文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廖平经学,以“六变”著称,学界已耳熟能详。事实上,廖氏经学多变,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时势变迁与时代风气。廖平生活的时代,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僻处内陆的四川与全国没有两样。从学术文化上看,巴蜀自文翁启化,蔚为大邦,魁儒硕学,历代继踵。但至清世,达于国史、置之儒林文苑者实在少之又少。体现清代经学成就的正、续二部《经解》之中,竟无蜀人之作。虽然不能据此否认四川学者之贡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蜀學不振的状况。不过,这种状况在清光绪年间开始发生改变。张之洞督学四川(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年,1874—1876),创办尊经书院,以“读书”相号召。后来王闿运又以名士掌教尊经书院(清光绪四年至十二年,1878—1886),讲今文学,治学重大义而略训诂,亦影响蜀中学风。廖平在入尊经书院之前,受四川本地学术风气影响,喜读宋人书,醉心于制义、时文,目的当然在于取科第。但入尊经书院后,始觉宋学空疏无实,故钻研小学,从事朴学考据,学术兴趣发生第一次改变。清光绪六年(1880)以后,受王闿运影响,又觉训诂考据破碎支离,于是转求“大义”。不过,廖平治学不肯依傍,并没有按张、王所指示的治学道路亦步亦趋。此后他的学术兴趣不断发生变化,形成廖氏经学独有的特色。在接下来的50多年时间里,廖平经学多变,使人应接不暇: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大统小统”,四变“人学天学”,五变“天人大小”,六变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解《诗》《易》。其学六变(如果加上初变之前的二变,甚至不止六变),重点实际在于前四变,五变、六变只不过是四变的衍化而已。正如他本人所言,多变之中,有不变存焉。如果归纳“经学六变”,可以看到廖平经学的三个维度:古今、大小、天人。
一
汉代经学,有所谓今文与古文之分。但东汉末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①,混合今、古,今、古文界线渐泯。后世学者解经,不再区分今文、古文家法。即使有所分别,也只从文字异同上立说。廖平经学“平分今古”到“尊今抑古”的第一、二变,其实都是针对经学今古文的问题而展开。廖平认为,若就文字而论,不仅今文、古文之间有差别,即使今文、古文内部,也存在今与今不同、古与古不同的情况。所以经学今、古文之分的根本不在于文字,而在于制度。他的看法集中反映在写成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的《今古学考》一书中。其要点在于:不以文字而以礼制分今古;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周礼》为孔子早年之说,主法古;《王制》为孔子晚年之说,主改制。其他诸经制度,都是从《王制》《周礼》二经推演而来。但是,无论今文、古文,同出于孔子,不分轩轾。这就是所谓“平分今古”。
廖平以制度分今、古,张明两汉师法,被誉为经学史上的一个卓识。不仅康有为“引为知己”,俞樾也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先后受到廖氏“平分今古”之说影响,从晚清到民国,还有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顾颉刚、周予同等,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众所公认。对此,蒙文通等先生有的评,兹不赘述。
“平分今古”之说,解决两汉经学分派的问题。但是,同为儒家经典,为何《王制》与《周礼》在典礼制度方面会产生如此差异或矛盾?廖平以孔子早年晚年、法古改制作解释,其实只是假说,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因此,他继续对该问题进行思考,“发现”所谓古文家的传授渊源和师说,都是出自伪造,与孔子并无关系,而且西汉以前,谈经学者皆尊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孔子所作新经,并非旧史。根据这些“发现”,廖平作《知圣篇》以尊今文学,又作《辟刘篇》以驳古文学,其经学思想进入“信今驳古”的“二变”阶段。廖平还著有《周礼删刘》1卷,所删者为九畿、九州、五等封诸条,与《王制》不合者,认为是出于刘歆纂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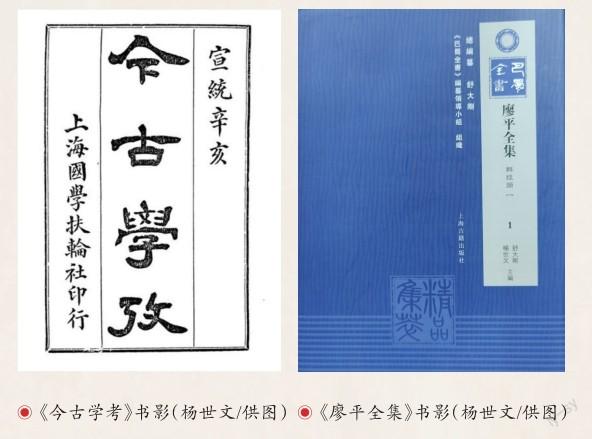
尊今抑古、不信《周礼》,用《王制》遍说群经,主张素王改制,尊孔子、抑周公,这是廖平经学二变的核心内容。《知圣篇》意在阐发孔子“受命制作”“作新经”“为素王”的微言大义,并认为“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互相启发,针芥相投。自失此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①。由于《知圣篇》《辟刘篇》持论与主流学界往往相左,成书后并没有立即刊行,但“东南士大夫因转相钞录,视为枕中鸿宝,一时风气为之改变”②。康有为受其影响,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倡素王改制说,人们追溯其思想渊源,认廖平为始作俑者。
对于廖的这些论说,张之洞非常不满。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冬初,宋育仁转述张之洞的戒语,并命改订经说条例。廖对张十分尊重,张对廖也爱护有加,张的意见,廖不能不加以考虑,据说廖平“为之忘餐寝者累月”。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这年十一月,他上书张之洞,解释自己并非以《王制》强说群经,且表示近来正在对《周礼》进行重新研究,最终力求将诸经“统归一是”,则“不必更立今古之名”③。从上书中可以看出,廖平关于今古之分、《周礼》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向“合通今古”的方向发展。
二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后,廖平经说发生重大变化,即以“大统小统”说取代“今古”说,从而泯灭今古界限,实现群经大同。以《王制》治中国,属王伯“小统”;《周礼》治全球,属皇帝“大统”。以《易》《诗》《书》《春秋》四经,分配皇、帝、王、伯四政;皇、帝、王、伯之分,由所治疆域大小而出。这是廖平“大统小统”说的核心。
廖氏经学的这一重大改变,与他以经学“经世”的情怀关系尤为密切。19世纪末,中国发生许多重大事件。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学说乃至历史地理知识蜂拥而入,远在西蜀的廖平也能读到大量的西学书籍,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中国发达,西方的制度具有优势,如果不抱残守缺、深闭固拒,不得不予承认。而进化论、地理学知识的传入,也使廖平这样的中国儒生开阔了视野。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世界。在对待西学上,廖平并非食古不化之徒,他竭力使自己理解西学,了解西方。但是,作为一位孔子的忠实信徒,他必须严守儒学疆界,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去解释世界,力图将西学纳入中国经典的知识体系。
改“古今”为“大小”,既是廖平经学思想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接受师友劝告而作出的必要调整。梁启超所谓张之洞“贿逼”之说固然不成立,但也不能否认廖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张的意见(尽管廖氏之说始终未能令张满意)。
经学分今古,尤其是信今驳古,虽然极力抬高了孔子的地位,但以古文为伪经,造成儒学内部今、古文之间的争讼互斗,终有割裂六经、分裂儒学之嫌,实际上不利于尊经崇儒。面对师友的批评,廖平不得不慎重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经说做到“既无删经之嫌,又收大同之效”。所谓“大通”,据《三变记》说,戊戌以后,将《周礼》删改诸条陆续通解,乃定《周礼》为海外大统之书,于是以前所删、所改之条,今皆变为“精金美玉”,无异于“化腐朽为神奇”。
廖平认为,《周礼》中所讲的“九畿”,《大行人》所说的“九州”,过去因其与《王制》不合,定为刘歆纂入之说,其实是不对的。《周礼》为专讲大统礼制之书,因其书专讲海外,故九畿、九州、万里,即邹衍所说的“大九州”,都与《王制》讲中法小统不同。《王制》中国疆域五千里,《周礼》海外疆域一万五千里,广狭不同,这在《诗》《易》二经中也有依据。《诗》中有“小球”“大球”之说,指地球而言。如《诗》之“海外有截”“九有”“九截”,《易》之“鬼方”“大同”“大川”“大人”“大过”,《论语》之“浮海”“居夷”,《左传》之“学夷”“求野”,《中庸》之“洋溢中国”“施及蛮貊”,邹衍之“海外九州”,其实讲的是海外大统,并非中国之事。《山海经》《庄子》《列子》等书,尤属讲海外的专书。
“大九州”之说,出自邹衍。但廖平认为,诸子为六艺支流,皆源本于六经。子学皆出于四科:道家出于德行,儒家出于文学,纵横生于言语,名、墨、法、农皆沿于政事。孔子以前之黄帝、老子、管子、鬻子者,都出于依托。如此,则诸子百家皆收归孔门。地球之事,孔子早已前知,地球千奇百怪,世界千变万化,不出孔经范围。孔子为全球之圣,孔经为世界大法,得以证明。
三
廖平“大统小统”说泯灭今文、古文界限,实现经学统一,经学不再分裂,群经归于大同,皆属孔子制作,为全球立法。但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廖平受佛学启发,逐渐转向第四变,着重讲天学、人学。
廖平注意到,以孔子为全球之圣,六经为世界大法,所治不过于“六合之内”,属于人学。顺着尊孔宗经的思路,廖平又将目光投身“六合之外”;不仅讲人学,也讲天学;不仅讲圣人,也讲至人、神人、化人。同时,《灵枢》《素问》《楚辞》《山海经》《列子》《庄子》《穆天子传》、释典、道书这些曾被儒生称为“诡怪不经”之书,皆得其解,都可以统摄于天人学之中。
廖平认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最能反映天人学之精微。《大学》为人学,《中庸》为天学。《中庸》中讲“至诚”“至道”“至圣”“至德”,于“圣、诚、道、德”之上别加“至”字,以见“圣、诚、道、德”有小大、至不至之分。后世儒者不讲天学,遂以圣人为止境,对于道家之所谓天人、至人、神人、化人,皆以为属经外别传,无关宏旨。不仅《中庸》有“至德”“至圣”“至诚”,《孟子》言“神人”,《荀子》言“至人”,《易》言“至精”“至圣”“至神”“大人”。《中庸》曰:“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可见圣人之外,尚有进境。因此六经有天学,有人学,“人学为六合以内,天学为六合以外”①。他承认,“天学”化境不属于现在,而属于未来科学进步、文明发展以后的情形,由此可见他对进化论有接受。
随着“天学、人学”的提出与完善,标志着廖平完成了对经学的重构,也实现了对儒学的改造,孔子成为教主,儒学变成孔教。廖平将经学涵盖的范围从“六合之内”扩大到“六合之外”。经学不仅规划了全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且扩大到整个宇宙;人类文明的成果,未来发展的方向,都在孔经范围之内。
四
由“今古学”转向“小大学”“天人学”,强调“素王制作”,廖平“经世”目的非常明确。作为一位经学家、教育家,虽然廖平一生并未从政,但他的经学思想具有明确的现实关注,他的经学建构是对近代“古今中西”冲突的回应。
近代中国的危机,正如张之洞所言,是如何“保圣教”“保华种”“保国家”的问题。此所谓“三保”,排列顺序实有深意。对于廖平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教”。在他们眼里,此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保种”“保国”的问题。面对当时“人才猥琐,受侮强邻”“守旧者空疏支离,维新者废经非圣”的现实以及儒学危机,廖平主张必须保教,而保教必须尊孔、崇经。要达致此目的,就必须将孔子与普通著述家相区别,将六经与旧史相区别,尊孔子为全球圣人,六经为万世大法。廖平经学辨今古,别大小,分天人,屡变其说,层层转进,其最终归宿,即在于是。
廖平经学尽管不囿于今文,但其治经方法是今文家的路数。因此,特别重视“微言大义”的阐发,是其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廖平认为,鲁、齐传经有“微言”“大义”二派,“微言者,言孔子制作之宗旨,所谓素王制作诸说是也;大义者,群经之典章制度、伦常教化是也”②。廖平提倡治经从条例入手,以制度为核心,即是重视“大义”的体现。在经学一变时期,廖平以礼制分今古,主要注重“大义”的探究。至二变以后,他在揭示“大义”的同时,更注重孔经“微言”的发挥。廖平强调经、史之别,经非旧史,皆为新创。经与史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言立教,垂法万世”,若以史学读之,是不知圣人神化。因他反对“六经皆史”之说,认为清人著作如《禹贡锥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说经,不得为经学。面对来势凶猛的西学冲击,廖平并没有回避。廖平对西学作了基本估价,主要有两条:一是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在于伦理,而不在于物质;二是中西之间的差异,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他断言,西方文明程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始由禽兽进于野人的阶段。理由是西人仪文简略,上下等威无甚差别,与中国春秋之时大致相同。孔子乃作《礼经》以引进之,设为等威,绝嫌疑,别同异,拨乱反正。
总之,廖平认为,孔经是拯救当时世界的良药,《中庸》说“施及蛮貊”,天生孔子,垂经立教,由春秋推百世,由中国及海外,独尊孔经,以拨全球之乱,推礼教于外人,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礼教固不囿于中国一隅。由此可见廖平以孔经规划世界的意图。
(作者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
①范晔:《后汉书·郑玄列传》。
①廖师慎编:《家学树坊·知圣编读法》,民国三年(1914)成都存古书局刊本。
②高承瀛等修,吴嘉谟、龚煦春纂:清光绪《井研县志·艺文四·知圣篇》提要。
③廖宗泽编:《六译先生年谱》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条引《答张之洞论学书》。
①廖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
②黄镕、胡翼等公拟:《致箌室主人书》,见《家学树坊》。案:实为廖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