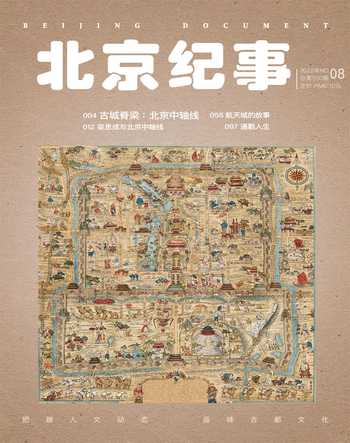雄阔的意象与理趣之美
施亮

李培禹年轻时与臧老合影
晚唐诗评家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论述雄浑的诗歌境界:“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也就是说,雄浑壮美的诗风应当有包罗万象的气势,苍茫无际又横贯太空的审美境界,犹如飞云流动,长风浩荡,既要有超越生活表象的宏阔意象,又要有发自生命意识深处的激情,不造作,不矫饰,不可勉强拼凑,须注重诗中内在旋律美与语言的轻灵质感,方可诗情醇厚,意味深长。在《失去》这部诗集里,我们可读到许多这样的优秀诗作。比如,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多家报刊选载并有网络歌手谱曲传唱的《赛里木湖的波光》。
作者李培禹去新疆的博尔塔拉州采风,被“世界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的辽阔和壮美所感动,原本想写一篇散文,几次欲动笔都觉得还是诗句更能够“发泄”情感。在诗篇里,美丽的“赛里木湖的波光/ 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也“让维吾尔古丽的发辫飞扬 / 她们跳起迷人的舞蹈”,又“把锡伯族猎手的眼睛擦亮 / 他们封存了骑射的弓箭 / 家乡更有了满坡满岭的牛羊”。诗人充分发挥了诗歌动态之长,将哈萨克小伙、维吾尔姑娘和锡伯族猎手三个意象相联。最后,开拓了一个新的深远意象维度,美丽又圣洁的赛里木湖“笼罩着29个民族的篷帐 / 他们和睦相敬的劳作与歌唱/在北疆一个叫博尔塔拉的地方”。这三组意象展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种宏阔之美,一种雄奇之美,也描绘了民族团结的时代画面。
在这部诗集的序言《读诗·品诗·写诗》中,培禹兄深情回忆起北京二中教师贾作人、赵庆培对他栽培的往事,他们用业余时间向他传授课本外的文学知识,尤其是赵老师与他谈起“宋诗的理趣”,开拓了他的写诗思路,影响了他以后的诗歌创作风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提出“风骨论”,创立了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思想,认为文学情感的抒发及表现,也就是“风”,必须渗透一种内在的理性力量,亦即“骨”,否则,无论文章或诗歌都会内容空虚,艺术品格也必定会软弱无力。在当今时代,一些诗人罹患严重缺钙的“软骨病”,沉溺于时髦写作的靡靡之风,抽空思想,玩弄技巧,“使诗歌变成了空洞的彩色气球”。甚至连真诚,诗人最低的起点都做不到。还写什么诗呢!这是老一辈评论家谢冕、徐敬亚的痛心之言。
前一时期,著名影视评论家、老友李京盛和我在微信中谈起对当代诗歌的看法时,就引用谢、徐的这一些话。我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所以,我认为我们如今重温“风骨论”是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诗歌中的“理趣”,当然不是宋诗的理学之理,体现的应该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人生哲理,抒发诗人不为时势所屈、不为利欲所动的人格精神。这种热烈的生命意识与情感抒发,正是某种理性精神的内在凝聚力的体现,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这其实是诗歌的另一重要特质。
这部诗集以《失去》为书名,《失去》一诗无疑是充分体现“理趣”之美的优秀诗篇,诗人对失去的人生题目做了六次形象譬喻:“失去是一次苦涩的落潮 / 失去是永远不再得到 / 失去是铅重的心忽地悬起 / 失去是晚风吹累了的螺号 / 失去是解脱来得过于突然 / 失去是倦旅中有了意外的歇脚”。里有人生挫折中的领悟,有痛苦情绪的凝聚,有迷惘感觉的抒发,有忧郁画面的白描,也有微言大义的阐发。而后便是简洁有力的结句:“懂得失去总是来得太晚/ 螺号的回音已是那么飘遥 / 然而,有些却永远失不去—— / 失去了才会真正知道。”诗人用“失去”的复杂系列意象,展示对我们生存真相的一些领悟与思考,最后达到对生命真谛的某种洞悉。
据我所知,原诗中还有两句:“不是所有的失去都是失去,不是所有的得到都是得到。”正式发表时,培禹兄删掉了这两句。我是当然赞同的,其实“失去”又是某种“得到”,这话是不必写出来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托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再吟诵《寂寞》一诗,即可深入感受“怊怅述情”的“风”之抒发,诗中尽情地抒写了惆怅情感,“寂寞是走不出的冬天”,对冬日做了富于诗意的过程白描,寒风,深夜,落雪,孤寂,“寂寞是泥泞中的跋涉”,疲惫的旅人哼着不成调的歌,脑海里却又纷扰着混乱记忆;“寂寞是压在肩头的日子”, 现代社会喧嚣扰攘忙碌中,手机里微信频繁,各种人焦虑呼叫,乃至赌气关机,其中隐含了人们内心的孤寂。诗人将现实的琐碎信笔写出,没有任何铺饰的辞藻,天机洋溢,意趣内蕴,而自然意趣中又深含理趣。最后结句绝妙:“然而 / 寂寞,是一种情感!/ 寂寞,是一种尊严!”恰如刘勰所言:“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寂寞》一诗的“文骨”,就在于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山流水的人格之美,写出了甘于寂寞、抛却功名利禄的云水襟怀。《往事》一诗表现的也是这个主题,“一个成功的人回首 / 往事是叠映的骄傲 / 一个成熟的人回首 / 往事不再是种荣耀。”这几句诗也是饱含了盎然的意趣,而又形成寓意深刻“理趣”的范例,诗人将“成功”与“成熟”相对偶,然后如大匠运斤,未见丝毫斧凿的痕迹,道出了二者的不同人生感悟,其诗句的理趣,已经纯为一片天机,平淡语句却含有浓深人生哲理意蕴。尤其是诗的后半段,还写到进入老境的苦涩心态,“往事常在梦中萦绕”,许多故友离去,人生知音越来越少,进一步又在诗中阐发了视功名利禄为身外物的人生态度。这其实也是作者“理趣”之核心。
我记得,青年时代的培禹兄如饥似渴搜寻著名外国诗人的中译本,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白朗宁夫人、里尔克、聂鲁达等经典诗作,他那时都读过,其中有些诗句还能够朗朗背诵。
先父施咸荣极赞誉他的这种好学精神,每当有出版社馈赠他外国翻译诗选时,总忘不了对我说:“给你的朋友李培禹啊!”培禹兄正是在老一代文化人关注与影响下成长的,他与著名诗人臧克家有着密切交往,受到臧老的深刻思想影响,在诗集“后记”一文有着生动记叙。他的诗歌创作也继承了郭小川、贺敬之、徐迟、金波等老一代诗人的优秀文學传统,所以,培禹的诗歌中选用的意象很朴厚、很宏阔,更注意开拓现实生活的创作空间,同时也注意继承古典文化的优秀精华,他的诗中有一股清新简约之美,且诗歌的情调自始至终洋溢着青春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