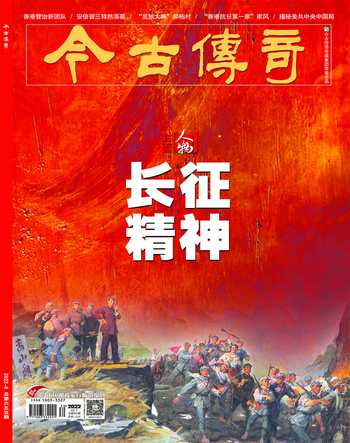罗雨中:“杀头无所谓,只求万世传英名”
1949年10月1日他无惧国民党架起的机枪在香港新楼街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罗雨中,原名罗观屏,出生于1919年。抗战期间,曾任南涌人民联防队首任队长、东江纵队税收总站站长。
1943年,罗雨中被捕入狱,不到十天,便经历了三次审讯,日军用尽了饿、渴、吊、打、电、钉、灌水等酷刑,都未能让罗雨中屈服。他始终意志坚定,顽强斗争,他说:“杀头无所谓,只求万世传英名!”
抢运:“这是什么样的军队?如此简朴,如此勇敢”
1937年,罗奕辉去世时,罗雨中刚满18岁。几乎在同一时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罗雨中说,他一生中最为骄傲的就是抗战时期没有坐以待毙,没有屈服在日军的残酷统治之下。
英国殖民者向日本投降后,罗雨中愤怒地表示:“只有我们这些真正的主人才会拼死保卫香港。”他带领人民联防队,开始了保卫香港的战斗。
1942年2月,港九大队成立不久,罗雨中就被港九大队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成为游击队的骨干。
罗雨中领导的人民联防队,参与了非常重要的抢运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南洋相继沦陷,没有了华侨和香港的支持,游击队的供给陷入困境。英军仓库存有大量游击队急需的物资,游击队要在日军全力组织进攻九龙和港岛地区的真空时段,抢先把物资运回。
抢运,陆路上的交通工具就是队员的两条腿和肩膀上的一根扁担。罗雨中领着人民联防队日夜开展抢运,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张饼三口两口就送进了肚子。
公开抢运的黄金时间只有十多天。1942年,日军在新界各区建立了警备队、宪兵部、区役所等机构,对所辖区域严密控制。但罗雨中等人的抢运没有终止,只是从公开转入秘密,从大型转入小型,物资采取分散速运,从存入仓库变为存入山洞。
此时的抢运无异于与虎谋皮,罗雨中等人不得不调整抢运策略:改走更偏僻的山径;运输队人数要精不要多;减少集中仓储,尽量快运快分配到游击队;运输时间改为晚上10时至凌晨2时。
罗雨中改头换面扮成乡绅商贾,五官端正、仪表堂堂的他穿上长衣马褂,戴上礼帽,在港湾监督货物装船,遇到伪军检查,他总能泰然处之。
英军的物资抢完了,罗雨中等人就去抢日军仓库。一天深夜,待武工队清除了日军仓库的守军,罗雨中便发动各乡精干组成的几支抢运队开始抢运。不承想遭遇了日军巡逻队,他们不得不在武工队护送下往大山撤退。队员们挑着重担,在崎岖的山路上小心行走。大家不开手电不讲话,一个跟一个,只能听到彼此的喘息声,支撑他们的只有一个信念:把物资安全运到游击队。
在日军眼皮底下抢运物资,危险重重。1943年5月,大环村的王丁有运送药物时被日军抓捕。日军把他拉到空地,强迫村民看他们对王丁有实施酷刑。无论日军用何手段,王丁有始终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西径村的李观妹,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逮捕,被割去了耳朵。这些抢运队员都是普通的百姓,却完成了神话般的抢运,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美亚》杂志曾评价抢运队员:當香港沦陷时,游击队立即派人到“新区”去将难民、军火与供应品运出香港。当年,正是他们,在3年零8个月中,完成了许多类似于巧运武器、运粮食、运送盟军等神奇的抢运,完成了这些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945年1月16日,美国第14航空中队飞行员伊根跳伞落在新界滘西的海面上,罗雨中等人救了他,还领他参观了队员们训练。伊根好奇队员们使用的怎么全是英式步枪,罗雨中自豪地告诉他:“这都是我们游击队从英军仓库抢运出来的武器!”
伊根看到这些衣着破旧的战士没有统一的军装,使用的手榴弹也是五花八门,有石片造,日本式、英式、菠萝式、美式,禁不住问:“政府给你们多少军费?你们如何征兵?”罗雨中告诉他:“政府没有给我们军费,枪支都是缴获的,每月几角钱的生活费,最好的时候一年发两套衣服两双草鞋。”
伊根吃惊极了:“这是什么样的军队?如此简朴,如此勇敢。”伊根最后参观的是海上中队的“战舰”:三条简陋的木船。伊根直言:“你们的船太小,没有机械,全靠人力,要装备炮艇,才能抵挡日军的炮力。”罗雨中说:“我们不能等到有了炮艇才抵抗日军。武器重要,更重要的是使用武器的人。”
罗雨中领导的税站是宣传队、征兵站、治安点、联络站
为了抢运开辟的三条运输线维持了3年零8个月,游击队还在这三条运输通道上设站收税。
1940年底,面对日军的全面围攻和经济封锁,游击队在多处设立税站,征收抗日捐税。第一站设在宝安县梅林坳,这里拦路打劫的土匪很多,过往客商提心吊胆,站长陈前带领短枪队赶跑土匪,在路边插上一面“自愿捐助抗日经费”的小旗,旁边放着块包袱皮,开始了“税收”。税站是流动的,采取薄收乐捐的政策,一担货收2角钱。税收人员向客商宣传抗日,表明游击队保护过往客商,客商们也总尽其所能地缴税。
1943年,罗雨中被任命为沿海税收总站站长,当时形势比较复杂,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犬牙交错,税站就建立在这之间。
罗雨中记忆中的税站不像税站,与今日的税务局有极大的不同,税收员也不是坐在办公室。唯一相似的就是都有正规的税收单据。
张广祥曾经担任沿海税收总站下属的沙鱼冲税站的会计,每天登记税款。他记得战时国内物资极其匮乏,许多紧缺货物,如轮胎、煤油,都是客商不惜代价通过香港运送回国的,运送货物的船到达沙鱼冲,靠岸后商人会自觉去码头的税站缴税。
沙鱼冲税站只有20多人,但分工具体合理,有负责检查货物的,有负责写税单的,税单都有标准格式。税务员根据货主填写的货单核实物料,然后按税率写上税项。虽然说是核对,但一般很宽松。税收人员与客商彼此信任,客商有时还会送些衣物或鞋子给游击队。这样的税站,在沿海有很多,都在有序有效地运行着。
税站大部分远离领导机关,税收人员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夏天睡在荔枝园、山林和岩石洞,冬天睡在草丛、甘蔗地。常常不见天日,早上天没亮就赶早去税收点,天黑才收队回来。税收人员基本不拿枪,保护他们的武装人员大约有10个,或在路头路尾放哨,或在海岸线巡逻。
税站收的税款有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有的是汪伪政府的货币,这两种币天天贬值,面额也愈来愈大,税款有时多达几个麻包袋,无法一次性上交,更不能带在身边。罗雨中就想到将税款放在客家人坟边的“金塔”(客家人二次葬风俗,起出的死者骨头装进有塔盖的陶器,这种陶器被称为“金塔”)里。“金塔”就成了税站的保险箱。
税站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藏款地点,想挪用非常容易。罗雨中最赞叹和骄傲的就是税站工作人员的廉洁:生活这样艰苦,破衣裤,烂草鞋,起早摸黑,有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又累又饿,就是没有人私自动用一分钱,反而拼了脑袋都要保住税款,直到上交军需部门。
东江纵队3500人,税收队伍就有900人,占了约四分之一。每一分税款都是队员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收取的,或许就在收款的这刻,日军偷袭,子弹说来就来了,绝对命悬一线。税站是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常常遭到他们偷袭或伏击。
在许多税收人员的记忆中,遭袭击是家常便饭,所以保护税收人员的武装人员不能少,甚至是税收员的几倍,武装队伍还兼保护老百姓、护送商家的任务。
曾连山曾在税站武装排当战士,他回忆,他刚刚入伍时配发了一条枪和三颗子弹,一颗黑黑的打不响,一颗弹头缩进弹壳,只有一颗勉强能用。游击队里,比较好的武器都留给战斗部队,税站一般使用最差最老旧的武器。很多时候不敌日军。
1943年,何基所在的税站武装班负责保护罗雨中所在的小梅沙税站,他们每天早上都从小梅沙向大梅沙方向巡逻。一天,天蒙蒙亮,日军便来偷袭。何基等人边打边往山下撤。天大亮后,一艘日军电船开过来,几个隐蔽在岸边礁石的战士不停地射击,阻止他们登上沙滩。日军的海上部队和陆上部队一起攻击,炮弹和机枪一轮轮地打来,火力很猛,他们冲进税站后,把税站烧了。
这样的战斗反反复复,税站经常处于第一线的战斗状态,总是烧了建,建了又烧。罗雨中要求沿海总站各分站部属认识到“税站不仅仅是税站”:
税站是宣传队。税站所设地点大多公开,每到新的地点,必定宣传游击队的抗日方针政策。动员群众支持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這样的宣传,让商人和老百姓明白他们是取信于民的抗日队伍。
税站是征兵站。游击队神出鬼没,流动性太大,常有想参加游击队抗日的青年找不到游击队。易找到的税站便成为征兵站,据说大概上千名青年都是通过税站引领加入东江游击队的。
税站是治安点。战争年代,土匪横行霸道,四处打劫。税站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打击土匪,惩罚恶霸,保护商旅和老百姓的安全。
税站还是联络站。税收人员都活动在水陆交通要道、闹市圩镇,大多接近日军据点,方便了解日军动向。税收人员接触面很广,熟识的商人愿意当游击队的耳目,日军有异动情况立即报告。
可功能强大的税站简陋得只有人,为了躲避日军,税收站人员常常上半夜睡番薯地,下半夜睡坟头,从未有过怨言。
日军对他实施了棒打、冷水灌、吊飞机、电击、十指钉竹签的酷刑,但他始终意志坚定
1943年冬,罗雨中被捕,从这一刻起,罗雨中作好了死的准备。
入狱后,罗雨中镇定自若,还通过堂弟罗东生(香港地下党员)将自己被捕的消息传给组织。
入狱第二天深夜,罗雨中突然被拖进一间布满刑具的房子:吊飞机的架子,打人的大木棍,灌水的水龙头、胶管,火烧的铁架等等刑具,罗雨中过去只是听说,今天亲眼所见。
罗雨中不断地与日军周旋,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没等罗雨中说完,几个日本宪查的大木棍就劈头盖脸地打来。几轮棒打后,日军得到的还是罗雨中的“我不知道”。
棒打失效,接着是吊飞机。罗雨中被押到吊刑架前的木箱子上,整个人被吊在刑具上。渐渐地,罗雨中两手关节“格格”作响,骨筋断裂的剧痛令他感到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几分钟不到,他全身被汗湿透了。
罗雨中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摇头,勉强从牙缝里说出“我什么也不知道”。
灌水是日军最热衷使用的残酷刑罚,罗雨中被紧紧固定在木梯子上,水管插进他的口中,水龙头打开后,水不断地灌入他的肚中。被灌水后,罗雨中始终没有招供,可是他的身体投降了,他像死了一样躺着。
后来的情况是别人告诉他的。两个200多斤的印度宪查踏上他的肚子,用力踩踏,水从口、鼻、眼、耳喷射而出……
入狱不到十天,罗雨中便经历了三次审讯,饿、渴、吊、打、电、钉、灌水等等酷刑都没有打败他,他对自己说:“杀头无所谓,只求万世传英名!”
日军无奈之下以他妻儿的性命相逼。罗雨中的妻子黄财娇不但默默支持罗雨中抗日,还是他的战友,她于1942年加入港九大队,负责组织妇女会和军需物资等工作。
面对妻儿,罗雨中心如刀割,怒吼道:“要杀就杀!为什么还要折磨我妻儿!”他转过身对妻子留下遗言:“要带大儿女,告诉他们,爸爸是被日本人害死的。”事后,罗雨中年仅两岁的儿子因受惊吓猝然身亡。
罗雨中后来被组织成功营救,出狱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意志仍然顽强。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自己的国庆,当然升挂自己的国旗”
解放战争期间,罗雨中继续在香港开展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罗雨中组织联乡会,在香港沙头角新楼街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当时,沙头角的华界仍被国民党萧天来部队控制,升旗的队伍与之仅有一街之隔。
萧天来听到消息后集合了大量兵力,全部枪口对准新楼街大会集中地。沙头角英警见状,喝令罗雨中等马上停止集会及升旗,罗雨中毫无畏惧,和新界乡绅代表直接到警署谈判。他说:“10月1日是我们的建国大典,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自己的国庆,当然升挂自己的国旗!”
罗雨中理智且强硬,要求警司加强警力,维持治安,保障升旗典礼顺利进行。在他的努力下,新界的六辆警车满载英警驶进沙头角新楼街,布防警戒,保卫升旗典礼。
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堂堂正正地升起了,罗雨中热泪盈眶:“中国人,我们,这片土地属于我们。”
(责编/张超 责校/陈小婷、李希萌 来源/《血脉中华——罗氏人家抗日纪实》,张黎明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血脉:烽火罗氏》,张黎明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