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献给战败者的史诗
赫晶晶
酝酿已久的战争小说
一八九一年四月十七日,一辆马车从兰斯出发,车中载着左拉夫妇,车夫兼向导是阿登省本地人,一行三人沿着沙隆第七军一八七○年的行军路线前往色当。此时,《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的第十八本小说《金钱》业已付梓,左拉正着手为即将落笔的新作收集材料。据一八九一年四月二日《费加罗报》报道,布鲁塞尔街的工作室里塞满了与普法战争有关的地图、回忆录和其他文献,作家埋头其中,做着密密麻麻的笔记。左拉在三月便写信告知好友雅克·凡·桑滕·科尔夫(Jacques van Santen Kolff)自己将去色当小住一周,“因为我特别想描绘骇人的色当战役,那是一幅巨大的画卷,最悲惨的厄运朝一个民族袭来”。新作品的框架已酝酿成形,但具体的故事仍悬而未决。这位作家喜欢在落笔前先寻找可靠的原始资料,他向雅克讲述自己收集资料的方式:“去我将要描写的地方漫步;阅读大量书面文献;最后,和我能接触到的事件亲历者长谈。”(Zola ?, Baguley D. La Déb?cle. ?uvres complètes-Les Rougon-Macquart,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XIX. Classiques Garnier, 2012)左拉将为期九天的田野调查手记命名为《我的色当之行》。他一边记录兰斯到色当沿途的地形地貌,想象第七军在荒原、树林、山丘、高原战斗的情形,一边拜访当地居民、旅店老板、媒体人士及镇长,收录他们提供的珍贵见闻及轶事。斯通隘口的恐慌、巴赛叶的最后一颗子弹、阿尔及利亚高原的苦战、囚禁俘虏的“苦难营”,一切都变得历历在目,作者不免心生感慨。他在调查手记最后一页写道:“回到日沃讷的夜晚,美丽晴朗的月夜让我产生幻觉。仿佛所有的死者都从无边的墓地中苏醒过来。”(Zola ?, Baguley D. La Déb?cle)从色当返回巴黎后,左拉花了近三个月时间整理历史文献,构思小说情节。一八九一年七月十八日,这位严谨的作家终于动笔,开始《崩溃》(La Déb?cle)的写作。

普法战争之前,创作一部战争题材小说的想法已萦绕在左拉心头。一八六九年,作家致信出版商阿尔伯特·拉克鲁瓦(Albert Lacroix)详述《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初步写作计划。他写道:“我十分希望让读者看到真正的战场,没有沙文主义,让人们了解士兵真实的痛苦。这个系列必须有一本军事小说。”(Zola ?. Les Rougon-Macquart.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vol V. LArgent, La Déb?cle, Le Docteur Pascal, éd. Henri Mitterand, Paris, ?ditions Fasquelle et Gallimard, 1967)起初,作者将思绪集中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和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1859),这两场战争是少年左拉对战争认识的启蒙。在《给尼侬的新故事》里,作者痛斥“战争,可耻的战争,该死的战争”。他回忆起军团穿过南部小城艾克斯,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克里米亚战场的画面,然而,当战事结束,原本应该凯旋的士兵“一瘸一拐,浑身是血,步履艰难地在路上前进着”(Zola ?. ?uvres complètes: Contes et nouvelles. Tome neuvième, éd. Henri Mitterand, 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 1968)。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真实遭遇也许从此刻起就已经令十四岁的左拉难以释怀。这位作家从未沉湎于胜利者的荣耀,他的目光从一开始便审视着战争罪恶的一面。处女作《给尼侬的故事》的第六则故事《血》如同《崩溃》的遥远先声: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四位打了胜仗的士兵梦到人类的第一次谋杀,即该隐杀害自己的兄弟亚伯,人类相互屠戮的血腥欲望由此开启,战场流淌的鲜血注满山谷,甚至要涌向世界。《崩溃》延续了《血》的结尾—士兵掩埋武器,离开战场,决心重拾犁铧,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
阿尔芒·拉努(Armand Lanoux)指出,《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第十九部是属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拿破仑一世远征俄罗斯为题材铸成不朽杰作,左拉受其启发,将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倒台、巴黎公社等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崩溃》(阿尔芒·拉努《左拉》,马忠林、孙德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八七○年战争将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引向覆灭,拿破仑家族的衰亡为《卢贡-马卡尔家族》提供了一个“恐怖又必然的结局”, 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左拉在《卢贡家族的发迹》序言里表明:“从现在起,我的作品是完整的了;它在一个有限的循环中摇摆;它成为一个业已衰亡的王朝的画卷,一个疯狂又羞耻的奇特时代的写照。”(Zola ?. La fortune des Rougon, Par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 A. Lacroix, Verboeckoven et Cie, 1871)左拉偏爱结构的对称性,他以色当战役为核心,将小说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各八个章节,分别讲述沙隆第七军在战斗前、战斗当天以及战败后的境况。小说开篇军队扎营的画面与爱德华·德塔耶(?douard Detaille)的油画《梦想》遥相呼应:“野营扎在距牟罗兹两公里、面临莱茵河的一片肥沃的平原中间。八月的一个黄昏,太阳已经下山,阴沉沉的天空,浓云密布,下面有无数营帐排列成行,步枪顺着警戒线一堆堆地支架着,间隔均匀,闪闪发光。”(《崩潰》,华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德塔耶画中的将士梦到曾经战无不胜的先辈,梦想着为一八七○年的耻辱复仇;而左拉笔下的士兵对一切尚未觉察,正怀着“打到柏林去”的豪情走向必然的败局。如果说《血》旨在揭示战争残忍血腥的一面,《崩溃》则更进一步,为战争赋予“进化论”的含义:战争即大自然循环更迭的法则。拿破仑三世宣告帝国成立时已埋下法兰西民族堕落的种子,因此,一八七○年,将士们在战场洒下的热血既是牺牲,也是赎罪,等到偿清过去的罪孽,一个全新的民族将从废墟中浴血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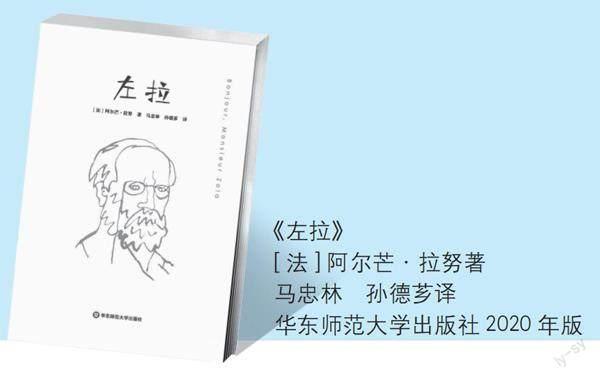
反英雄史诗
批评家埃米尔·法盖(?mile Faguet)称赞《崩溃》是左拉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堪称一部“散文体史诗”(?mile Faguet, M. ?mile Zola : La Déb?cle, Revue Bleue, Tome XLIX, Paris : Bureau des revues, 1892)。作家选取了英雄史诗的经典主题—战争,整部作品也具有大量史诗的特点。左拉将故事置于英雄史诗偏爱的宿命论之下,溃败的宿命朝色当袭来,命运之神通过主人公默里斯(Maurice)透露着军队即将面临的遭遇。威斯(Weiss)、戴拉欧舒(Delaherche)两个次要人物也承担着“预言家”的角色,小说第一章便着墨于威斯对德法两军实力的分析:德军将领英明,士兵严守军纪,军备优越;相反,法国军制腐败,武器落后,将军平庸无能,整个根基已经腐朽,士兵们跟被骗到屠宰场的牛羊没有分别。此外,左拉还不时勾勒出荷马式的画面,甚至重现《伊利亚特》中哭泣的战马:大战过后,出身非洲猎兵的普罗斯柏(Prosper)怀念心爱的战马“赛飞儿”(Zéphir),他在冲锋时跌下马,“它那空虚无光的大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我……说也奇怪,也许有人不相信我:的的确确从它的眼睛里流出了大颗的泪珠……我那可怜的赛飞儿啊,它曾像一个人似的恸哭过……”(《崩溃》)这一场景酷似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e)的战马在哀悼死去的主人,“埃阿科斯的后裔的战马这时站在/远离战涡的地方哭泣,当它们看见/自己的御者被赫克托尔打倒在尘埃里……它们也这样静默地站在精美的战车前/把头低垂到地面,热泪涌出眼眶/滴到地上,悲悼自己的御者的不幸”(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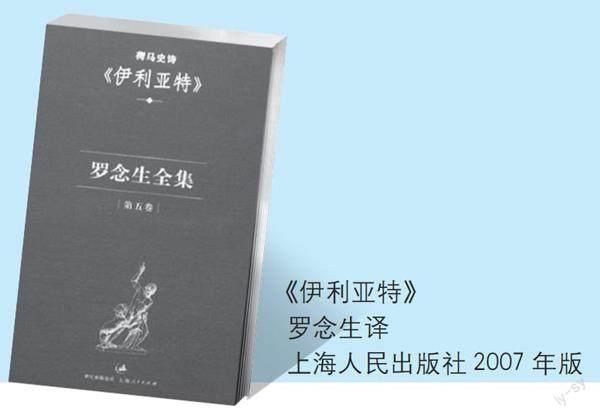
叙述者的声音因连续的重复、夸张的语气以及情感的直接表露带上史诗的语调,这一特征在默里斯回忆祖父讲述拿破仑一世的辉煌战绩时尤为明显。匿名的叙述者将话语权交给将孙子孙女抱在膝头的祖父,这位拿破仑“大军团”的老兵担任元叙述层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开头宛若行吟诗人的吟唱:“这些故事讲起来,先后的时间很难分清,仿佛是历史以外的事,发生在各民族可怕的冲突之间。英国人、奥国人、普鲁士人甚至俄国人,不管怎样缔结联盟,都一个接着一个或一下子一齐败走了。”拿破仑的赫赫战绩在整齐划一的排比句里渐次罗列,对这位伟大将领的赞美和崇拜也逐渐加深,“英勇和天才的攻击”,“拿破仑荣耀的太阳照亮了冬季的浓雾”,“预料到一切的神明的拿破仑”,“这是全知全能的皇帝的战略杰作”,“法兰西昔日的军事荣光令人沉醉”。(《崩溃》)讽刺的是,当默里斯的思绪回到现实,恰好听到第一军团对阵普鲁士的败绩,作为侄子的拿破仑三世没能继续叔父战无不胜的传奇。
为了方便向公众演述,古希腊英雄叙事诗的人物性格大多較为单一,左拉延续了这一特点,因而《崩溃》中众多人物的性格趋于扁平化。评论界对此多有指摘,让·饶勒斯(Jean Jaurès)认为小说的人物过于简化,每个人物代表“一种缺点或优点,就像中世纪的道德剧”。在《崩溃》英译本的序言中,左拉明确表示对人物性格的标签化设置是有意为之,“我想反思当时在法国人们的精神状态”,“《崩溃》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叙述细致、精准,可以说具有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特点,因此它能够成为一八七○年法兰西心理学档案。这便是为何作品里有那么多人物。每一个人物都代表着当时法国人的某种精神状态”(Zola ?, Baguley D. La Déb?cle)。换言之,左拉想要刻画的不是独立的、个性化的人物,而是一个又一个人物类型。因此,人物的出场常常伴随着固定的标签式表达。例如,拿破仑三世自始至终都以优柔寡断、沉疴多病的形象示人,“脸色苍白”“无用的累赘包裹”“悲惨的皇帝”“可怜的人”成为这位皇帝的标记。绣满蜜蜂的华服和气派的随从也反复出现,与士兵的落魄及皇帝本人的病态构成双重讽刺,第二帝国的命运和这位皇帝的遭遇如出一辙,战火之下大厦将倾。
如果说《崩溃》是一部史诗,那么它是一部反英雄的、属于战败者的史诗,悲惨的沙隆军团是这出悲剧的真正主角。让·坎普费尔(Jean Kaempfer)将战争叙事作品分为“古典”和“现代”两大类型。古典战争叙事作品通常采用外视角,即历史学家和参谋部的视野,将战事明确地呈现给读者,它们偏爱理性的“帝王书写”,因为“战事的智慧不在于那些浴血战斗的无足轻重的尘埃,而在于事先下命令的将领的头脑”。(Jean Kaempfer, Poétique du récit de guerre, Paris: José Corti, 1998)古典叙事中,普通士兵往往满腔热血,英勇杀敌,但他们的牺牲却无关紧要,甚至被视为将领英勇御敌的佐证。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首开现代战争叙事先河,坎普费尔指出,尽管现代战争叙事作品没有共同的书写范式,但在《帕尔马修道院》之后,战争叙事不再像史诗那样表达愉悦,反而转向揭示焦虑不安的状态。普通士兵取代高高在上的将领成为故事的主角,叙述视角转向人物的内视角,即士兵即时的个性化表达,理智、明晰的英雄传奇让位于一个混乱、荒诞、失去人性的世界,对军功的颂扬在现代战争叙事中成为不可能。就此而言,左拉对战争的书写无疑位于现代战争叙事作品之列。戴维·巴古雷(David Baguley)进一步指出,《崩溃》常常对史诗有所颠覆,“不是因为塞万提斯式的滑稽,而是因为它通过无数细节与英雄视角进行对抗”(Zola ?, Baguley D. La Déb?cle),对普通士兵视角的侧重是《崩溃》与英雄史诗的本质区别。
左拉竭力与史诗构建的战争神话保持距离,他坚持文本的真实性,从生理学视角观察战争,没有对战场的丑恶与残忍做任何掩饰。色当战役前后,“肚子问题”一直折磨着法国军队,当所有人被困在伊里半岛成为俘虏,人的兽性终于占据上风,士兵们在饥饿之下捕杀战马,撕扯马肉的场面与恶狼用獠牙撕碎猎物别无二致,同样的杀戮在抢夺战友的食物时再次上演,毫无袍泽之情可言。战场之外,伤兵医院成为炮火无情的投影,救治无效的伤兵被埋在金雀花后的墓穴里,“在尸体脚下,紊乱地堆着割断的胳膊和大腿,以及一切从手术桌上切下和截断的残余物,这很像肉铺老板用扫帚扫了一下,把无用的碎骨和残肉推到一个角落里来”,这是屠宰场的碎片,“杀戮的第二天的凄惨的残渣,显现在阴郁的曙光之下”。(《崩溃》)停战翌日,茜尔芬(Silvine)和普罗斯柏前往伊里高原寻找奥诺莱(Honoré)的遗体是全文对色当战场最后的直接描写,沿途的村庄只剩下被火焰熏黑的残垣断壁,垃圾车清理着遍地死尸,广袤的平原尸横遍野,士兵们还保持着生前战斗的姿势,森林被炸出豁口,树木流出的浆液哭泣着人类战场的惨痛。
不协和的尾音
色当战役的余温在小说第三部分渐渐进入尾声,作者笔锋陡转,将全书最后两章留给一八七一年的内战—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与凡尔赛军的对抗。对公社的描写如同一段不协和音,《崩溃》因此饱受争议。埃米尔·法盖认为这是小说唯一令人迟疑之处,它与前文缺乏必要的衔接,就像“来自其他国家、其他星球的叙述,将永远被当作题外话”。左拉描写巴黎公社的意图也令人疑惑,“他是把公社作为战争最后的结果了吗?还是把它看成帝國的最终结果?这位在一八六五年已经二十五岁的男子汉难道曾天真地相信过帝国的腐败?”(Zola ?, Baguley D. La Déb?cle)《崩溃》出版两天后,艺术评论家古斯塔夫·杰夫洛瓦(Gustave Geoffroy)在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高卢人报》上援引默里斯离开雷米利之前和让(Jean)拥抱亲吻的场景,他认为“作家本该停笔于此,不必加上最后的意外事件、对公社的简短描写以及两兄弟在街垒战中的兵戎相见”;莫莱尔将军(général Morel)不满左拉将一群无耻之徒称为“公社的战士”,左派评论家则更多反对作者对公社的批判,因为《崩溃》直接道出公社承诺的社会改革“一项都不能实现”,“半点持久的事业都不会留下”,作为公社社员的默里斯也不禁思忖:“公社无能,反对分子太多,把公社都拖垮了。” (《崩溃》)
普鲁士对这场内战作壁上观,公社带着“截取烂肉的切刀”和“烧尽垃圾的大火”成为针对凡尔赛军的复仇者,默里斯倒在让的刺刀之下,公社和凡尔赛的对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兄弟相残?熊熊燃烧的大火是公社最后的报复,巴黎如同遭受天罚的“罪恶之城”索多玛,在滔天的烈焰中沦为地狱,这是《崩溃》的最终结局,“是最后不可避免的一幕,是在色当和麦茨的失败战场上发育起来的流血狂,是由巴黎被围而产生的破坏的传染病,这是一个面临生死关头的民族在屠杀和崩溃路上的最高峰”(《崩溃》)。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左拉认为战争带来的毁灭固然残酷,却是民族更新必不可少的自然法则。帝国在罪恶中诞生,因此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巴黎因长期累积的罪恶和淫佚遭受火罚,日耳曼人前来扫除拉丁民族腐化的最后尘污。作者将对真实历史的评论功能交给默里斯,陷入谵妄的主人公喃喃自语:“用血洗一下澡是必要的,而且在这炼净罪恶的大火中要有法国人—可憎的祭品,活的牺牲的血。从此走向最可怕的临终的痛苦路程,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民族在赎完了罪之后,就可以新生了。”(《崩溃》)《崩溃》将民族新生的希望托付于勤劳务实的农民让·马卡尔,然而,饶勒斯指出,正是由于农民狭隘的利益算计对帝国的暴政保持宽容,才加速了此前民族的衰亡,左拉给出的民族得救之路让人难以信服。

左拉(?mile Zola,1840-1902)
布朗热(Boulanger)掀起的民族沙文主义在一八九二年余温尚存,二十多年过去,色当依旧是一道没有愈合的创伤,重现一八七○年惨败的《崩溃》一经付梓即遭到爱国主义者的猛烈批判。亨利·荣格将军(Henri Jung)认为这部小说侮辱了民族自尊心,因为法兰西所经历的苦难根本不是一个适于自然主义的主题;莫莱尔将军则直言贬低战败者以颂扬战胜者根本算不上爱国,左拉的目光只局限于色当战役和法国的投降,对法军在战事其他阶段的英勇顽抗一直保持缄默,作家本可以用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来鼓舞人心,最后却写出来一本骇人听闻、伤风败俗的小说。克里斯汀·弗兰克更是撰写了一本长达九十一页的小册子,题为《请重写〈崩溃〉》,他指出,左拉作为“史诗诗人”,丝毫没有赞美法兰西的英雄主义,也忽视了法国人的反抗精神,《崩溃》既不讲究真实和公平,也缺乏爱国主义热情,“左拉先生,请重写或者完善您的《崩溃》”(Christian Franc, ? refaire La Déb?cle, Paris: Dentu,1892)。与此同时,《崩溃》也激起德国读者的讨伐之声,作家、哲学家弗里茨·毛特纳(Fritz Mauthner)批评这部小说情节巧合太多,而且对德国军队充满偏见,仿佛德军是以十当一,胜之不武;亲历战争的巴伐利亚军官塔内拉(Tanera)九月十九日在《费加罗报》上以《一位德国军官眼中的〈崩溃〉》公开致信,希望左拉对小说的不公正及细节失实予以回应。彼时作家已前往法国南部为即将动笔的《帕斯卡尔医生》和《卢尔德》收集资料,在他十月七日返回巴黎时,梅塘家中的信箱已被读者来信占满。
欠缺公正的反对意见将左拉气得跳脚,待思绪冷静下来,作家于一八九二年十月十日在《费加罗报》发表《旅行返程》一文对部分批评做出回应。左拉表明,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小说家有权根据创作需要选择自己认可的部分,并且作家有进行虚构的权利,因此,对于类似“皇帝是否化妆”的细节指控他拒不苟同。针对爱国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军官的来信,左拉强调《崩溃》没有歪曲或夸张,只是客观陈述一八七○年的事实,巴伐利亚军队确实曾在巴赛叶屠杀平民,法国士兵也的确在溃败时丢盔弃甲,德国以优越的兵力和军备打赢了补给不足的法国军队,这些都是法兰西经历的真实苦难。承认敌军的优势与我军的劣势并非不爱国,而是为了从旧时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巴伐利亚军官称赞法军强大的谎言只会将法兰西引入更深重的灾难,“我们需要承认错误并付出代价,对过去做出忏悔,才能在将来的胜利中使我们的自尊心和希望免于灾祸”。这位作家敏锐地察觉到,法兰西仍然迷信英雄战斗传奇,哪怕面对一场毋庸置疑的溃败,人们也只愿看到法国睿智的一面、将士们伟大的献身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的狂热,然而,辞藻华丽却虚假作伪的英雄传奇正是民族衰亡的根源之一。正因如此,《崩溃》有道出战争之恐怖的必要,作者希望展现“一个像我们这样战功累累的民族,是如何被惨痛击败,这二十年间是从怎样的牢笼中重新站起,这个强大的民族又是经历了何等的血浴才获得重生”。况且,对民族溃败的真实记忆、对士兵惨死的悲悯、对法兰西命运的担忧,又何尝不是出于拳拳爱国之心呢?
尽管评论界褒贬不一,这部献给战败者的史诗甫一出版即大获成功,仅在一八九二年便重印九次,当年在法国的销量达到十七万六千册,欧洲各国的出版社也纷纷争取译本的出版权,在俄国甚至出现了十余种盗版译本。左拉借《崩溃》开辟出一种新的战争小说模式,他是第一个“以生理学理论来观察战争的作家”,从而创作出与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截然不同的著作。(阿尔芒·拉努《左拉》)然而,《崩溃》也预示着左拉自然主义创作的尾声,它以反英雄的视角将“第二帝国一个家族的社会史”引向终篇,通过小人物之口传递出作者对法兰西民族命运的反思,这从侧面证明作家已有意参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大辩论。在这部承前启后的战争小说之后,左拉创作的《三名城》与《四福音书》甚至可以直接纳入“介入小说”(roman engagé)之列。或许正是这种悄然生长的“介入”意识,让功成名就的左拉在一八九八年愤然而起,化身“德雷福斯事件”中为正义呐喊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