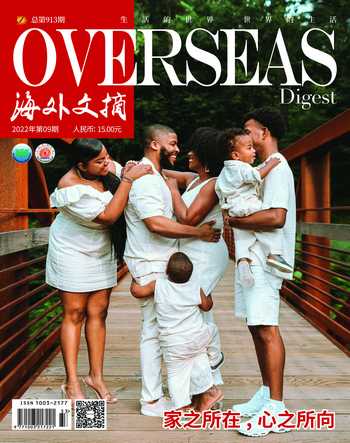家人待租
艾莉夫·巴图曼

家庭租赁服务公司的负责人称,这类服务是“ 借用家庭的形式来表达人类的情感”。
| 假女儿找回了真女儿 |
两年前,60来岁的工薪族西田一成租了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彼时,他妻子刚刚离世,他22岁的女儿也因为一场争执跟他断绝了往来。
我和西田在2月的一个晚上见面,他个子挺高,有点驼背,穿着西装,打着灰色领带,在一家公司的销售部上班。“我本以为自己蛮坚强的,”他说,“但真一个人了,还是非常孤独。”我对他的印象是声音低沉,为人谦和。
母女二人从西田的生活中消失以后,他和往常一样,每天都要上班,得空了会跟朋友喝几杯或者打高尔夫,但到了夜里,他还是要独自一人回到家中。他一开始觉得自己过一段时间就会适应,但事实恰好相反,他越来越难受了。
后来,他想到了自己之前看过的一则电视广告,打广告的是一家叫“家庭罗曼司”的公司,日本有一类公司专门提供家庭租赁服务,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广告中,一位年长的女客户热情地说起了“孙子”陪她逛街的经历。“孙子虽说是租来的,但她的快乐是真的。”西田回忆道。
西田联系“家庭罗曼司”,下了一个订单,他要租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共进晚餐。他还在订单上备注了女儿的年龄以及妻子的体型。价格算下来是4万日元。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小餐馆,按他的说法,租来的女儿比他的女儿看上去要时髦一些,租来的妻子看上去倒是“普通的中年家庭妇女形象”。“她不像松基女士。”他将目光转向了我的翻译松基智惠,“松基女士这样的人一看就是职场人士。”松基留一头干练的花白短发,戴一副塑料边框眼镜,她笑着将这段话翻译给我。
西田详细跟她们讲了讲妻子和女儿的特点,比如妻子甩头发的动作,再比如他女儿有时候会戳他的肋骨逗他开心。讲解完毕,她们就进入角色了,他妻子怎么称呼他,租来的妻子就怎么称呼他。其间,她也会像他妻子一样用甩头发的方式整理头发。租来的女儿则活泼地戳了几次他的肋骨。任谁从旁边经过,都会觉得这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西田随后不久就下了第二笔订单,这一次地点定在他家。“妻子”在厨房做薄煎饼,他在客厅和“女儿”聊天。饭做好以后,他们一起吃饭和看电视。
这之后,他们又一起吃了好几顿饭,大多是在西田家中,其中也有一次例外,他们一起下馆子,但吃的还是西田太太生前爱吃的薄煎饼。西田一开始也在想,是不是应该带她们去更上档次的馆子,毕竟她们是客人。不过,他转念一想,西田一家平日里下馆子确实不会去更好的地方了。
再后来,他给“家庭罗曼司”提供了一把家里的备用钥匙。按他的要求,那一次的家庭聚会是这样展开的:他晚上下班回家,一到家,面对的就是明亮温暖的房间,“妻子”和“女儿”在门口跟他亲切地道了句“欢迎回家”。
“这种体验非常温馨。”西田微笑着回忆起那次经历。她们每次离开,西田并不会有特别的不舍,也不会有立马要和她们再次见面的冲动,但他确实会想到:“下次要是能跟她们再这样聚聚也不错。”
西田用自己妻子和女儿的名字称呼她们,他们见面的形式也是一家人一起吃饭,但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她們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停止表演,显现出真实的自我。租来的妻子有时候会跳出角色,抱怨自己真实的丈夫,西田则会给出建议。大家的状态松弛下来以后,西田发现自己其实也在扮演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他逐渐在她们面前放下戒备,谈起了自己的女儿。她当时要和男朋友同居,而西田从没见过那个男人,父女二人因为此事大吵特吵,断绝了往来。
西田租来的女儿20来岁,谈到这一话题,她说西田并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跟女儿交流,也没有用恰当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把话说到那份上,他女儿很难主动道歉,他要想办法首先打破僵局才成。“你的宝贝女儿在等你的电话呢。”她告诉西田。“虽说她在演我的女儿,但与此同时,她确实在跟我讲她作为女儿的真切感受。”西田说,“不过,我们如果真是父女关系,她大概不会这么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多亏了“女儿”的这番话,西田最终拨通了电话。他试了好几次,女儿才接电话,但他们至少说话了。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妻子的灵位前摆着一束鲜花,这说明女儿白天肯定来过。“我希望她回家,我每次打电话都这么说。”西田小心翼翼地说,“我希望我可以尽快见到她。”
|“家庭罗曼司”的创办史 |
“家庭罗曼司”的创始人石井佑一说,公司创立的理想是,租来的家人最后会成为客户生活中多余的存在。石井的终极目标是“让这个社会不再有人需要我们的服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一场电视采访。他30多岁,面容英俊。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有一张他的卡通头像,下面印着一句标语,翻译过来是“我们提供的快乐比现实提供的要多”。
东京出生的石井在千叶海岸长大,父亲是水果商,母亲是游泳教练。他上小学的时候,喜欢模仿成人的声音打恶作剧电话,他的同学会围在旁边听,他的厉害之处就是可以忍住不笑。20岁的时候,石井开始当模特和群演,同时还在好几家养老院兼职做护理员。他给我看了几张当年养老院的照片,老人们围着他,面露笑容。他喜欢帮助别人的感觉。他是那几家养老院最受欢迎的护理员,这让他备感骄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那会儿扮演的就是那些老人的孙子。
租来的家人最后会成为客户生活中多余的存在。
11年前,石井的一位朋友说她想送女儿进一所幼儿园,但她是单亲妈妈,而学校对离异家庭的小孩有偏见。石井主动请缨,扮演孩子的父亲参加幼儿园面试。他们配合得非常生硬,面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经历让他萌发了继续做下去的想法。用他的话讲,他想要“纠正不公”,帮助那些和他朋友有类似处境的女性。他想看看有没有公司提供这种服务,最后找到了“请振作起来”,这是一家专门提供家庭租赁服务的公司。
2006年,市川柳一创办了“请振作起来”。2001年,大阪郊区一所小学发生了恶性持刀伤人事件,八名小孩遇害,他们的年龄跟他儿子相近。这起事件给市川留下了不小的阴影。这种事在日本极为罕见,当时的学校也没有条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受这件事影响,市川报名了心理课程,打算之后到学校当心理咨询师。不过,他最后并没有到学校工作,而是搭建了一个网站,用电子邮件的形式给别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之后,他的网站衍生出了家庭租赁服务,他发现很多问题似乎都是因为缺了某个人,而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往往就是找一位替代者。
石井和“请振作起来”签约的时候26岁,公司负责人认为他太过年轻,不适合扮演丈夫和父亲之类的角色,他唯一能扮演的就是婚礼宾客。婚礼是家庭租赁行业谋生的主要手段,这或许是因为城市化、人口流动、小家庭、工作不稳定等趋势尚未改变日本传统文化对婚礼宾客人数的要求。丢了工作的新郎会请人扮演同事和上司;上学期间经常转学的人会请人在婚礼上扮演儿时玩伴;刚订婚的情侣为了不让父母离异之类的烦心事打扰到另一半,会找人扮演自己的父母。公司的一位客户不希望未婚妻知道他父母离世了,为此专门请了两个人扮演他的父母。
2009年,石井成立“家庭羅曼司”。如今,公司有20位全职员工,公司数据库里储存着1200多位自由演员的信息。婚礼这样的一次性大单贡献了公司七成的收入,余下的收入来自长期的合作关系,像西田这样的客户,双方的合作关系可以长达数年之久。
2009年以来,石井总共扮演过100位女性的丈夫。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他最多同时扮演过十个家庭角色,如此大的工作量自然不可持续。他说:“我会觉得肩上仿佛扛着别人的人生。”于是,他定了一条规矩:演员最多只能同时扮演五个角色。
这份工作的风险在于客户会对演员形成依赖心理。石井说,有三四成女性最后会向租来的丈夫求婚。男性客户产生依赖心理的概率要低得多,因为出于安全考虑,租来的妻子一般不会到他们家里去。西田租来的妻子同意去他家中,主要是因为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位租来的女儿。
单亲妈妈的依赖心理最为棘手。“我们不可能直接将她们推到一旁,冷冰冰地说:‘不,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有长期扮演她们伴侣的职责。”石井说。这种情况下,他首先会将双方见面的频率降低到每三个月一次。这种方法对部分人有效,但对部分人并不好用,她们还是会执意要多见。这种时候,公司只能终止合作。
| 宗族·核心家庭·单身家庭 |
1868年,明治维新拉开序幕,日本逐步从过去的封建国家转型为现代化强国。改革者制定了新的《民法典》,对“家庭”的概念进行了规范。过去,日本并不存在这一概念,也没有任何词语可以表达“家庭”的意思。为此,改革者造了个新词来代表“家庭系统”,这一系统是基于日本长期的宗族观念建立起来的。宗族观念等级森严,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儒家思想。族长控制着宗族的所有资产,他会从年轻一代中挑选一个继承人,一般来说都是他的长子,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他的女婿甚至养子。宗族的延续比血缘更为重要。余下的宗族成员可以选择留在宗族内部,除此之外,女孩可以通过婚姻的方式嫁入别的宗族,男孩则可以开辟自己的“分家”。民族主义者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一个大家族,天皇是族长,余下的都是“分家”。因此,日本的国家认同非常讲究“家庭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大相径庭。
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日本期间起草了新宪法,内容之一就是用西方的核心家庭观念取代日本的宗族观念。依照新的法规,包办婚姻违法,妻子在法律上和丈夫平等,家庭财产也要平均分给孩子,不论性别和出生顺序。日本经济在战后快速发展,企业文化也随之兴起,宗族逐步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住公寓的核心家庭,一般由一位工薪族丈夫、一位家庭主妇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繁荣期,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上班族。出生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和单身家庭增加成为了日本的新趋势。与此同时,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也在增长,老年人的比重逐年上升。
也正是在80年代,日本兴起了首波家庭租赁的热潮。1989年,大岩札木开始向老年人提供租赁子女和子孙的服务。大岩是东京一家公司的老总,专门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服务。她培训的时候,总有员工抱怨说没时间看望父母,这些抱怨声让她嗅到了商机。短短几年时间,她就为上百位客户提供了租赁亲属的服务。有一位父亲特地租了个儿子去听他讲过去的苦日子,他的亲生儿子跟他住在一起,但就是不愿意听他提这些陈年往事。此外,他和妻子很怀念抚摸婴儿皮肤的感觉,而他们的孙子早已过了这个年龄段,他们为此又多租了一位儿媳妇和一位婴儿。租来的儿子儿媳以及孙子总共在他们家待了三小时,费用是1100美元。每位客户的需求都略有区别。有一对年轻夫妇特意为他们的孩子租了爷爷奶奶,还有个单身男子专门租了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好体验一下电视上看到的核心家庭生活。
90年代,日本撤销了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打那时起,工薪阶层的生活方式就受到了侵蚀。如今,日本38%的劳动力打零工。许多日本媒体称,家庭租赁服务是赚外快的有效方式。2010年,单身家庭的数量首次超过了核心家庭。眼下,日本年轻人和国外年轻人一样,有更多自由流动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但他们在安全感、社群归属感以及家庭归属感上是有缺失的。与此同时,日本老年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一部2008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讲述了一位老年女性任由一位年轻人欺骗她的故事,她愿意这么做,都是因为他让她想起了死去的儿子。
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可以用真切的个人感受和传统的社会期待来解释,家庭租赁现象也不例外。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将传统的社会期待放在自己的真切感受之上,别人并不会觉得他虚伪或者在骗人,而会觉得他无私,懂人情世故。前文提到有一位男士为了掩盖父母离世的真相,特意租了两人在婚礼当天扮演父母。他后来将真相讲给了妻子。她不仅没责怪他,还说她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样做不是有意要骗她,而是为了避免在婚礼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她觉得丈夫考虑得很周到。
毫无疑问,日本的家庭租赁现象从许多角度来讲都是日本独有的。话虽如此,人类历史上却不乏花钱聘请陌生人扮演亲属的例子,古希腊、古罗马都有花钱请人哭丧的传统。时至今日,印度还在延续这样的传统。2013年以来,英国也有了这样的服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姆、护士和厨师不也是租来的亲属吗?他们承担的难道不是过往母亲、女儿、妻子承担的部分职能吗?
| 女性为爱付出的巨大代价 |
家庭意味着“无法用金钱买来的爱”,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其实比较新鲜。前工业化时代,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每个新生儿都相当于一个新生的劳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开始出去工作,赚薪水,家里每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张吃饭的嘴。换言之,世界成为了市场主导的世界以后,家庭才成為了提供无条件爱的避风港。
1898年,女权主义者夏洛特·吉尔曼将“浪漫爱情”和“母性牺牲”称作“意识形态的建构”,是让女性留在家中的诱饵。年轻女性从小到大接触的就是“浪漫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她们会花心思打扮自己,吸引意中人。她们虽然毫无准备,但结婚以后,未言明的社会契约会让她们变成没薪水的全职护士、老师和清洁工,而驱动她们这么做的就是神秘的“母性本能”。
人类学家岳山秋子认为,日本于19世纪末引入了类似的“浪漫爱情意识形态”——一位女性理想的路径是浪漫爱情、结婚生子和母爱觉醒。她还指出,很多已婚妇女如今去牛郎店一掷千金,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再次体验浪漫爱情。她们成为丈夫口中的“孩子妈”以后,浪漫在家中就不复存在了。
换个角度想,将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职责看作无价浪漫爱情的外化,或许比租伴侣、父母、孩子更奇怪。父权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鼓吹浪漫爱情,主要是因为这种观念对它有利。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赖希指出,有女性免费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资本家就可以少给男性付一些薪水。吉尔曼认为,要破解女性的困局,就应该衍生出新的职业,负责家务、照看小孩、做饭等工作,男女都可以做。不过,这么多年过去,这些职责并没有衍生出受人尊敬以及有体面收入的职业,相反,这些职责被塞给了处于经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而条件好的女性则可以追求事业。
| 九年的“父亲”|
石井说他想纠正不公,他的想法与吉尔曼不谋而合。正如吉尔曼所写:“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不论是未婚男子、丈夫、寡妇、女儿、妻子还是鳏夫。”多亏了“家庭罗曼司”,西田这样失去家庭的人才能感受到久违的家庭温馨。
九年前,牙医助手玲子联系了“家庭罗曼司”,她是单亲妈妈,十岁的女儿曲真因为从小见不到父亲有些自闭。她为了打开女儿的心扉,希望租一位父亲。九年间,石井一直在扮演曲真的父亲,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见一次,曲真确实比过去开朗了不少。不过,她眼看就要20岁了。石井跟玲子提过,他们应该停止见面。“曲真一旦结婚生子,我就要扮演外公,外孙外孙女固然很好,但这也意味着我要跟更多的人撒谎,更别说她的丈夫和姻亲了。”他说,“我和玲子明确说过,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她需要将真相讲出来。”
石井真心觉得曲真会理解这一切。我觉得他的话有几分道理,曲真母亲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石井也在尽其所能地给她提供温暖。不错,他每小时要收50美元,但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你即使给他们再多的钱,他们也无法提供陪伴和温暖。石井的善意总不能因为收了钱就变得毫无意义吧?
石井有时会梦到曲真,他在梦中说自己并不是她的父亲。“她在我的梦里坦然接受了这一切,”他说,“但她紧接着告诉我:‘尽管如此,你还是我父亲。”
“你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也算她的父亲?”我问。
石井闭上了眼睛,看上去有些疲惫。他说:“我们并非真实的一家人,我只不过是她租来的父亲,不过,我们相处的方式确实让我们成为了某种形式的家人。”
[编译自美国《纽约客》]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