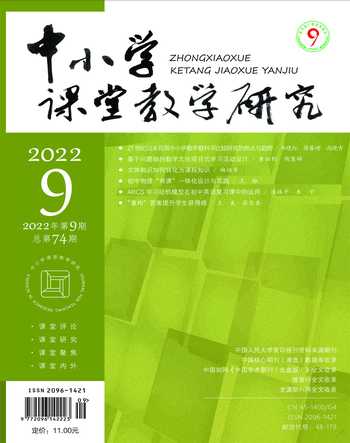文体知识如何转化为课程知识

【摘 要】文体作为文本特有的话语体式,在阅读教学中需要转化为课程知识进行教学。充分挖掘文体学的本体知识,发挥其教学价值,实现文体性与教学性的有机统一,是培养学生文体感和文体素养的重要途径。以小说的三层级解读为例,教师可以在语象与语脉、结构技法与形象创造、跨体阅读与复调对话三个方面为学生提供小说释义、解码、评鉴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文体知识;课程知识;小说;释义;解码;评鉴
我国历来就有“体制为先”的传统文论。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提到,文章需要“因情立体”,也就是不同的情感需要通过不同的体制进行表达,并且“即体成势”,依据不同的文体表现出不同的文势。从写作的角度而言,作者需要“因情立体”;而从阅读的角度而言,读者需要“依体悟情”。特别是文学类文本,体制特征异常丰富,并且“文变殊术”,更有不少妙处可供教师讲解。然而在实际的阅读教学中,文体知识却没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转化,教师的讲解往往停留在明确文体知识的静态层面上,这就导致学生的文体素养过于薄弱。
一、作为话语体式的文体知识
文体作为文本特有的话语体式,是语言结构的存在体,也是重要的审美文化存在形式,这个语言结构存在体和审美文化的存在形式与文本的多个要素都互有关联。张毅认为,文学文体正是以特异的文化感知方式呈现生存本体及其运思过程[1]。陶东风则认为,文学文体作为话语体式必然会延伸至精神层面,这个话语活动就建构了一个深广的精神文化关联域[2]。两种说法都点明了文学文体不仅仅是形式或质料层面的简单分类,还意味着更深层面的审美文化内涵。文学文体大致有四个相关联的维度:第一个是语言学维度,这个维度主要呈现文本的形式结构特征,借助共时语言学的思想,通过文本内部的语体等形式结构特征来表征文体的审美文化存在;第二个是心理学维度,这个维度主要呈现作家及其群体文化心理特征,关联作品的个体风格、流派风格、时代风格等,比如中国古代诗歌的作家风格、流派风格,德国以施皮策为代表的心理文体学等;第三个是接受美学维度,文体展现出创造者想要呈现的形式的同时,也暗含着接受者所理解的形式,因此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文体有含混的属性;第四个是文化学维度,文体是文学以特有结构独立存在的文化形式,因此文體的产生与演变必然包含着文化的意味,展示着时代精神文化的风貌,影响着文学时代风格的形成。
即便文体在文学理论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许多教师对深厚的文学文体理论资源却视而不见,仍长期停留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教学文体的运用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文体的简单分类上。虽然语文教育界普遍重视语感的培养,但是潘新和认为,“文体感”比语感更重要[3]。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文体与语言的话语体式相关联,“文体感”的培养就是语感培养的重要路径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体感”的培养自然比语感培养更“实在”。
二、文体知识转化为课程知识
传统意义上,课程知识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上课程知识与学科知识等同;另一个层面指教师应当具备的,与整个课程的实施过程相关的技能性知识。一个文本要进入语文教材,必然要依据课程标准的意图进行转化,要经过课程专家、编者对文本体现的学科知识进行选择和编制,最终才会成为“课程文本”。“课程文本”具有课程教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教师认真思考一个文学类文本进入课程语境后所承载或呈现的课程知识。这是因为文学文本一般具有丰厚的文学价值、多样的美学意境,也承载着大量的语言学、文章学知识,甚至还附带其他非语文学科的知识要素,但并不是所有知识都要进入课程并传授给学生。因此,教师要钻研文本进入课程后的教学价值,合理选取并综合运用文学、文章学、语言学等理论解读本文所含知识,再运用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等知识促使学生在文本解读中将文本的本体知识转化为文本解读素养和语言运用能力。此处学生在文本解读中接触到的综合知识结构体即文本解读的课程知识。
文体知识是语文课程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从文学层面来说,文体是文学类文本的体裁分类;从文章学层面来说,文体是对文章体式的分类和辨识;从课程与教学层面来说,学习上述学科本体的文体知识并加以重构,形成的便是文体课程知识。以小说的文体知识为例,小说的“三要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体现小说特性的知识历来被当作小说重要的文体课程知识。但是小说文体具有未完成性和杂糅性,因此以往归纳出的小说文体知识不一定能充分解读新时代的小说。比如在教学《变形记》《墙上的斑点》等现代派小说时,如果还是依靠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小说的阅读经验,自然难以解读新小说。此时就不得不吸纳更多小说理论进行补充,如西方叙事学理论中关于叙事者、叙述视角等分析方法就可以适当选择并转化为小说文体的课程知识进行教学。将文体知识转化为课程知识,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文体素养。文体素养由文体意识和文体能力构成[4],是阅读或写作时主体对文本话语体式的自觉观照。文体意识主要表现为创作者在创作时对文本的建构有明确的文体意向,或是阅读者在阅读时对文本形式的感知有适切的预测和意向。文体能力则是将这些意向转化为现实话语结构的能力,也就是将“胸中之竹”转变为“笔下之竹”的能力。对于创作者而言,文本的创作要么是依循已有的文体形式建构新文本,要么是对已有的文体进行形式上的创新,探索新的叙事策略。而对于阅读者而言,他们接受文体的能力也有再创造的可能,比如进行跨文体的阅读。从本质上来说,将文体知识转化为课程知识就是充分利用文体学的本体知识,尽可能地发挥文本在文体学上的教学价值,以此实现文体性与教学性的有机统一,促成学生文体感的生成和文体素养的培养。
三、三层级阅读培养文体素养
三层级阅读教学在教学中更强调为学生建构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层级阅读教学必然要关注文体阅读素养的培养。如图1“三层六级”阅读金字塔所示,下方作为基座的四级能力都与文体素养息息相关,最上端的两个高阶能力也需要以文体素养作为攀升的基础。
(一)释义层:语象与语脉
海德格尔认为,人在说话的同时“话”也在说人。所谓“话”说人,指的是以话语体式表征人的文化存在特性。因此可以说,话语体式是以语言学的方式表征文学,甚至表征主体的文化存在。指向话语体式的文体阅读,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充分挖掘这种体式特征,以此充分析出文本的语文要素,凸显文本的话语特点和体性特征。汲安庆在《语文阅读教学:必须正视的三大范畴》一文中就提出语文阅读教学应该充分关注文本的“体性”“类性”“篇性”三个重要范畴[5]。实际上,这三个范畴正是指向话语体式文体阅读的关键所在,辨体、分类、“掘篇”就是文体阅读的基本流程。辨体与分类是以较宏观或中观的视角对文本进行文体分析,这种分析较大程度上是运用文体学知识进行判别。判别时可以形成相应的文体阅读姿态并调动已有的文体知识为阅读文本做好准备,属于最基本的文体阅读。但是指向话语体式的文体阅读更多的是在基础阅读上进一步发掘文本的篇性特征。所谓文本的篇性特征,是文本文体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表现出该类文体的体性、类性,又呈现单一文本的话语体式,因为每个文本都会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式去表现它作为体和类的特征。以小说阅读为例,“三要素”仅仅是小说这一体和类的特性,仅用“三要素”进行教学,教学价值就十分有限。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探索“三要素”在小说中以何种话语体式建构(甚至可以适当联系叙事学相关内容),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不同文本如何处理“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张心科提出,小说教学离不开“三要素”,但教学的关键应该是“三要素”之间的关系[6]。“三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都体现为文本特有的篇性。从话语体式的文体阅读角度来看,教师可以从文本的语象和语脉两个特征入手揭示文本的篇性特征,实现基于文体的释义。
语象是每个文本特有的语言形象,指向单个文本的言语密码,而不是整个文体的语言形象。赵毅衡考证新批评学派“image”这一概念的运用和翻译后提到,“image”的概念比较复杂,既包含情境和人物形象等宏观的文学形象,也包含微观上细胞级的语言形象,同时还在意义之象和语言之象之间纠缠不清,因此他建议将“image”翻译为“语象”,这样能更好地体现新批评的原初内涵。[7]赵毅衡对“image”这一术语的辨正恰好揭示了隐含于新批评理论中的文体学要义:文体学的类别特征都是由具体的语象,也就是细胞级的语言形象来实现的。比如,鲁迅的小说就常常以模糊、含混的语象来表现人物或传达特别的信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就是此类。像这样含混的、悖反的語象在鲁迅的作品中多处可见,这就是他独特的话语体式。
过去的小说解读过分强调对情节的把握,往往忽略了语象的特征、话语的结构,使得文本特有的话语体式在教学中难以得到揭示。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很简单,关键词分析就是典型的语象分析法。文本中一个词语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面是语音层面,包含了言语节奏、音韵等方面的处理;第二面是词汇的选择,关键词对于文本文体的创造,以及建构文本特有的话语结构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大多数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建构方式,主要通过对词汇的选择来完成建构;第三面是文学文体中的词汇往往通过变异的方式彰显文体效应,相当于形式主义文论所说的“陌生化”审美效应或新批评所说的语言的内在张力效应。比如在《故乡》的教学中,许多教师可以抓住回忆中的故乡与现实所见故乡的反差,但是鲜有教师关注其中的语象。如果能在释义层抓住“呜呜的响”“冷风”“苍黄”以及与之形成反差对比的“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项带银圈”等关键语象,那么学生在解读这一文本时文体感就会被激活。
如果说对语象的分析对应的是言语的释义,那么对语脉的梳理就具有将释义推进到解码的价值。语脉这一概念源于文章学,顾名思义就是语言的脉络。张寿康将其界定为“文章中起承接流贯作用的相互呼应契合的词语线”[8]。文脉是文本整体的结构线索,语脉则是微观层面的言语关联线。语脉将语象贯通起来,在言语流变中起到衔接贯通的作用。因此,从文本建构的角度来说,语脉的贯通是文本意义流畅的重要因素,语脉通则意义表达顺畅;从文本接受的角度而言,语脉贯通了语象,因此循语脉阅读可以发现更细微的文本篇性特征。小说的情节往往以序幕、开端、发展、高潮、尾声、结局六要素进行分析解读,但是六要素难以体现小说文本的篇性特征,如果能将语脉这个文章学理论融入对小说的解读中,学生对文体的解读则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如《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是周锐的幽默小说,小学教材将之定位为记叙文,并用于复述能力的训练。教材意在引导学生通过梳理第一天至第四天顾客的要求与裁缝的表现来归纳故事情节,但是实际上这个文本有两条独特的语脉,即棉袄、夹袄、短袖衬衫、春装四种样式的衣服及与之对应的四个季节。这两条语脉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把握情节,同时文本独特的篇性特征也得以揭示,这篇小说以时间串线、以事串线、以物缀线的阅读方法也就转化为学生的策略性知识。
(二)解码层:结构技法与形象创造
结构技法艺术是重要的文体课程知识。作为重要动态解读能力的结构解码能力,一方面要求能熟练地辨识文本结构方面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体察小说家在结构上的匠心,要以“潜在创作者”的身份创造性地解读小说。如《腊八粥》一文中可以梳理出八儿“等粥、盼粥、猜粥、看粥、喝粥”几个阶段,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归纳整理上,简单明确“盼粥”是详写,“喝粥”是略写等,显然对文本线索和结构的分析就停留在释义层,未能深入辨析结构技法。一般而言,小说文本的结构技法艺术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文本艺术秩序的安排和编织,如果要向解码层进一步推进,就需要探查这样编织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哪里。小说以事件发展的流变作为线索,其线索的表征往往是比较“实”的人、物、事。但优秀的小说家运思结构线索时,不仅会考虑事件如何发展,还会考量文本背后情感的流动,因此事件的编织往往指向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解码的关键就在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只有掌握写事与写情的详略结构技法与八儿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学生才能有效培养语文要素。潘丽华在执教这一课时①,紧扣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及修辞手法进行品读,引导学生进一步体证小说详略安排的艺术巧妙,并设置了“进出灶房的八儿不仅看到了一大锅粥正在叹气,他可能还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挖掘文章描写的空白处展开想象”这一活动,以补白的方式让学生进一步体会作者对人物的刻画。从情节节奏、心理拓展两个角度来看,《腊八粥》的结构安排也是人物生活的结构面貌,作者的匠心在于能够用艺术的形式组织和展示生活的结构,并能使艺术的结构更典型地展现生活的节奏。这些结构与线索的安排好像是作者在文本中建构的一处处机关,只有打开这些机关才能读懂文本,才能欣赏到文本的精妙之处。
审美形象是语言符号的高级形态,是用语言符号构造出的艺术的幻象世界。中西方的文学理论都有塑造审美形象的思想,如中国古代文论的意象、意境思想,西方文论的象征、意象、典型等理论,均关涉审美形象层。叙事性文学类文本主要表现出事理特征,以典型作为重要的审美形象。小说文本以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作为基础。从审美形象来说,主要是构造人物形象和环境美,审美典型论是这类文本解读的重要工具性知识。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解读是小说解码的关键。首先,作为审美形象的人物,来源于生活的现实逻辑,但又超越现实生活的原生琐屑,作者以集中的笔法以少总多地展示人性的复杂,探索特定环境中人性发展的可能性。其次,文本内部的人物形象关系往往以错位的形态呈现,正因为揭示了人性的错位关系,才能更深入人性或社会的内部本质,比如《祝福》中祥林嫂与鲁四老爷社会阶层关系的错位,《故乡》中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历时演变的错位,继而与“我”的关系产生的等级关系的错位,都很好地揭示了人性与社会的复杂。除了解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教师还要在人物与情节(叙事特征)、人物与环境、文本内部人物、人物与当时社会文化原型几个关系中建构其课程知识,解码形象。
(三)评鉴层:跨体阅读与复调对话
除了批判性阅读、互文性阅读、读写结合等形式可以将文本阅读推向评鉴层,教师也可以通过跨体阅读与复调对话来实现评鉴。
适体阅读与跨体阅读的辩证统一在阅读教学中可以激活学生的文体期待,使其阅读到达评鉴层。适体是为了找到文体的一般代码图式,顺着文体的契约特性進行阅读;跨体是为了激活文体的陌生化效应,使学生对文本文体产生阅读的惊异。如果某小说文本具有适体与跨体相统一的可能性,也就是小说的文体具备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那就极易在适体与跨体之间一同激活读者的文体期待。比如郑振铎的《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文本的文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作者本人将其视为小说,这是作家文体创造意识的体现。有的研究者将其看作散文;阅读教学中有的教师当作散文来教,有的教师却当作小说来教。张志盛在两次执教《猫》这一文本时对其文体属性进行反思,也就实现了从第一次执教文体意识的缺位到第二次执教具有鲜明的文体意识的转化。第一次执教时,张老师主要设计了“整体理解”“精读感悟”“深入思考”“案情假设”四个环节,“整体理解”环节主要通过三只猫的形象和“我”对三只猫的不同情感来达成目标,教学重点在于为第三只猫“查明冤案”,并进一步以“如何避免冤案”的讨论引向生命教育。这个“查明冤案”的教学设计颇具创意,能激发学生的情境意识和学习兴趣。但是这一次的教学设计没能承载更多有教学价值的课程知识,仅做到更细致地展现文本内容,基本停留在读懂内容的释义层。文本的文学文体意识被稀释消解,如果是当作散文来教,作者的情感线索没有得到重视;如果是当作小说来教,形象分析也不到位。在没有文体意识的情况下进行阅读教学,很容易便会导致教学知识的选择模糊不清。因此,在对文本的文体属性进行进一步探讨后,张老师开始了二次教学设计,第一个环节的“整体理解”转变为“整体理解,梳理情节”,重点对三只猫及“我”的形象进行解析,进一步探讨“猫”形象的隐喻性,指向对小说主旨的探究。[9]这一次文体阅读教学激活了学生的文体期待,使得文体教学知识有了鲜明的小说文体意向性特征。
当然《猫》这一文本还可以尝试跨体阅读。陈罡在《〈猫〉的文体知识辨析及教学价值探讨》一文中立足学科知识探究《猫》这类文体模糊文本的课程教学,最终将之定位为“散文性小说”[10]。在辨析这类文本时,如果将适体阅读与跨体阅读相融合,可能会产生特有的文体期待效应。小说中的“我”可以作为叙事者,也可以看作情感的抒发者。因为如果通过情感脉络进行探寻,可以发掘出一个元叙事者,也就是作为小说叙事者的“我”与真实世界的“我”(作者)。这两个“我”有时是纠缠在一起的,甚至是合二为一的。“我”对第三只猫的死亡感到震撼并展开反思,这无论于小说叙事而言还是于散文抒情而言,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这里体现出的文体模糊性可以用来强化学生对文体的期待,实现文体感知到阐释体验的升华,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由言及情。不只是《猫》,其他体现出一定跨体现象的文本,也可以采用同一思路设计教学。
小说这一文体本身就是人物对话的场域。以复调对话的方式介入文本,亦是一种独特的评鉴方式。巴赫金所谓的“复调”概念,实际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高超的人物形象塑造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塑造依靠的不是独白,不是大量的客观描述,他的人物塑造超出了一般文本形象的客体属性而具有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使得主人公成为参与内在对话性的主体,成为“纯粹的声音”[11]。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小说都表现出复调的效应。正如复调是一种高超的小说技巧一样,教学复调也是一种对话技巧,教学的奥秘与小说的复调类似,就是激活原是客体的各种角色,使其具有自我意识,参与到教学内的对话机制中去,形成一个和谐的多声部。比如在教学《我的叔叔于勒》时,教师可以梳理小说的线索让学生把握故事梗概,并通过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称谓的变化让学生体会两人态度的变化,紧接着让学生找出文本中描写夫妇两人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词句,对其内心活动进行分析和揣摩,最后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将菲利普夫妇的心理活动通过对话还原出来。在这个对话活动中,师生双方都相互展示了自己理解的人物心理,激活了课堂上各要素的对话特性。学生需要与文本深度对话才能品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文本中的相关描写转化为心理描写。学生作为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自然产生的对话,学生还原的人物心理作为菲利普夫妇自我意识的载体也参与到整个课堂对话中,形成文体阅读的再创造,实现评鉴层向创造力培养的迁移。
参考文献:
[1]张毅.文学文体概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3]潘新和.“文体”“教学文体”及其他[J].中学语文教学,2007(12):3-6.
[4]黄伟.提高文体素养:语文教学的当务之急[J].语文建设,2009(1):9-12.
[5]汲安庆.语文阅读教学:必须正视的三大范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6):96-100.
[6]张心科.重回“三要素”:小说教学的问题与对策[J].语文建设,2018(5):26-30.
[7]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8]张寿康.汉语学习丛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9]张志盛.由《猫》的两次教学看文体意识的落实[J].语文教学通讯,2016(32):45-47.
[10]陈罡.《猫》的文体知识辨析及教学价值探讨[J].中学语文教学,2018(9):22-26.
[11]巴赫金.巴赫金集[M].张杰,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朱晓灿)
【作者简介】梅培军,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小学语文教材文学文本国家认同意识研究”(20YJC88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