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域下的庐隐作品研究
赵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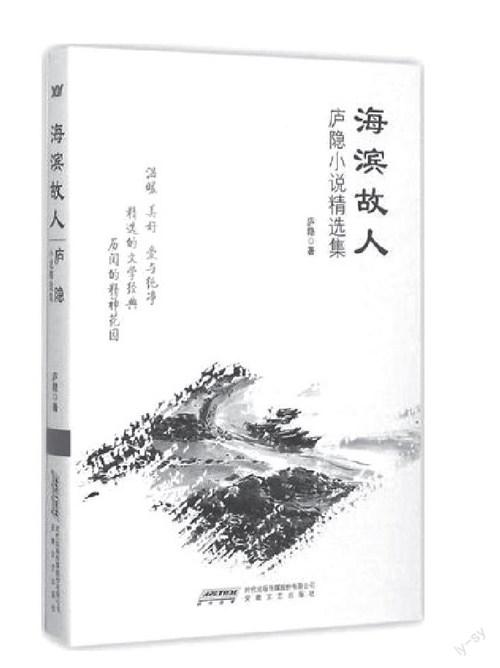
摘要: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出发探索庐隐作品中对女性命运的呈现方式及其透视出来的历史社会意义,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个人叙述声音到集体叙述声音的转变;二是从“交叉性”的角度剖析女性自我拯救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庐隐;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叙事学;女性命运
“五四”以来,女性作家群体崭露头角,为中国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她们曾努力改变女性“被书写”的局面,成为言说的主体。庐隐便是“五四”一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她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然而与后两人不同,庐隐是“五四”时期叛逆的“女儿”,她决绝、勇敢且富于才情,她的作品中充满着苦涩和忧郁。由于她是父母的弃子,在艰苦的成长过程中过早地尝尽人间辛酸,也许正是这样,她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所面临的“低矮的天空”和“血色的未来”。
庐隐笔下的女性大多面临着情感和理性的冲突。“在她的文本中,除了情智冲突的困境,几乎没有传统叙事所必须的动作与行动。她的主人公的行动(相爱、结合、组织新式家庭)永远属于外文本叙事范畴,而在文本中她们则永恒地处在前途未卜的幽瞑地带。”[1]
作为“五四”时代女性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同时受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庐隐是现今研究“五四”女作家的重点对象,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悲剧意识、女性意识和比较研究三方面。在对于其小说的叙事性及女性主义的探讨上,研究成果并不多。大部分论文都鲜少从女性主义叙事的角度分析庐隐的写作。女性主义声势浩大,其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它的思想理念自然也影响到叙事学的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文评和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典叙事学面临着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窘境,女性主义叙事学则从叙事与性别权力的关系着手缓解了这种尴尬,并且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支生力军。而在本篇论文中,笔者将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切入,以《或人的悲哀》和《海滨故人》两篇作品为例,揭示其女性主人公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所面临的困境,进而窥视“五四”时代女性的真实处境,透析庐隐的叙事所暗示的历史社会意义。
《或人的悲哀》和《海滨故人》是庐隐在1922年和1925年分别创作的两部作品,从体裁来看两篇都是书信体小说。在庐隐的个人写作中,书信体和日记体的创作随处可见。她如此执着于这两种体裁的创作,原因便在于:她的小说多属于情感氛围型小说,这两种体裁可将抒情最大化,将自我剖析进行得十分深刻。另一方面,写作、出版领域,长期由男性占据。在“五四”时期,民主观念深入知识分子群体中,女性也由此获得了写作和出版的权利,然而男性并不愿意放弃由写作和出版带来的舆论高地。而书信体和日记体都明确规定了受述者,讲述的往往是个人的经历,因而具有“私语性”的特点,这种“私语性”限制了女性话语的影响力,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可以说书信体和日记体的创作模式正是“男权社会”与“民主自由”相契合的产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五四”时期第一代女作家十分热衷于书信体和日记体的创作。
然而,在女性话语如此受限的情况下,庐隐还是尽可能地多发声,在《或人的悲哀》和《海滨故人》中实现了从“个人声音”到“群体声音”的转变。
一、 蜕变的体现:从个人叙述声音到集体型叙述声音
女性主义者的声音通常指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这些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兰瑟用“个人声音”(personal voice)来指代“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2]20,而用“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来指代“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2]22。《或人的悲哀》完全由9封书信构成,只有单一叙述人,属于个人叙述声音的作品;而《海滨故人》则由多个人物轮流叙述,表达女性群体的共同心声,属于集体型叙述声音的作品。由此可见,叙述者由一个变为多个,由单一的声音变为集体的共言,这无疑增加了女性言说的声量。
在《或人的悲哀》中只有亚侠一位叙述者,她通过9封书信,前后相隔半年多的时间,不断地向好友KY述说自己身体上的病痛、思想上的纠结和痛苦。在这些书信中她的声音显得“一家独大”,其声音所包含的情感力量也不断地漫延至整个文本,使得读者只能看见她的痛苦。这种结构上优越的声音,一方面彰显了亚侠精神世界,扩充了其情感容量,让她成为绝对的主体;另一方面也拒斥了其他的声音的存在,她的挣扎与痛苦得不到其他人的回应,便显得更为绝望。同时,亚侠用字母“KY”代指好友的名字,其实是用自己的声音虚化好友的存在,让好友只得成为一个空洞的倾诉对象,而无任何实存的意义。KY在文本中只发出过4次声音,其余时候都是由亚侠转述。这种无实存倾诉对象、无回应的情况,让亚侠只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沉沦,独立舔舐着伤口。
而在《海滨故人》中有5位女性主角,5人分述的形式汇成了同一支女性声音,即对自由与爱情的天真渴望,但又囿于社会现实的苦楚。她们生活在同一纬度,有3种不同的结局:露沙“一年不通音信”;玲玉、宗莹、连裳都结婚了,其中宗莹婚后憔悴了不少;云青研究佛理,想要回乡避世。这5位女性有3种不同的人生结局,但都揭示了当时的女性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作为一个人时,可以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作为一位女性,便要受制于种种力量的辖制。这5位女性的共言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力量,她们互相帮助,给对方支招,虽然最后仍然四分五裂,但是這种女性联盟的形式仍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
二、女性联盟的失败:忽视“交叉性”因素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在研究黑人妇女问题时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她认为黑人女性同时处于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交叉路口。由于二者的相互强化,黑人妇女同时被白人女性主导的女性主义运动及男性主导的种族主义运动排斥在外,进而更处于弱势地位。[3]后来“交叉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性问题的分析之中,兰瑟也将此引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之中。“交叉性指主体所拥有的不同的及多重的身份认同之间互相交叉、彼此作用的性质。它强调不同的社会范畴之间以及各压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4]
(一)男女各异的“交叉性”
《海滨故人》中的女性联盟以追求婚恋自由来反抗“父亲”所代表的封建礼教,正如玲玉和宗莹。在身份认知上,她们是“子的一辈”,同男性一样遮蔽在父权的阴影之下。她们接受启蒙(上新式学堂),与男性站在统一战线上共同反对家长制的权威。然而她们却忽视了,在男性面前她们还具有女性的身份,女性在面临封建专制的压迫时,也面临着男权社会的压迫。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并不意味着也推翻了男权社会。宗莹忤逆了父亲,顺利地嫁给了师旭,然而却日渐憔悴,这正是她没有认识到其身份的复杂性。“女性”和“子辈”双重身份的叠加,“男权”与“父权”两种机制的共同运作,让她们仍然沦为命运的牺牲品。
(二)女性内部的“交叉性”
《海滨故人》确实集聚了一众出身富庶的知识少女,但是每个人身上仍有其交叉性。正如露沙和云青。露沙从小被家庭抛弃,寄养在乳母家,在青山绿水环绕中成长。她没有享受过父爱,并且父亲早逝,在她的生命中缺乏体会父系权威的经验,自然也就不会被这种经验所裹挟。童年时,她没能在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没有享受过父爱母慈,而是在优美的自然環境中成长,体会到了自然的灵性,容易使生命得到舒展。她也会陷入爱而不得的痛苦之中,但是她能及时认清男性的面目,看清爱情不过是“战胜者的胜利品”,并且建立“海滨故人”之居来满足自己乌托邦的幻想,这正是她从自己的成长历程中获得的启示。然而云青不同,她从小生活在父母之家,享受父亲宠爱时自然也会依赖父亲的权威,她与父亲之间是一种割舍不断的关系,如果硬要在父亲和情人间做出抉择,她的内心必定痛苦而撕裂,一方是宠爱自己的父亲,而另一方是深爱自己的情人,当两者的矛盾无法调和时,她必定自我放逐,独自承受着所有的代价。在露沙和云青身上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女性身份,一种是“弃儿”,另一种是“宠儿”,这两者的差异则在于父亲经验是否介入,由此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事先假设有一个‘妇女的范畴在那儿,只需填入各种种族、阶级、年龄、族群和性欲等成分就可以变得完整,这是错误的想法。”[5]21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当建立女性联盟时,事先规定一个“妇女”的范畴是行不通的。露沙在建立“海滨故人”之居时就是预先框定了她们5位朋友,这等于是把“妇女的范畴”限定在她们5位之间,用她们来代指所有的“妇女”,然而正是身份的交叉性因素让她的尝试失败了。知识分子女性与劳动女性不同,而知识女性内部也有其分化。“海滨故人”的女性一是被隔离在男性主流叙事话语之外,二是与当时广大的无产阶级女性脱离,三是她们自身内部对父系权威的经验也不同。于是“海滨故人”的女性联盟尝试只能是一次女性自救的乌托邦幻想。
三、结语
波伏娃认为,“在存在主义的厌女症分析范式里,‘主体一直就是男性的,它等同于普遍的事物,与女性‘他者有所区别;女性‘他者外在于人格的普遍规范,无望地成了‘特殊的,具化为肉身,被宣判是物质的存在。”[5]16在“五四”的浪潮里,女性被磨灭了性别特征、暂时隐藏了“他者”地位,遮蔽于男性的“主体”之下,而与男性共同进行反抗,她们虽分享了一部分的成果,但是终究没有摆脱“肉身”和“物质的存在”,因而也不可能具有自我的超越性。
“五四”女性以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来反抗家长制及父系权威,转而投身于年轻一代的“子辈”,如宗莹便是。但是不曾想,“子辈”也没有给她们生存的空间,如宗莹婚后便患上了病,从此身体孱弱,精神萎靡。无法反抗父辈但又不愿意屈从于父辈之人,如云青,只好继续宥于原生家庭之中,研究佛理,以寻求精神的解脱。
从这两篇小说中,可以看出庐隐思想的转变和成熟,她敏锐地意识到了当时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自我与环境的冲突、自由与束缚的对立、女性自救的困难。但是这些困境背后的原因,她却鲜少深入分析,可能是由于她缺少如鲁迅般犀利的思想与批判的笔法,也可能是因为她只想在女性内部经验中寻求突破。不管是哪种原因,她都深深根植于女性本身,以感伤细腻的文笔书写,让尘封了数千年的女性内心得以敞开,为中国的文学史贡献了独有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CRENSHAW.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J].Stanford Law Review, 1991, 43(6):1241-1299.
〔4〕张也.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J].国外理论动态,2018(7):83-95.
〔5〕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