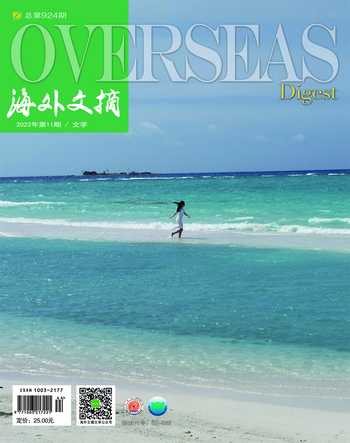一个人走夜路
谢维海

车一停稳,我逃跑一样下了车。不用乘务员提醒,我知道这是唐家站。
母亲托人带话过来,家里的稻子熟了,让我这个周末回家帮忙。我是周五下午4点多上的车,那时太阳还很毒。车从企水站开出,途经田西站、唐家站,终点站在雷州城。企水镇与唐家镇相距约15公里,我的家乡田西村是唐家镇的一个自然村,在唐家、企水两镇的交界点。
我又一次成功地逃了票,混在乘客里。那是1983年的夏天,我刚好10岁,我到了需要买票的高度。一张企水至田西的学生票要一毛钱,我口袋里有四毛六分。一毛六分是平时的积蓄,三毛是外婆给的。
不到两周岁,我就被寄养在企水外婆家。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村子与我家一样穷。那时村组叫生产队,劳动力也叫劳力。报酬多用工分计算,上工叫挣工分。起早摸黑地劳作,年终能分到几十块钱,过一个像样的年,这要感谢老天的恩赐。我出生后,母亲在家坐月子。就是这样的时候,队里还是有人三天两头来家门口提醒母亲该出工了。这些人是见不惯别人有闲下来的片刻,他恨不得你为队里献上你的分分秒秒,不分日夜。母亲只是在家休息一个多月,就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爷爷去世早,奶奶嫁到邻村也有5年多了。家里没人照看我,母亲就用背带背着我出工。对土地最初的好感,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没有与这片土地混个面熟,母亲就断了我的奶,把我送到外婆家,也断了我对田西最本真的记忆。我离开企水时,已是初中毕业。我没有理由去埋怨母亲,要养活一家子,总要腾出手去抚摸生活。现在想来,这是母亲一生中做出的最伟大的决策之一,我在外婆家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并顺利完成学业。村里的人都说,我是昵公昵奶(外公外婆)养大的。
我没有乡愁,可能与靠近故乡有关。母亲说:“你刚到企水的那几天,没日没夜地哭。才一岁多的孩子啊,但我还是狠下心来不去看你。”如果我的情感里真的有那么一段属于乡愁,我相信它应该就在那几天里消耗完了。
现在的小孩,上学有人接送。我从一年级开始,就与其他小孩一样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那时没有车来车往,落在你身上的目光充满善意,没有邪念。我可以选择到校的路径和时间。肥二的杂货店我基本没有停留过,这是由我的口袋决定的。街头的一些杂耍我喜欢围观,有意思又不用花钱。我慢慢适应了父母不在身边的生活。一些生活日常我过目不忘。从缝补衣裳到带小孩我都可以。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除了不会生孩子,我什么都会。我空闲时间帮外公照看小摊口,晚上到电影院卖冰棍、葵花籽,周末出租公仔书,这是好有场景化的生活。我左拇指有一伤疤,是为客人开椰子时伤到的,那年我14岁。当时不太认真护理,伤口发炎,后来是一个叫梁华国的同学从家里给我带来药粉才得以治愈。这个伤痕,是我与梁华国同学的友谊见证,也是一段岁月的青春打卡。
我的童年是温热的,这与外婆家的悉心照料有关。进入青春期就没那么幸运了。在这个个性张扬的年龄,我慌张无措,以愤青的姿态努力展示,却因缺了合适的观众,注定这是一个不合格的青春。我孩子正值青春,他平日里有了情绪,来了脾气,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向我宣战不需商量。这点,我是羡慕他的。
我从8岁开始就尝试着一个人从企水坐客车回田西。身高与年龄特征决定了车票的价位与购买要求。
显然,这次我是需要花一毛钱购买一张学生票的。我有购买实力,但没有这个打算。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口袋里哪怕只揣着一毛钱,出入就有人前呼后拥,有很高的江湖地位。一毛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了,两根雪条,或者一本有一定厚度的公仔书,汽水也有一瓶了,并且是气泡翻滚厉害的那种。我有逃票的强烈欲望与最初动机。
逃票也是一门技术活。你要找到一个不带孩子的乘客,最好是认识的,躯体配合表情让乘务员相信你们是父子或母子关系。成功地上了车之后,那感觉就像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了。这真是一次愉快的旅程。那时车里没空调,公路是夯实的黄土路,不时就有沙土从全开的窗子飘荡入来,但这不影响我因省下的一毛钱而滋生想象力。
很快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路边闪过的景物来看,田西站应该很快就到了,但客车喘着粗气还在匀速前进,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混在人群里,不敢吱声。我最初的预想是在田西站跟着别人一起下车,这样乘务员就不会发现我逃了他们的票。我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除了我,没有其他人需要在田西站下车,客车直直地往唐家站开去。这可是我头一回遇到的情况。当然我可以叫司机停车然后补票,这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只好继续猫在人群里。
我最终选择在唐家站下车,就像蓄谋已久的一件事情一样。只有我知道,这只是一场意外。在这场意外里,我要眼睁睁地看着客车经过我的村子,还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下车,不要下车。“你知道吗?这种滋味只有经历过才能体会。”很多年后,我对妻子说。
走出唐家站,我唯一而强烈的愿望是,我要尽快回家。我向着企水的方向走了回来。太阳温顺了许多,可以不用理会阴凉与否,拣直路走就是了。但很快我就遇到了难题,前面有一个三岔路口,我分不清哪一条才是回企水的路(我后来才知道,左边的是企水方向,右边的是纪家方向)。先走吧,遇到人再打聽,如错了再回头,大不了再耗些时间,反正我也不在乎了,我决定往右走。才走几步,我突然发现一辆手扶拖拉机载着鱼箱往左边方向开去。企水是渔港,这样装束的车辆我在企水经常见到。我知道,它是上帝的化身,给我指路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走走停停,也不觉得累。这个季节刚好是山稔果成熟的时候,路两边的林子就有,墨黑墨黑的,吃了两颗就停不下来,但也不敢多吃,这教训我是经历了多次。满肚子都是山稔果,不会饿了,但口渴得厉害。粘人草随处都是,这可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你要随时提防它的热情,走不多远,满裤腿都是,如果带着它在时装秀上出现,定会赚了一个生态环保的名号。
我急着赶路,大汗淋漓。稍一停歇,便能感到森森的凉意。一半因为汗水蒸发,一半因为恐惧。几里路都难遇上几个人,在空旷的天底下,有种闯入月球表面的错觉。经过一片坟茔地,那里神秘阴森,我几乎是小跑过去。都是一个人走路。上学时,街上人多,是心孤独,现在是人孤独,心杂乱丰富,可以发挥的东西实在太多,无端带来的恐慌挥之不去。我似乎成了某篇小说或电影里的主人公。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来到了三元桥。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这地方我来过,顺着溪水的流向右拐不远处是我三姨妈的村子。几头黄牛在溪中畅饮,有持续不断的鸟鸣声从远处传来,天地间空灵悠远。小黄牛躺在溪水里泡澡,尾巴一动,周边的水便被夺去了清澈。远处有鱼跃出水面,让黄昏的小溪生动起来,使岸上的人充满了希望。我在滩地挖了一个小坑,等里面的水澄清后,狠狠地喝了个够。
我突然发现了炊烟。如果那是我家的炊烟,便能牵着我一直回到家。显然不是,这炊烟是从距三元桥不远的一个村子里袅袅升起的。田西村不远了,前面的路都是我熟悉的,我浑身上下便有了力气。
黄昏渐渐暗下来。再一暗,就是夜了。天边远远地扔着几颗星星。公路两旁的行道树,黑黑地站在夜幕里。风吹树叶沙沙沙,有些吓人。我不敢想象剩下的一截子黑路会是什么样子,虽然我已习惯一个人走路,但走夜路并不多,我不由得加快脚步。我的田西村,有个词很特别,叫坡岭。当作岭,很矮,没岭的气势,但坡度很长。这对于走夜路的人是最好的暗示,坡岭到了,田西村也就到了。
是我走得快吧,我回到田西村时,月亮还没有完全升起。母亲在村口显得很着急,应该等了很久。
为省下一毛钱,我走坏了脚丫,大把时间都扔在了路上,还让母亲虚惊了一场,我惭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