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赫里福德的“世界之布”
田颖

“从我的脚跟到脚尖是二十九点七厘米,折合十一点七英寸。这是我步伐的单位,也是我思想的单位。”这是剑桥大学英语系教授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在《古道:徒步旅行》(The Old Ways: A Journey on Foot,2012)一书中写下的话。这位英国著名的学者和旅行家沿着古道徒步行走一千六百多千米,用双脚丈量土地,记录自己足迹所到之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看古地图册时,瞥见了赫里福德(Hereford)的“世界之布”(Mappa Mundi),它距今约八百多年,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纪“T-O”地图。之所以被称作“世界之布”,是因为地理学(geography)在中世纪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只能用拉丁文“Mappa Mundi”来统称“世界地图”或“书面的地理描述文本”。拉丁文中“Mappa”指“桌布或餐巾”,“Mundi”指“世界”,这是“世界之布”美名的由来。在地图的左上角,一个将巨大脚掌举过头顶的伞足人(Sciapods or Monoculi)引起了我的注意。看到伞足人的瞬间,我想到了麦克法伦对“脚”的推崇。从大脑思维到双脚徒步,这种形而下的方式是探索、感知世界的隐秘途径,只有旅行者自己最清楚“我行故我在”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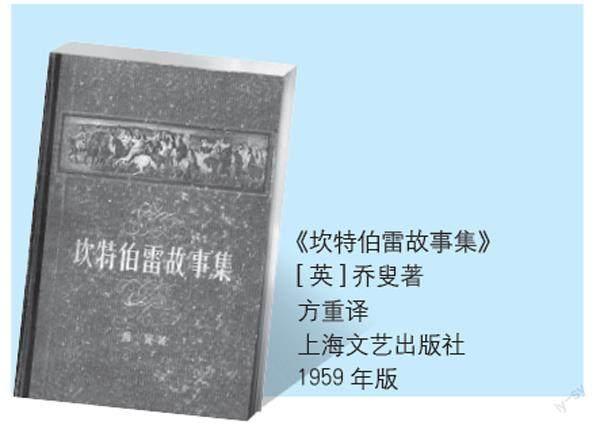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带着对伞足人的好奇心,我独自踏上前往赫里福德寻找“世界之布”的旅程。英国的铁路交通非常便利,四通八达。从剑桥出发,一路向西,经“英格兰心脏”伯明翰(Birmingham)中转,火车继续往南,直奔目的地—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的赫里福德。漫长的旅途总会让人浮想联翩,一路上思绪飞转,我惊讶地发现在时间轴上,赫里福德的“世界之布”与英国“诗歌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二者所处的时代都是中世纪,宗教是那个“黑暗时代”(Dark Ages)的信仰之光。乔叟拥抱信仰之光的方式是创作举世闻名的诗体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1387-1400)。这是一个关于二十九位形形色色的朝圣者,前往坎特伯雷朝拜圣托马斯的故事。在英格兰明媚的春天,“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竭的根须,沐濯了丝丝茎络,触动了生机,使枝头涌现出花蕾,当和风吹拂,使得山林莽原遍吐着嫩条新芽”(《坎特伯雷故事集》,方重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1页),坎特伯雷的故事由此开始。无独有偶,珍藏在赫里福德大教堂(Hereford Cathedral)的“世界之布”也不是以科学为目的来呈现地理、地形的,它是一幅关于中世纪精神世界的图像。这个惊人的巧合让我陷入沉思,向车窗外望去,七月英格兰的夏季美景并不逊于乔叟笔下的春色,蓝天白云下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绿草如茵的草坪上牛羊成群。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此次找寻赫里福德“世界之布”的旅行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朝圣。

瓦伊河
历经四个半小时,火车抵达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从火车站步行五分钟,我到事先预订好的酒店安顿了下来。稍作休憩,我拿着前台提供的手绘赫里福德小镇地图,按图索骥,开始探索这个古朴的小镇。
英国小镇的命名很有讲究,如果熟知英语词源,光看名字便可对其地理位置略知一二。赫里福德的英语“Hereford”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其中“here”意为“军营”或“士兵队列”,“ford”意為“河流穿过之地”。事实上,确有一条形如字母“Y”的瓦伊河(River Wye)穿城而过。虽为弹丸之地,但赫里福德历史悠久。追本溯源,小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六八○年左右圣古斯拉克修道院(the Saxon St. Guthlacs Monastery)的建成。后来,赫里福德被威尔士人摧毁,直到一○六六年诺曼征服英国之后,它才得以慢慢修缮。
从酒店出发,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小镇的中心地段“高城”(High Town),街道两侧不少老房子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里热闹非凡,出租车司机在此招揽生意,等候客人上车。拐角处,一栋黑白相间的木房子尤为打眼,它是小镇的地标建筑之一黑白木屋博物馆(Black and White House Museum),旁边有一座矫健有力的公牛铜像。这栋三层木屋建于一六二一年,是英格兰保存得最好的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建筑之一,原本是小镇上一个屠户的住宅兼商铺,这就不难理解房子旁为何矗立着一头公牛,似乎有“广而告之”的功能,以此为屠户招揽生意。木屋内的家具陈设和木质架构基本保持了原貌,几经修缮后,木屋被改造成博物馆。

黑白木屋博物馆

黄油集市
那天适逢周三,是赫里福德小镇每周的“赶集日”(Market Day)。我站在木屋三楼的窗边,透过厚厚的玻璃格窗向外看,不远处是教堂尖顶,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小贩的吆喝声和教堂钟声不绝于耳,这情景好似一幅油画。四百多年来,这栋黑白木屋一直屹立在镇中心的拐角处,见证了古老的赫里福德小镇的历史和变迁。
从博物館出来,往前走几十米是“黄油集市”(the Butter Market),大门装饰着华美的雕像,每到整点,最上方的大钟会准时被敲响。依据手绘地图的标识,黄油集市是“市中心隐秘的瑰宝”。自一八六○年开放以来,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当地十分有名。从大门进入,我发现集市并不大,各个商铺沿室内通道两侧有序排列,这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商业街模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有地毯、黑胶唱片、农产品、美食、手工鞋包等出售,五花八门的商品应有尽有。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可以淘到不少宝贝。不过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走马观花逛了一圈后,从侧门而出,顺道右拐,圣徒教堂(All Saints Church)赫然映入眼帘。
圣徒教堂很有特色,它与咖啡馆合二为一,这样的经营模式在英国并不多见。沿着“宽街”(Broad Street)直行三分钟,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赫里福德大教堂。从正门进入,教堂北耳堂(the North Transept)是十三世纪时期赫里福德大教堂的圣托马斯大主教之墓,灵柩上方绘有一幅三角形的镶金蛋彩画,画面中心是“世界之布”的复制品,它被圣母、圣子、圣徒和天使们环绕着。这幅画提示前来朝圣的人们,“世界之布”的真迹应该就在不远处。横穿教堂中殿(the Nave),从南耳堂(the South Transept)的侧门而出,便到了室外的教士会礼堂花园(the Chapter House Garden)。这座十四世纪的哥特式花园与北耳堂遥相呼应,原本花园有屋顶加盖,但在英国内战时期(1642-1651)被毁。园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景色非常怡人。在花园里,我偶遇一对当地英国母女,她们对东方充满了好奇,我们相谈甚欢。她们告诉我,让我心心念念的“世界之布”就珍藏在花园后面的大教堂图书馆里。
古人有“近乡情怯”一说,于我来说却是“近图情怯”了。告别母女俩,我从花园左拐,穿过狭长的咖啡店,来到位于教堂东南角的图书馆。购票后,径直往里走,可以看到走廊两侧关于“世界之布”的简介。一扇大大的玻璃格窗下是用现代技术按照原图尺寸复刻的“世界之布”3D打印制品,我用手仔细触摸,可以明显感觉到地图并非光滑平整,而是上下起伏,凹凸有致,这让我对“世界之布”的真迹更加充满期待。在走廊尽头,一扇厚重的感应木门自动打开,里面是光线略显昏暗的展厅,闻名遐迩的“世界之布”就挂在展厅右侧的墙上。

教士会礼堂花园

收藏于赫里福德大教堂的“世界之布”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地图的奥秘:认知、信仰与文学》的小文,文中提到“世界之布”,并论及中世纪的人们是如何凭借有限的地理知识,来勾勒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世界之布”总共绘制了五百多幅图画,其中包括四百二十个城镇,三十三种植物、野兽、鸟类和怪物,三十二个世界族群形象和八幅古典神话图画。因此,“世界之布”融地理学、制图学、动物学、人类学和文学于一体,堪称一部中世纪的“百科全书”。我从未想过,曾经仅凭二手资料写下的想象性文字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现在,这幅绘制于十三世纪的中世纪地图如此鲜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之前难以企及的遥远,如今却缩短至区区的几厘米。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地图上的所有细节,甚至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张巨大牛皮上的粗大毛孔、微微翘起的边角和被钉子敲打过的孔洞,这一切都让人惊叹不已。
身临现场让我对“世界之布”的前世今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它的原材料是一张完整的牛皮,皮革经人工除毛后,用石灰水、尿液浸泡进行软化,再用力拉伸,以扩大使用面积,最后变成了一张高1.59米、宽1.34米的宽大“画布”。除了牛皮这个主要的原材料之外,橡木苹果的虫瘿与动物毛发混合后被制成墨水,色素与蛋清混合后被调成各种颜料。整幅地图用黑、金、红、蓝、绿五种颜色进行绘制。其中,绿色是海洋,蓝色是河流,右上角醒目的红色是红海和波斯湾。以左上角为起点,沿顺时针方向,地图圆周的四个角分别绘有四个烫金拉丁字母“MORS”,意为“死亡”。这似乎暗示一旦越过被绿色海洋环绕的地图边缘,最后将面临生命的终结。

“世界之布”上一个将巨大脚掌举过头顶的伞足人
在空间布局上,“世界之布”沿袭了中世纪T-O地图的传统。地图以圣城耶路撒冷为圆心,T代表三大水系,分别是位于下方中轴线的地中海、左侧的顿河和右侧的尼罗河,O则代表环抱地球的海洋。三大水系又把陆地划分为三大块,上方半圆为亚洲、左右两侧的四分之一圆周分别是欧洲和非洲。在“世界之布”上,制图师分别在三块陆地上标识了欧罗巴(Europa)、亚细亚(Asia)和阿非利加(Affrica)的烫金字样。但特别有趣的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十三世纪的制图师对地理的认知有限,欧洲和非洲的名称完全标反了—欧洲大陆被标为Affrica,非洲大陆却被标为Europa。至于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目前学界还无定论。亚洲之所以位于“世界之布”的上方,是因为在中世纪文化中,人间天堂位于东方,所以最尊贵的东方位于T-O地图上方的醒目位置。与之呼应的是西在下方,北在左侧,南在右侧。换言之,与现代地图相比,T-O地图的方位相当于逆时针旋转了90°。
在“世界之布”左上角的十一点钟方向是一直让我好奇不已的伞足人。仔细端详一番后,我发现伞足人原来只有一只脚,却健步如飞,脚掌大如巨伞,翘起脚掌便可遮挡阳光。依据整幅地图的空间布局,研究者们推断伞足人所处的位置是现今的印度。在地图左下角,有一大块醒目的陆地,它是今天的大不列颠—英格蘭、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在现场讲解员的指点下,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在“岛国”上找到位于瓦伊河畔的赫里福德。在“世界之布”上,赫里福德毫不起眼,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它。据说这是因为几百年以来,远到而来的朝圣者们都喜欢用手指不断触碰赫里福德所在的位置。天长时久,它的轮廓线条变得黯淡模糊,这不免让人担心有朝一日赫里福德会从“世界之布”上消失。

铁链图书馆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世界之布”圆周内的文字均为拉丁文,但圆周之外边缘地带的文字却是法语。在中世纪,社会上层阶级都说法语,而博学多才者则以说拉丁文为荣。“世界之布”的这一细节显露了制图师的雄心:这幅地图的受众群体不仅是满腹经纶的博雅之士,还包括身份尊贵的上层阶级。于是,与其他中世纪T-O地图相比,“世界之布”另一与众不同之处便显现出来—在地图的左下角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的脚下有一行用法语写的文字,它明确标注了“世界之布”的制图师是霍丁汉或拉福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Haldingham, or of Lafford)。这样的署名方式在当时十分罕见,因为中世纪地图很少会出现制图师的名字。历史上关于这位制图师的资料甚少,研究者们推测他为斯温菲尔德大主教(Bishop Richard Swinfield)工作,并一路追随大主教,从林肯大教堂(Lincoln Cathedral)来到赫里福德大教堂。由于存在这样的关联,所以学界一致认为,赫里福德的“世界之布”参照了同一时期珍藏于林肯大教堂的另一幅地图。
在不大的展厅里,“世界之布”的对面是一块三角形的橡木嵌板,顶部用花形木刻浮雕装饰。这块嵌板直到一九八九年才重见天日,别看它其貌不扬,却隐藏着一桩至今悬而未决的“迷案”。原本这是一幅高三米多的三联画,左右两侧的画板上的天使和圣母庇护着嵌在中间的“世界之布”。在十八世纪晚期,两侧的联画不翼而飞,至今无迹可寻。大约在一七八○年,一位名为约翰·卡特(John Carter)的古董收藏家绘制了一幅“世界之布”三联画的素描图。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这张线条简单的素描,想象它当初的华美模样。在橡木嵌板的正中央,一个凹陷的压痕十分醒目。经研究考证,它很可能是圆规留下的印记。这个位置恰好与“世界之布”的中心耶路撒冷完全吻合,以确保地图被固定时在尺寸上与嵌板严丝合缝。如今,原本合体的“世界之布”与残存的橡木嵌板隔着展厅走道,默默凝望彼此。八百多年来,它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毫无保留地呈现了中世纪的精神世界。
赫里福德大教堂的图书馆不止“世界之布”这一件珍宝。还有另一件无价之宝“铁链图书馆”(Chained Library)珍藏在展厅的另一头,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铁链图书馆。顾名思义,所有的藏书都无一例外地拴上了长长的铁链。铁链一端固定在书封上,另一端固定在书架的铁杆上。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图书被盗,因为当时印刷业还未大规模发展起来,很多图书都是手抄本,弥足珍贵。赫里福德大教堂的铁链图书馆收藏了约一千五百本图书,其中有二百二十九本中世纪的手抄本。为了准确找到藏书位置,每个书架的侧面都贴有整理好的图书目录。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铁链图书馆在欧洲十分流行,后来随着印刷业的兴起,图书不再那么珍贵,铁链图书馆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了完好地保存这些图书,铁链图书馆内常年使用空调来保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每扇玻璃格窗上还安装了卷帘,以遮挡强烈的阳光。当我从每个书架边踱步走过时,感觉这些被链条紧锁的典藏古籍是时光的卷轴,它们虔诚地记录了一千多年前先哲对知识的尊重和敬仰。
当我从展厅出来时,已是黄昏时分。英格兰的夏天日照时间相当长,这个时间点阳光依旧明媚。孩子们在教堂外的草坪上嬉戏打闹,大人们三两成群地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或手捧咖啡坐在长椅上聊天,这是难得的休闲时光。刚刚从时间卷轴另一端游览完毕的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最后,乔叟十分谦逊地宣告了“作者告辞”,希求“在未死之前达到圆满的境地”(第345页)。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不敢有这样的奢求,看着一直拿在手上的小镇手绘地图。不由想起二○二一年十月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另一幅地图—巴比伦世界地图,这块大约在公元前七百年至公元前五百年间制作的泥板是已知最古老的世界地图。巴比伦世界地图与赫里福德的“世界之布”相距近两千年,它们却以不同的方式勾勒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和认知。离开赫里福德大教堂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教堂尖顶,一轮弯月若隐若现地挂在上面。这是我向“世界之布”的辞别方式,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我无意中效仿了麦克法伦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土地。虽然我无法像伞足人那样健步如飞,但在回望自己足迹的那一刻,我完成了一个人的朝圣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