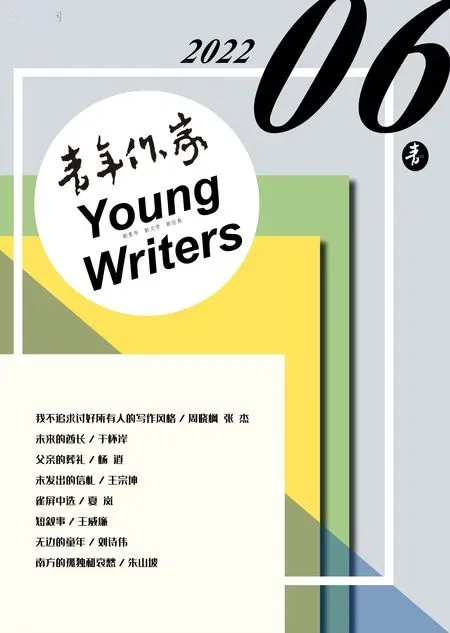南北文学差异及南方写作的弱势
刘火
一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77—1986),无论作家、批评家,还是读者,只要留心便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情况:大致以长江为界,文学南北的各自总体格局,有着许多差异。本文不以理论先入为主,先从个体的文本开始谈起。
北京的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宣告了“文革”文学的结束,上海的卢新华的《伤痕》(1978),与之南北呼应,迅速(但当时并未意识到)合力筚路蓝缕地开创了一个即将勃兴的文学大潮:“伤痕文学”。这是新时期文学的触发点,它预示了“五四”新文学过了几十年后又一次的大爆发和大趋势。不过,如果我们将这两篇(真是巧合!北京一篇,上海一篇)稍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明显差别。前者的大声疾呼和控诉,后者的娓娓诉说和哀怨,正是这个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一开始似乎就暗示了文学南北的分野态势。 蒋子龙的《燕赵悲歌》(1985),柯云路的《新星》(1984)、《夜与昼》(1986),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1983),而在南方,像这种气势的作品几乎少见。南方似乎就只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1979)独树一帜(幸好当时有北方的作家孙犁相助)。以改革为题材的作品,南方也极少像北方那样大刀阔斧和金戈铁马。在自然景观上,北方有张承志的《黑骏马》(1982)、《北方的河》(1984),邓刚的《迷人的海》(1984),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1984),郑万隆的《异乡异闻》(1984)等。这些作品的自然景观呈现出“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萧萧落叶”“百岁如流”(司空图语,《诗品集解》)的壮阔;而在南方,李杭育的葛川江、李宽定的黔北山岩、周克芹的川中丘陵、孔捷生的南方之岸,似乎就是一种“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语,《天净沙/秋思》)的意境。虽说这是不同的美学范畴,本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但由此足见文学南北的差异,无论题材还是美学意蕴。连最能触及时弊、惊世骇俗、讴歌新人和报告时代风云的报告文学,以及撰写报告文学的大家也几乎为北方所垄断,有名的乔迈、理由、陈祖芬、肖复兴、李玲修等人都是在北方。更为奇怪的是,许多南方发生的大事(如海南岛贩卖汽车狂潮)也常被北方作家抢了去。
以上粗略对比,绝没有扬北抑南的意思,何况笔者就是十足的南方人。而是说,在笔者有兴趣于当代文学时,平时读书时缕缕丝丝的想法总在缠绕着我,总想弄点什么头绪出来。于是,当我着手整理手边的卡片和准备撰写本文时,我才“顿悟”起来,斗胆地写出了“文学的南北差异”这个大题目,而且还试图写出这种差异的原因。
二
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里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即地域制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他这样说:“气候与自然形势仿佛在各种树木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一种树木生存繁殖,而多多少少排斥其余的。”(《艺术哲学》,傅雷译,34)。丹纳依据这个观念(或理论模型)举了许多例子,现摘录一条:“法兰德斯人的气质的确是在富足的生活与饱含水汽的自然界中养成的:例如冷静的性格,有规律的习惯,心情脾气的安定,稳健的人生观,永远知足,喜欢过安宁的生活,讲究清洁和舒服。”(同上书24)。用这种观点来观照中国文学的并不多,罗根泽写于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提及,但并未深入;并非文论专家但为通识大师的金克木先生,倒是专门写过一篇题为《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4期)。当然,这篇文章正如题目所示,仅仅提出一种观念和一个模式而已。从本文一开始所举个案看,新时期文学的地域所制约产生的情况,事实是明摆着的事。
稍有点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以淮河-秦岭而划界的南北中国有着明显的地貌、水文、气候、植被的不同。南方多丘陵,而无高山大壑,北方有莽莽丛林、浩瀚草原和沙漠,还有被水刻出的黄土高原的大沟大垇。于是北方就出现了《北方的河》与乌热尔图《琥珀色的篝火》(1985)式的大兴安岭的雄浑壮阔,出现了《肖尔布拉克》(张贤亮,1984)里展现的戈壁和荒漠。这种以大森林、大草原、大漠为地理背景建构的文学文本,在南方是无论如何都没有的。由于描写对象(也可以说是未被审美主体过滤的审美客体)本身的粗犷,因此它往往激发作者本人主体意识的一种裂变。“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张承志、张贤亮等人以北方自然景观为背景的小说所呈现的气氛,往往是悲壮和苍凉的结合体。由于有“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景观,迫使其审美主体的潜意识和联想必然不同于南方的小坡小溪修竹等景观产生的意象。即使是同时表现大河源头的作品,陈村的《走通大渡河》(1986)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就有着显著的不同 。前者以英雄主义为主题,后者以人化入北方的河的魂灵为主旋律,将各自的大河壮观显示于众。这两个主题的确立和最后的形成,显然与南北大河的不同历史与共时状况而诱发的(不是决定而是诱发)。北方的河是汉文化的摇篮,但历史长远,历代治理不变,因而造成了许多灾难及导致这些灾难的地理现状,这便使进入北方的河的作家意识到对这个对象的历史思考和未来思考;而大渡河的文明历史毕竟晚于北方的河,而愈到源头,愈是蛮荒,那么就愈是增强了征服者的勇气,诱发英雄主义情愫的高涨。这样,陈、张二位作家就各自演出了一出依托于描写对象上的好戏:《北方的河》成了思考汉文化历史的象征,《走通大渡河》便成了实习英雄主义的壮举;这也导致了前者在风格上的深沉和悲壮,后者在风格上的冒险和稚嫩!
由于自然景观的参照系不同,表现人类共同心理(即马克思所说的“类意识”)也会出现差异。比如同时以情爱为中心的作品,张承志的《黑骏马》(1982)与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1981)和李宽定的《山月儿》(1984)就不同。前者的自然景观是浩瀚的大草原,在此生活的蒙古族人养就了一种剽悍特质,因此,索米娅与白音宝力格的爱情悲剧就有一种撕裂人心的气氛。后者的自然景观或是川中的浅丘或是平缓无大坡的黔北高原(地域空间较为狭窄),以至于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内心也呈现一种似乎没有波澜(许多年前的李劼人《死水微澜》似乎也能佐证这一点)的状况,学英的爱情就是这样,山月儿的悲剧也是这样(李宽定的全部小说都是如此一种舒缓平稳的叙述节奏),而周克芹的容儿的情窦初开却写得如晓风一般清扬舒缓。北方女作家木伦·乌拉(即乔雪竹)的《在查干陶拉盖草原上》(1985)中的情爱描写的格调、气氛和意境,即老罗、凤朵、肖哥拉的爱情纠葛所产生的悲剧就与《黑骏马》相似。再来看下面几段文字:
巧巧忙回答说:“你这个人才怪哩!挖根儿挖底儿,人家不听就不听嘛,你还问……”她拉着容儿的手说:“走吧,找小翠去!”容儿没有动。不知怎么的,她愿意在这潮湿的田坎上多坐一会儿,听凭清风吹拂她滚烫的面颊。近两年,容儿家里的生活的明显变化,她并不是不知道——哪能不知道呢!她又不是一个傻女子。然而,却只有在今夜,在此刻,对于变化了的生活,她才强烈地感觉到了。就像前两年,有人对她说:“哎呀,你长这么高了,长成个大姑娘了。”经人家这么一说,她才感到自己真的长大长高了,再不是个小女孩了。(《山月不知心里事》)
山月儿送学英回家。在融融的月光下,她们相跟着,在窄窄的山路上,慢慢地走。有风,但那风,小小的,仿佛是路边的白杨树轻轻地摇动,树叶儿扇出来的。她们不说话,把脸儿朝着风的那边,让风吹,凉凉的,好舒服。”( 《山月儿》)
这时,前方的晚霞在草原上拉开了整个天际,像出征的战舰一般雄壮威武,面对着越来越暗淡的天穹,它们扯起了火一般的风帆,金闪闪红彤彤地向东扩展,而老罗的四驾马车,在天似穹窿、笼罩四野的草原上,犹如沧海中的一叶小舟,飞在草尖上,淹没在芦苇丛中,颠簸在沙窝里。(《在查干陶拉盖草原上》)
此刻,宇宙深处轻轻地飘来了一丝音响。它愈来愈近,但难以捕捉,像是在草原上空的浓郁空气中传递着一个不安的消息。等我刚刚辨出了它的时候,它突然排山倒海地飞扬而至,掀起一阵壮美的风暴。我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黑骏马追赶着它的步伐。接着,从那狂风般的雄浑前奏中,流出了一个优美悲怆的旋律。它激烈而又委婉地起伏着,好像在诉说着草原古老的生活。(《黑骏马》)
其实,不标篇名,我想,读者也会一眼便认出它们各自的背景以及这背景前的不同心境。也许有人会以为地理决定文学是一种机械唯物论,但我现在所说的不是决定而是制约和诱发。我们当然知道,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精神现象,一种作为审美主体的独立的外在形式。虽然这种外在形式是通过社会的触发为前提的,但在诸多前提中,与作家长期生活的地理因素有着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这地理(水文、气候、山川走向、与外界通塞等)因素对文学的诱发和制约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它作为审美对象对审美主体的有形与潜形的吸引力,迫使审美主体对客体作出此时此地而不是彼时彼地的审美感知。这种感知就是康定斯基所说的“自然创造出一个精神现象”(康定斯基,《论艺术里的精神》,50);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诱发剂对审美主体起着离心力作用,迫使审美主体通过对客体的反射作出此时此人的“人化”(马克思语)过程。前者从表层展示小说产生不同地理的外在风格的不同;后者从深层展示不同地理产生的文学具有共同处在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总体文化心理格局之上。从而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决定和成就了文学的差异。
以此观点,我们同样可以观照小地理环境,答案也是一样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几乎篇篇简约淡泊,也有一些哀婉,贾氏的古秦地,虽是山地,但没有大兴安岭般的莽原雄浑,也不具备大草原般的浩瀚辽阔。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1982),由于状写的是特大洪水,因此其描写对象(包括地理和地理中的人物)才产生了南方文学少见的粗犷。周梅森更是一个例外,其具有史诗般意味的小说是建立在“沉沦的土地”“崛起的群山”“黑色的太阳”、恐怖的“黑坟”、要钱不要命的窑工、充满诱惑和死亡的矿井等等上,这使周氏小说在南方以至于在全国都独树一帜。魏氏与周氏的悲壮氛围,其美学格调,相似于北方文学的豪放和悲壮,除了表明文本之外的对象对文本的意义,还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可以一统天下的。在大致的格局中,也就是本文所限定的文学的南北差异的大致格局,不同的风格,总有(而且一定有)与自己游离的成分,也就是,即便差异的存在是一种常态,但常态之下的变态(或异态),可能才是文学多样化和互动化的必然。在这种常态与变态中,相互掺和相互作用,也一样不能相互替代。文学的个人化和个体化是文学的本质决定,计论文学的南北差异,从文学的本质来讲,也是讨论文学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文学。文学的优莠,不是文艺政策所决定的,而是由文学的个体性、多样性、丰富性和差异性所决定。正如艾略特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替代另一样东西”(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文学的南北差异的原因首先表现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上。在文学主体论的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我们以前的文学研究太注意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不太重视其内部研究,以前的外部研究主要落实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上,其实从新时期十年文学实践和业绩看,我们知道,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就“文学与地理环境”这个领域。事实上,不仅研究得很不够,且一涉及政治领域,包括政治地理和地理政治领域,便裹足不前。
三
八十年代兴起的寻根小说,后来被这群作家命名为“文化小说”。关于文化小说的讨论已经很多了,笔者曾在第一时间(刘火《我不敢苟同》,《文艺报》1985.8)介入过这场后来影响巨深的讨论。在此,我不准备谈它的是非功过,之所以要谈它,是因为即使在同一个“复兴汉文化”的旗帜下,文学亦有着明显的南北差异。比如北方的贾平凹、郑义等人,南方的韩少功、李杭育等人的作品的差异。
如果说文化小说的内部有差异的话,那么首先就表现在对汉文化的区域(或准区域)文化表征的直接继承之上。有的论者提出汉文化具有八大区域(即中原京派、江浙海派,闽粤岭南、江汉楚、四川、陕甘、辽吉黑、关东等)文化模型(见《黑龙江日报》1986.6.25),在我看来,汉文化的最大区别其实就是以齐鲁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和以荆楚(包括江浙)为中心的南方文化(疑古派大师顾颉刚在讨论神话时讲过,中国的神话是一个从昆仑到蓬莱,从黄河到湘江的过渡、转圜及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过程,可参见《古史辨》第一册与第五册“自序”),当然不否定有更细的划分。在文化小说里,这种区域和历史沿革所构成的南北差异表现是很明显的。通观贾氏、郑氏小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讴歌一种藏之落后和愚昧中的美,也就是他们尽力去发掘这种美。不论是《远村》(郑义,1986)中的叶叶、万牛,还是《远山野情》(贾平凹,1985)中的香香,《天狗》(贾平凹,1985)中的天狗、《火纸》(贾平凹,1986)中的阿季,他(她)们都有一种“朴直的美”(郑义语,见《中篇小说选刊》1984.2)和“原始的美”(徐剑艺语,见《文艺评论》1986.4)。与此不同,无论是《爸爸爸》(韩少功,1985)中的丙崽的痴劲,还是《女女女》(韩少功,1985)中幺姑的自戕,韩氏是要剥开人性丑的那一面,让它于光天化日下裸露。韩氏小说中的疏寂和冷峻为揭示国民劣根性打下一种非美的氛围。即使以歌颂人性美为主的李杭育,在《船长》(1984)里,就曾将“船长”与秦寨的可憎可恨那一面不留情面地揭露出来。这个文学相悖共在的现象真实表明了南北文化差异对文学的潜在作用。儒学在齐鲁诞生,经过两汉,再经魏晋南北朝唐佛的浸淫渗透,最后在南宋集大成后形成理学,这一千多年时间嬗变过程的根据地大都在北方(佛在南北同时并行),经过从东到西(儒的横移)和从西到东(佛的横移)再从北到南逐渐扩展和深入“民族意识深层”(李泽厚语,见《文汇报》1986.1.28)。以仁、礼、义、孝、忠为主体的儒学于北方先天的根深蒂固,而在南方则具后天性,而且南方的楚文化又起到了某种抵制作用,使儒学正宗不及北方厚重或“正宗”。关于中华文化是否同源,李泽厚曾在《美的历程》(1981)中认为南北文化同源,后来李先生改变先前的同源说,李泽厚在《古典文学札记一则》一文中说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见《文学评论》1986.4)。不仅古代史是这样,近代史更有一个情况有意思。近代史是以南方大门被打开而西学东渐为起点,同时西方的文化和文明,由南向北衍生。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几乎所有关于打开国门请进西学,大都以上海、浙闽、粤港为重镇。虽然五四运动肇事于北京,但新文化的中心则在上海(如陈独秀的《新青年》就创刊于上海,现代出版印刷业最早、最大、最多的书局在上海,外文报纸期刊最先最多都在上海创刊等)。正如此,受正统文化深入的北方社会文化心态的制约,贾氏郑氏才那么不加批判地讴歌汉正统文化洗礼的北方民族的原始和朴直的美,如“兄弟换妻”“调换亲”“拉边套”等扭曲的爱情婚姻家庭形式发掘的美和善。南方就不同了,韩氏以荆楚文化的非正统(如巫教盛行、屈子行吟、屈子向天、屈子自沉等的胆量)观念来反映湘西风俗民情,剥开一些(不是全部)忠、孝、节、义的画皮。文化内在的差异,使南北文化小说也有着其价值取向甚至价值结构的不同。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必须提及。陆文夫与邓友梅这两位同时代而又几乎同命运的作家,都以写自己家乡风土人情见长。前者有《美食家》(1983)等,后者有《寻访画儿韩》(1982)、《烟壶》(1984)等,两人都爱写物化文化。所谓物化文化即某些物件呈现出(或积淀着)民族的某种精神,如宋元起的中国画表现出士大夫的闲情(即所谓“文人画”),由北向南而在南方蔚为大观。在同时描写物化文化时,陆文夫大写“吃”,邓友梅大写“玩”。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在笔者看来,这仍然与地域文化品格分不开。北方是儒学圣地,虽连年战乱,但由于统治中心在北方,儒学传播在北方,因此整个北方造成上下的正统和虚荣,人们于是更讲究穿、住、玩。在儒家礼制里,吃、穿、住、行都得是礼的表达和秩序。但相对于穿、住、行来讲,“吃”更具第一性,更别说物化后的“玩”。南方战乱少,加之开发比北方迟,但因南方物产丰盈,南方更讲究吃(如《九歌》中的祭祀供品就已经很精美了)。南方重“吃”,北方重“玩”的这种消费结构和精神内核的不同见证于文学,就呈现出了陆氏与邓氏的差异。北方的“玩”与南方的“吃”,现实中附首即拾。这样,地域文化及文化影响的风俗和魔杖,迫使南方的陆氏写苏州的“吃物”和“吃法”,北方的邓氏在那儿津津乐道灿烂文化凝结在古画烟壶的物体之上。嗨,这真是各人头上一方天哇!不!是各人脚下一方地呀!顺举一例,冯骥才从《雕花烟斗》(1979)到《神鞭》(1984)、《三寸金莲》(1985)之后越来越向中国古董皈依,除了再证南北文学差异之外(冯的中国式古董的话题,是这则小文不可能承担的沉重话题),也可以看到南北作家精神的差异。
在展现市井味上,南北也有差异。邓友梅、李龙云(此人的小说与戏剧一脉相承)等写市民的小说,就给人一种滞重、沉闷的感觉,活化出古老北京传统凝固于某隅的特殊文化气氛。南方由于经济开放活力和近代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雅马哈鱼档》(章以武、黄锦鸿,1984)、《女工牛仔》(陈敦厚,1987)等作品就是对外开放后出现的轻喜剧。北京陈建功的《鬈毛》(1986)与上海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1985),无论从内容、人物、故事框架以及叙述角度和叙述节奏都很近似(也许取掉作者名一瞟眼看还会以为是一人而作呢)。但是,“鬈毛”是从反传统逐渐走向玩世;“富士”则是从反传统走向现世,反叛式的皈依。这反映了南北文字在揭示青年走向成熟时的不同审美视角。
四
在阅读和欣赏报告文学时,我很久不得要领,我常想,为什么报告文学大家都在北方,为什么十年间最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品几乎都产生在北方?南方真缺如椽大家,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或触目惊心的人和事?从理由到陈祖芬、从大贪污案的震惊到大卖汽车案的深省,从四五运动的那感天动地到经济跃动的全方位等都涉及一点,即中国的政治!写政治大事件和写风云人物几乎成了重大报告文学的专利,虽说这一观念正接受挑战,即报告文学应写平凡人生,于是报告文学便“天经地义”地成了北方的专利。
由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是全国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的信息集结、贮存、反馈和处理最大最快的地方,这便使理由等人得天独厚。即使是远离北京的海南,理由也会很快飞到那儿采访、撰写和发表!另外,由于报告文学往往触及时弊,很可能牵一发动全身,导致居住在二、三、四线的作家不敢写,而居北京的一大批大家除了本身的人格力量和气质外,还在于背靠京域。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密集地,没有一个比较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中心,我想,有些作品是很难问世的。许多涉及敏感题材的作品和异质的表达方式的作品得以问世,正是抛弃过时的文艺政策,或者说文艺的管控松弛所形成。由此说到十年报告文学,无论如何都会提及徐迟的《地质之光》(1977)与《哥德巴赫猜想》(1978)。这两部报告文学是“文革”后文学的扛鼎之作和开山之作。为什么这两部报告文学会以歌颂为主基调,这是新时期所急需的力量和理想。当然也会有《人妖之间》(刘宾雁,1979)那洪钟般的急鸣。大约这跟作家处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缘故有关吧。于此话题,不是仅仅只希望南方出几个理由、陈祖芬式的大家,而是认为:我们的政治气候和文学气候还不是完全民主的,又由于这种不完全导致了一种政治上的南北不平衡,因而造成了报告文学总格局的北重南轻局面。
很显然,正是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使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在北方蔚为壮观,这与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引进和兴起出现在上海具有同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相似的文本语境。这就决定了重大题材(如改革)为重心的虚构文学在北方勃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发其端,此后随时间的推移又有: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1983),柯云路的《新星》,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1982),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一系列在全国引起震动的作品问世。虽然南方也不乏佳作如水运宪的《祸起萧墙》(1982),但总给人“小家碧玉”之感,而无“关西大汉”之慨。像张洁这样一个以细腻手法写女性的女作家,在《沉重的翅膀》(1981)里也表现了气吞如虎的气势:“让我们从这个普通人这句朴素的话里,得到超度吧:——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明政治气氛对文学有多么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文学的南北差异反映在这一点上也是很突出的。李洁非、张陵曾谈到上海文坛的“小家子气”(《当代文艺思潮》1985.6),我以为,这种“小家子气”是与南方处在非政治中心有很重要的内在联系。
五
“文革”后十年文学,虽然依有坎坷但却实实在在地可以说得上是“辉煌的十年”。从八个样板戏和少得可怜的《千重浪》《金光大道》《浦江哨兵》的文学荒漠里走出来,更因开放国策让国门打开,“十年文学”迅速地走上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与此同时,无论题材还是文本,呈现出全方位拓展的态势,以及取得了与“二十八年文学”不可比的业绩。文学的南北以其不同以及差异,共同开辟出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学新局面。在这一进程和趋势中,无疑,文学的形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形式的革新上,我们清楚地看到,北方要比南方活跃许多。王蒙以他横溢的才华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接二连三地推出《夜的眼》《风筝飘带》《说客盈门》《杂色》《高原的风》……这些作品一方面在内容上把文学从庸俗社会学上拉回到人自身,在韦勒克·沃伦看来,真正提示人物返归自身的内心活动是“小说的伟大贡献”(《文学理论》24)。王蒙这一时期的作品,正是这一返归的表征。而且,这些作品的另一方面是为这些小说的内容找到了寄身的形式,或者说正是王蒙有了这些“光怪陆离”“目不暇接”的形式,才使“返归自身的内心活动”(《文学理论》24)找到了最易表现的形式。王蒙的小说对新时期文学的重大影响不只是前者,更重要的还是后者,即王蒙的小说通过表现形式换取价值观的变化。南方文学里像这种寻求外在形式变革和多样的就鲜见。八十年代初中期兴起的纪实小说,也是由张辛欣、刘心武等北方作家建立的。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纪实小说,同样为新时期文学拓展了一角新领地。
1985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百舸争流各树一帜的一年。这是十年文学继1979年、1980年后又一里程碑的年轮。在这一重要年轮里,北方异常活跃,如《透明的红萝卜》(莫言,1985)、《活鬼》(张宇,1983)……这些除内容即题材新颖外,形式也特奇怪。其中两部算得上惊世骇俗的小说是《你别无选择》(刘索拉,1985)和《无主题变奏》(徐星,1985),其小说先锋性(由此,“先锋派”一词不胫而走),标识了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由隐形到显形。虽然上海的陈村写过类似《你别无选择》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和《美女岛》(1985),但不知什么原因,南北的评论界竟保持一种令人不解的缄默,而让北方的刘索拉们出尽了风头。我想,这跟北方文学在革新(观念的革新首先表现在方法的革新上)上的敏感和活跃有极大关系,虽然南方也不乏文学革新的勇士,如上所举的韩少功、陈村,还有何立伟等,但终不及北方的声音那么响亮。等1985年中国当代文学爆发后,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十年,苏童、余华、毕飞宇等南方才俊才走上了与之北方作家颉颃比肩的路程。
(南方写作的弱势,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或者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网络写作时代,才改变了北方开风气南方跟风的趋势。)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差异呢?新结构主义者吕·戈尔德曼在其著名论文《文学艺术在先进文明中的反叛》中指出,为了制止“人格和个性的削弱”,文学便出现了反叛,一面是“找出新的表现形式”的反叛,一面是“作品内部的反叛”。(《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96—97)在戈尔德曼看来,“形式的反叛”“极为重要”(同上)。这是因为形式的反叛(即广义的形式的革新)虽还谈不上是一种实质性的反叛,但它却是一种最具有可感性,最易使接受者得到刺激从而对旧的模式产生反感的显形的反叛。那么,北方的这种反叛为什么比南方强烈呢?从上面我们已知道,在北方,一方面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产生的保守性,一面又因政治中心带来的改革性,这两种势力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于是使新的东西在冲决旧的东西方面表面得更为坚决,以至于出现像戈尔德曼所说的使这种形式变成了“一种拒绝艺术”(《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101)。这种状况反映出人作为“单个的人”的主体意识的不同心态。这种反叛也可表明文学本质的一个层次,即它既可能是政治的传声筒(在中国当代的文学语境里,这是某种必然的情状),但文学终究成为文学,毕竟不可能是政治的单一传声筒,而是用语言符号固定下来的审美主(个)体的精神产物。如果说文学一开始还是“模仿”(亚里士多德语)或仅仅是劳作后的感情宣泄,那么文学到了成型期(如中国的《诗经》期和古希腊的悲剧),文学的反叛便逐渐形成了。即使政治再清明也如此,因为人本身(或许还包括社会在内)是一个永远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于是便导致了艺术拒绝“统一”,进而产生出反叛的本能。南北文学的差异,以及差异带给南方写作的弱势,事实上也在证实这一点。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