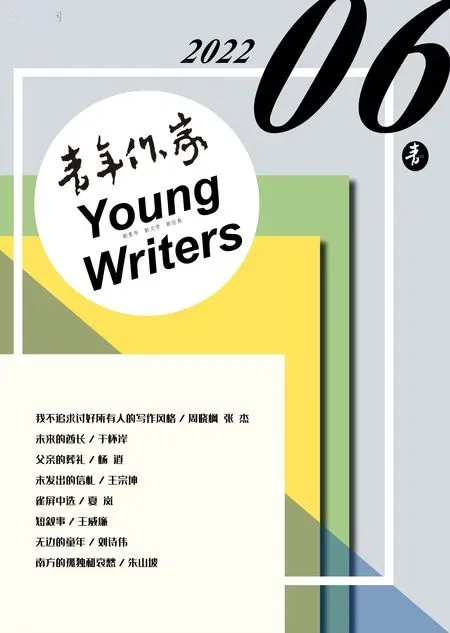主持人语 这也许正是“新南方文学”要正视的症结
贺绍俊
不出所料,这场讨论会有好戏。本期上场的三位作者全是南方人,且听听南方人是如何解读“新南方文学”的吧。
我好久没有在文学圈里看到刘火的身影了,大概是“新南方”这几个字眼勾起了潜伏在他心底的痒虫了吧,因为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界,他可是一名叱咤风云的人物。我相信无论他后来去干什么了,批评的情结一定不会消失。果然这回他一挥笔就写下了万言的文章,而且正是以当年他曾深陷其中的1980年代的文学为言说对象。他自称这是一次文学的考古,他的文学考古一直上溯到《诗经》时代。他强调了地域所带来的文学差异,主要不是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而是政治文化在地域中的权重。我很佩服他作为南方人却丝毫不给南方留情面,直言“南方写作的弱势”。
或许谦虚、低调是南方人的共同特点吧。因此,作为南方的一位优秀小说家,朱山坡在描述南方时也不吝使用令人沮丧的词语,他以自己的家乡为例,在他看来,南方人都有一个向北去的心愿,因为“北方是中心,是正统,是广袤,是无穷的坦途。”这一点倒是与刘火的关于政治文化权重的立论有一种互证效果。但聪明的朱山坡其实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他最终要证实的是:“跟真实的北方对比,我还是觉得南方更美丽。”在他这篇短文里,不乏严肃的反思,他总结自己的文学是:“用南方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并尽可能转换成北方规范化的语言乐此不疲地讲述,向你们描摹南方的模样。”这是否便是南方文学的共性?是否也正是“新南方文学”要正视的症结?
刘起林以他的锐利的理论眼光发现了“新南方文学”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在他看来,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文明转型的历史趋势在文学上的反馈。他由此提出一个区域现代性问题。他认为,地域的差异不仅由地理和文化所决定,在全球化时代,更由现代性所决定。在他阐释了南方的区域现代性特征之后,便赋予“新南方文学”足够沉甸甸的历史担当,他说:“‘新南方文学’命题的思想实质,则是对又一种文明转型形态、又一种区域现代性的审美塑形期待。换言之,中华文明转型的地方路径和区域性特征,才是‘新南方文学’审美形态与意义建构的基础和背景。”这位来自南方的年轻学者对南方充满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