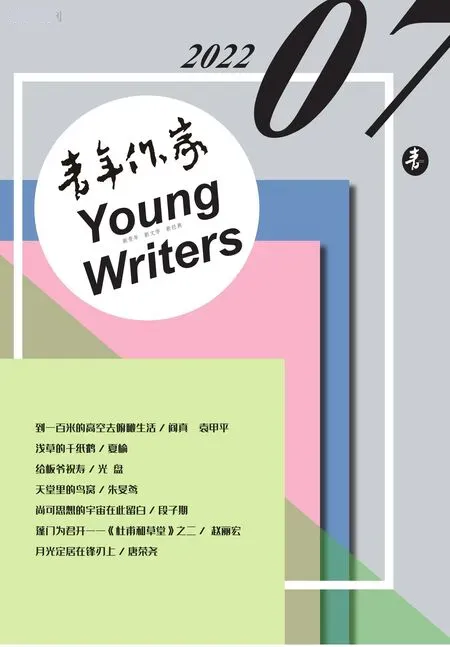牛录往事
郭晓亮
外公家距离牛录最北端的果园走路只需要二十来分钟。连接它们的是一条落满新鲜牛粪、马粪的横穿牛录的大马路。四月的最后一个早晨,我的苏花表姐由南向北走在这条马路中央。她身上穿着具有那个年代标志性特征的一身绿装,腰间扎着宽腰带,小小的个头,长着一张粉白的圆脸。当她迈着碎步向前走去时,头发后面的两支小辫子,一甩一甩的,煞是好看。苏花表姐这一年满十八岁,她中学毕业下乡来牛录接受再教育,被生产队分配到果园里劳动。果园里不但生长有种类繁多的果树,而且在果树下面的地里,还种着西瓜、甜瓜、梨瓜一类作物。果园的四周有着近两米高的干打擂土围墙,春天的这个时候,越过围墙,远远地就能看见,果园里开满白色、粉色或者是桃红色花朵的那些杏树、桃树。它们成排成行,列成队列郁郁葱葱地出现在走向它们的人的视野中,分外赏心悦目。今天是苏花表姐去果园参加劳动的第一天,为了给在果园里劳动的生产队其他社员留个好印象,她特意穿成现在这个样子。它们至少在那个年代看上去,显得十分的时尚、活泼、干练。当然,从南疆大城市喀什来到地处边远的牛录,接受农村生活对苏华表姐而言,完全是自愿。因为在当时,她是响应号召走出校园的。作为千百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表姐坚信:走出校园,走进乡村就是人生美好的开始。如今她抬头挺胸走在这条散发着牛粪味、马粪味以及尘土气息的牛录的大马路上,已经预感到自己正一步一步在迈向那理想中的广阔天地了。
晚饭后,苏花表姐坐在葡萄架下面的小板凳上一直在唱歌。我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但觉得她的声音好听。我用右腿支撑着自己,把身子斜靠在大院尽头的栅栏上,一边听她唱歌,一边吃着手里的苹果。有几只麻雀停在牲口棚的草垛子上,在瞅着我。一只麻雀飞下来,钻进牲口棚里边的鸟窝里。在苏花表姐唱完第四支歌时,天色朦胧下来,穿在苏花表姐身上的短袖花衬衣,因暮色而显得更加好看。我扔掉手中吃剩的苹果核,走进外公家的屋子去,也取了个小板凳,绕到葡萄架的另一头,坐下来继续听苏花表姐唱歌。“过来呀!小亮,干嘛坐那么远呢!”苏花表姐突然大声说起话来,要我坐到她身边去。我提着凳子走过去,静静地坐下。我听到苏花表姐在咯咯地笑,她一脸开心的样子。“你喜欢听我唱歌吗?”她问。“喜欢。”我说。“能听懂唱的什么吗?”她又问。我摇摇头。她再次咯咯地笑起来,而且笑着从坐的地方站起来。我觉得她笑的样子也好看。笑声停止了,苏花表姐哼着曲子,展开双臂,开始摆出舞蹈的动作。她在那里哼着曲子慢慢跳起来,她的花衬衣,随着她在转动,我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如同一枚柔软修长的羽毛在飘逸、在绽放。天色完全黑下来了,夜来到葡萄架下。夜经过苏花表姐的脸、手臂、哼着的曲子,遮蔽了我的视线。现在,我只能盲着双眼,听她舞蹈了。啊,长长的夜,在那个地方快速生长着,生长出它全部的黑暗。
通向果园的那片天空远远地敞开着,月亮和世界隐身于牛录下方的黑暗中。夜鸟飞过的风呼呼作响,我的一个耳郭探进风刮过去的黑暗里,倾听树林中发出一种陌生的声音。那里有一扇窗户,忽闪忽闪地从果园里透出一束灯光。灯光向黑夜环视,树林变得更加昏暗了,离开果园近一点的乡道上,有一个人影在走。现在已经是秋天,天气依旧很热,夜深时难以入眠的两个女孩,正静静地坐在果园的土屋里。一个女孩手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读着,另一个女孩面对面坐在木板床边织毛衣,掉到地上的毛线团不停滚来滚去,滚进了床下边的黑暗里。“歇一会儿吧,苏花。”织毛衣的女孩抬起头来冲着对面的另一个女孩说。叫苏花的女孩合上书静静地瞧着窗外,果园里一片寂静,不时有一只蝙蝠从窗前横飞过去,划过空荡荡的夜空。“今天是我来一牛录果园劳动的第60天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苏花看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从她的眼神中能看出来,她的思绪已经飘向远方,她在思念远在南疆的父母。“苏花,你都记着呢,想家了吧?”织毛衣的女孩说。“有一点。有一点。”苏花柔声细语地说,声调低低的,多少有一点凄凉的感觉。“你可以向大队请个假,回家看看父母。”“是的,我准备过了八月就请假回一趟家。”就在说话的当儿,苏花听到屋外有嚓嚓的脚步声,脚步声贴着地面清晰地传过来,苏花机警地挺直身子看向那里。但是,夜幕像一面厚重的墙挡住了她的视线。除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一切都是黑洞洞的、静悄悄的。“梅芳,我听到有人走过来了。”苏花回过头来朝织毛衣的女孩说。“真的吗?这么晚了什么人会来呢?”织毛衣的女孩起身靠近苏花,俩人一同望着屋外。随着心跳,嚓嚓嚓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黑暗中终于出现一个男人的轮廓,男人迈着八字步不紧不慢地走来。“是民兵队长佟林,好像还背着枪呢。”叫梅芳的女孩子口对着苏花的耳朵小声说。“夜里他来果园干什么?”“是来巡逻的吧。”“以前不都是白天来的吗?今天怎么夜里来了?我有点讨厌他。”“我也是。自从他当了民兵队长,整天背着一支枪在女孩子周围转游。”说话间,一个男人的影子走到了屋前,果然是民兵队长佟林,右肩上背着那支长长的步枪。他在屋外停了一会儿,从肩上取下步枪伸了个懒腰,又朝前走了几步,咚咚咚地敲门了。
门被向外推开了。黑魆魆的夜和一个男人的影子涌进屋内。站在明闪闪的灯光中面对两个女孩直逼的目光,民兵队长佟林多少显得有点紧张和不知所措。他先是把手中的步枪立在靠门边的墙角,又迅速地整理了一遍扎在腰间宽皮带下面的衣角,然后满脸通红地冲着苏花和梅芳张开嘴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来。“佟林,这么晚了你来果园干什么?”梅芳带着不欢迎的口气询问道。“我在巡逻,过来看看你们。”佟林的表情不太自然。“有什么好看的,我们要睡了,你走吧。”梅芳的声音尖尖的,音量十足。“让我坐下休息一会儿不行吗?我口渴了,请给一碗水喝。”佟林犹犹豫豫地说,并且用眼睛扫视了一遍屋子。这是一间坐南朝北的土房子,南面墙的中间位置有一扇大窗户,紧挨着窗户的两边各放着一张床,苏花和梅芳就站在窗户的前面。佟林瞧见屋子里面正对着窗户的墙边放着一把椅子,便走过去要坐下。“谁让你坐下了?我已经说了我们要睡了,你赶紧走吧!”梅芳气呼呼地赶过去叫住了他。佟林显得十分尴尬,身子被地面吸住了似的僵持在那里。“算了吧梅芳,让他坐下。”苏花心软,不忍心立刻赶佟林走,她走出屋子从外面端了一碗凉水给佟林喝。“还是苏花妹妹好!”佟林笑嘻嘻地说着,接过苏花手中的碗将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精光。这时佟林已经坐到那把椅子上,脸上还堆着未散尽的笑容。苏花和梅芳都不再理他,各自坐到两边的床上分别看起书和织毛衣。三个人就这样默不作声地坐了足足有十分钟,显然佟林心里也清楚现在两个女孩都不愿理自己,但他又不甘心马上离开。于是取过来立在墙角的那支步枪,坐在椅子上玩起了它。他不停地拉开枪栓又合上,弄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而且枪口随着摆弄转来转去,不时地对准坐在床上的两个女孩。“佟林,不要在屋里摆弄枪!要摆弄到外面去!”梅芳大声冲佟林喊,并且站起身躲开了枪口。佟林并没有立刻停下,只是动作幅度稍稍小了一些。“苏花,快离开那里!枪口老是对着你呢!”梅芳高声唤着苏花。苏花这才合上书本要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候,“砰”的一声,佟林手中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发出可怕的声音。枪走火了!刚从床沿半站起身的苏花,尖叫了一声便痛苦地倒在床上。躲在另一边的梅芳霎时完全给吓呆了,大张开嘴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风从指尖上滑过去,带走了牛录的夏天。一只蝙蝠紧贴着房檐飞过,在我的视野里留下空洞洞的夜晚。草丛里的蛙鸣消失了,一动不动的白杨树站在我走过的小渠边上,白杨树的叶子随着我的脚步在飘动。我的身旁还有风给村落上方吹来的土地气息。我感觉到我的身子很轻,轻得仿佛没有了骨架和肉身在走路。又长又弯曲的土路,我看不见自己的影子,也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我的呼吸把我带到了村边的一排房子前,这里有大片的阴影和乱糟糟的狗叫声。阴影中一盏马灯被一只手点亮了,灯光照出了由一匹马套着的一辆两轮马车,马车上躺着痛苦呻吟的苏花表姐,苏花表姐的身上盖着一床被子,被子上面有大块鲜红的血迹。马车周围人影晃动,一张张表情极度紧张的脸,我看见大哥和二哥,以及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大队民兵队长富林,另一个是木邓保的三哥木力克。二哥的手中牵着马的缰绳,民兵队长手提马灯垂头站在马车的另一边,大哥和木力克坐在马车上一左一右扶着苏花表姐的身子。二哥使劲拽了一下缰绳,马拉着马车开始快速向前行进。马车顶着死黑的夜色行进,满是车辙的石子路,我的影子静静地跟随马车移动。抛在后面的乱糟糟的狗叫声渐渐远去,马车走过了一户又一户人家,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路口,很快从一牛录走进三牛录地界。我的影子静静地跟随马车移动,我的目光盯着躺在马车上的苏花表姐的身子。我能想象到那里有一个疼痛的深渊,我能感觉到它的深度,它像旋涡一样包裹住了苏花表姐娇小的身子,死亡在一步步走近。死亡的前头是一盏马灯颤颤巍巍地跟着踉跄的时间走向夜的深处,夜是那样的死寂和空茫。
大哥额头上的皮肤在颤动。汗珠从那里一粒粒冒出来,顺着脸颊向下滚落。“坚持住!苏花妹妹。马车很快会把你拉到六牛录的,六牛录有县上的大医院,你的枪伤会被救治好的。”坐在马车上的大哥俯下身子,脸对着苏花表姐在安抚。苏花表姐脸色苍白,嘴中不断地发出呻吟声,而且伴随马车的加速行进,呻吟声在加剧。她的一双眼睛一直睁着,有几次冲着大哥说:“我要死了吗?我不想死啊!”马车在笔直的乡路上行进,路两边是连片的玉米地,民兵队长佟林手提着马灯在前方引路,二哥手中紧紧地抓着缰绳专注地驾着马车,车轱辘的每一次转动都揪着他的心跳。二哥努力地把马车赶得平稳些,再平稳些,以减轻因马车颠簸给苏花表姐带来的痛苦。架在车辕里的马是一匹枣红色母马,马的鼻孔里不时发出噗噗的响声,听上去好像在打喷嚏。夜幕中有股气流,忽前忽后地围着马车流动,给人一种不祥的幻觉。我的影子依旧跟着马车移动,像条甩不掉的尾巴。这时前方传来汪汪的狗叫声,狗的叫声提示我们前方就是四牛录。黑乎乎的玉米地尽头出现了高高的土城墙,城墙下面立着几间房子,马车赶到时一只大狗跑出来发疯似地狂叫。人和马车继续前行,穿过了四牛录的城门,然后又穿过了沉睡的四牛录。“富林,快把马灯提过来!”这时马车上的大哥朝前边的民兵队长喊了一声。马车停下来,民兵队长佟林小跑过来,把马灯举起交给车上的木力克,木力克接过马灯照在苏花表姐的脸上。苏花表姐的双眼紧闭着,她的脸不再是惨白惨白的了,而是变得铁青铁青,而且整个身子在不停抽动着,每抽动一下她的嘴里都要传出呼呼的声音。“苏花妹妹,苏花妹妹,醒一醒!你睁开眼睛看元儿哥一眼好吗?”大哥双手抱着苏花表姐的头在喊。喊声从马车上方传过去,在黑茫茫的夜空中传向旷野的深处。
马车周围全是夜的深渊。夜无法愈合的伤口也在流血,大面积溃烂。僵硬的道路和无边无际的秋夜,死亡又向前靠近一步。大哥的喊声终于使苏花表姐慢慢地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但是她的呼吸是那样微弱,微微张开的嘴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过了半晌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一句:“我……不行了,你们……把我……送回……去吧。”大哥终于抑制不住悲痛哽咽起来,眼泪扑腾扑腾地往下掉,他轻轻地用双手抬起苏花表姐的头,放在自己的怀里,泣不成声地对木力克和二哥说:“人已经不行了,怎么办?六牛录还远着呢,继续往前走吗?”木力克伸手摸了摸苏华表姐的两只手和脚,发现都是冰凉冰凉的,他摇了摇头说:“是不行了,不能再往前走了,那样会让苏花受更多的罪。”二哥则发愣似地站在马车旁,一个劲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民兵队长富林开始全身哆嗦,已经瘫坐在地上,全然像瞬间枯萎了一样。这当儿,先前那股前后转着圈在马车四周窜动的气流,已经停止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夜顿时变得万分沉闷、压抑,让人透不过气来。脚下的大地仿佛突然间像陀螺似地转动起来,而且转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这让受到惊吓的我,感到毛发耸立,毛孔全部张开了,太阳穴上的血管也都鼓起来,扑通扑通地跳动。是的,在这个时间里,一切都变得令人窒息和绝望。经过内心一番极其痛苦的争斗之后,大哥使出全身的力量向二哥摆摆手,说:“回去。”二哥拽住缰绳让马慢慢地掉转身子,马车在乡路上原地转了个圈,开始往回走。深深的夜幕中,躺在马车上的苏华表姐的身子在变小、变小,小到渐渐地变成一个黑点,看不见了。
夜静得可怕。黑暗中只有马蹄和车轱辘在路面上踩压出的响声。我看不见脚下的路面和土地,但我能闻到一股阴阴的死亡味道。乡野是古老的,庄稼地被黑夜淹没了。四下里飘动的是黑乎乎密麻麻的死亡的影子。当马车再次穿过四牛录时,苏花表姐的呼吸完全停止了,她离去时的面容和神态很平静,如同刚刚睡着了一样。大哥依旧在怀里紧紧地抱着她的头,并用一只手轻柔地抚摸她的脸。“好妹妹呀,怎么说走就走了?”木力克终于按捺不住,双眼含着泪花说。他把身子猛地转向前方的佟林,伸出右手指着佟林吼着说道:“佟林!都是你害死了苏花妹妹!当了民兵队长很了不起,是吗?你成天拿着一支枪到处炫耀。如果不是你他妈的夜里在果园里玩枪,那枪能走火打着苏花妹妹吗?”佟林黑黑的身子提着马灯,直呆呆地走着,沉得像一根木头。马车行进三牛录地界时,牛录的公鸡开始三三两两地叫了,这时大哥挪动身子,把苏花表姐的头轻轻放下来,放在起先枕着的枕头上,接着和木力克携手把苏花表姐的身子在马车中间摆正、摆平,这个时候苏花表姐的眼睛是睁着的,大哥用手掌缓缓地抚闭了它们。
在一个陌生的黎明,你不用心看或听,就能感受到你周围发生的事情。当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看见一群男人簇拥着一辆马车走进外公家大院时,惶恐和绝望便已经牢牢地占有了你的内心。在这个黎明,首先打破平静的是女人们的哭声,外婆、二嫂和街坊几个姨姨辈的女人迎着马车撕心裂肺的哭声,很快冲出院子,传向牛录的每个角落。哭声引来更多的族人,他们络绎不绝地走进外公家的院子,个个表情凝重悲伤。尤其是女人们赶来时,都要先进屋去探望外婆,然后在里面哭成一片,我在院子外面能听见她们谈话和走动的声音。门板一直咣当地响着,谈话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如同无数布条撕碎的声音,带给你浑身针扎般的痛苦。男人们进了院子就忙了起来。他们和大哥、二哥一同,很快在长廊一样的葡萄架下七手八脚地用长凳和木板搭起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平台上铺上了干净的褥子枕头,苏花表姐被抬到平台上,然后男人们散开,退到院子的另一头。屋里的女人们出来了,外婆带着她们开始给苏花表姐擦洗身子,哭声再次响成一片。“苏花啊!你小小的年纪怎么说走就走了?往后的日子叫我如何受得了!”外婆一遍遍重复地说着这句话,说着说着突然一阵眩晕就要倒下去,幸好有大姐搀扶着才没让她倒在地上。外婆依旧坚持守在苏花表姐的身边,女人们擦洗完身子给苏花表姐穿上新衣裤和鞋子,整个过程庄重而肃穆。之后,女人们又给苏花表姐的脸上盖上一块白布,身上盖上一大块黑布,然后都静静地守在一旁,等着给死去的人出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