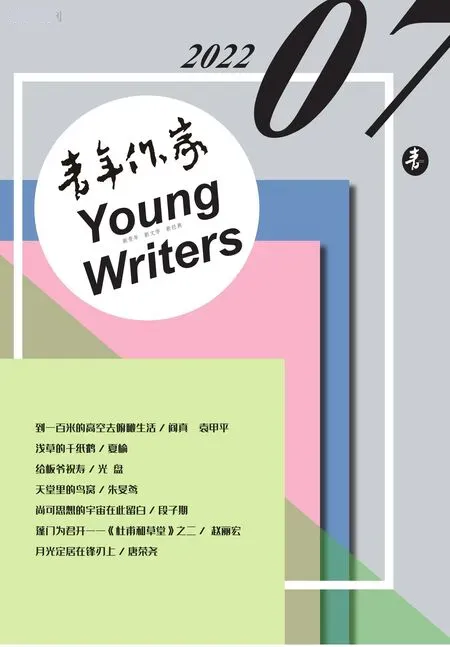月光定居在锋刃上
唐荣尧
吐尔迪的身份是一个在吐鲁番火车站“钓鱼”的“骑手”。在他们的行话里,“钓鱼”就是等待客人上车,“骑手”就是用摩托车载人。
从火车站出来,我一眼就看见吐尔迪的腿斜挎在摩托车上,眼睛像一部工作着的雷达扫描着车站出站口,等着属于他的客人。我的红色冲锋衣和背包,一定让他立即认定,我是他的“鱼”!
“你的嘛,哪里的去?”别的“骑手”还没反应过来,吐尔迪像个兔子一样敏捷地跳离摩托车,跑了过来!
我试探着和吐尔迪开始交流:“知道他地道么?”
“他知道?”吐尔迪迷茫但迅速不屑地向不远处那几个同行看了看:“这里的事情嘛,得问我,吐鲁番还有我吐尔迪不知道的吗?”
“是一个古代的道路,叫他地道!”我拿出自己手绘的地图,描述我要去的“他地道”线路!看着看着,茫然和歉色像上午越来越浓烈的阳光,爬上吐尔迪的脸。他从我的手绘图上看出了点门道:“要经过你说的他地道翻天山的话,得先到大河沿。”
手绘图是我根据敦煌藏经洞的《西州图经》里这几句简单的记述描绘的:“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我研究手绘图的时候,吐尔迪在旁边打电话,叽里咕噜的民族语言我听不懂,只是隐约地听到他断然而命令式的口气中有“汽车”等汉语词汇。不到20分钟,他就指着一辆驶来的小轿车说道:“这一下子,我吐尔迪的摩托车失业了;到大河沿100多公里远的路,要找个力气好的车子才行!”
我警惕且不解地问道:“力气好的车子?我们现在所在的火车站不就叫大河沿么?怎么还去大河沿?”
“力气好的车子就是汽车。我们这里有三个大河沿,这里是大河沿的爷爷,是能装下火车站的地方,叫大河沿镇;不远处的大河沿村,是大河沿的爸爸;你要走的‘他知道’经过的一个山沟沟,才是真正的大河沿。”
火车站前嘈嘈杂杂的人流中,我和吐尔迪互相选择了对方!开始了我们的“他地道”之行。
一
在红星农场,我告别吐尔迪,开始向天山走进。
海拔3600多米的琼达坂,犹如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竖在天地间,一直是我前行的一个巨大标识。2000多年前,它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达坂南北分别是属于车师国的南北两个小国,属地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和昌吉州境内;2000多年前的那支远征军,就像一段段精彩的、或长或断的句子,连接着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这两篇分居于天山南北的文章。
走在寂寥的山路上,没有想象中的田鼠、狐狸等动物,只有从山谷里如流水冲来的风的声音。2000多年前,那支军队就没有我这样轻松、休闲的旅行心理,他们沿着险要而隐秘的“他地道”,怀着警惕和信心:警惕源自对潜伏在山林敌军的忌惮;信心源自对自己国家的实力信赖。警惕与信心的交错,就像眼前这云与树、天与山、水与草、土与石的交错。翻越达坂、跨入北车师时,那些军人一定亦如我这样静悄!我的静悄是没人愿意陪我,如此辛苦地寻找一条对很多人来说毫无意义的废道;他们的静悄是出于军事策略,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敌方的警觉。
“他地道”是连接天山南北两个车师古国的一截肠子,在古老的史书和现在的旅游指南中,被称呼为“车师古道”。古道像一条收留岁月的皱纹,深深地刻在天山额头。那支远征军的每个军人的头上都飘荡着一朵写满艰难的云,艰难不仅体现在行程中山路的弯曲、海拔高带来的缺氧、植被渐渐稀少容易暴露,还有他们即将进入敌对势力的监控范围内,没有人知道死亡和下一个时辰哪个来得更快。
水会寻找自己的力量。山顶的积雪是溪流的源泉,顺山而下,逐渐接纳了越来越多的溪流,汇聚的过程便有了一条小河的流量、体量和气势。寂静的山谷因水有了随海拔依次降低而出现的名字:从六道桥到头道桥,像六个坚守岗位的哨兵,依次排立在幽深的山谷,头道桥附近的石崖上,四个褪色的大字“车师古道”楔入海拔2000米的灰白色岩石上,这意味着我从高处的大坂行到头道桥,完成了1000多米海拔落差的下山路途。山林中,不时遇见哈萨克族牧人骑马的身影穿梭在林间,炊烟般轻柔地穿行在林子深处,他们努力地把延续千年的世俗生活图景清晰而有力地镌刻在天山的记忆里。
“车师古道”曾连接着车师前、后两个小国,早就消亡了,但古道两端世居于此的两个古老部族如琼达坂上的积雪,一直生活在这里:古道南端的吐鲁番境内,以维吾尔族为主;古道北段的昌吉州境内,哈萨克族牧民主要居住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他们会在夏天赶着牛羊,赶着一份诗意和未曾丢弃的传统,向天山深处和高处的夏牧场而去。像一艘艘被拴在靠岸水里的小船,被季节之浪一次次推着,来回游荡于夏牧场与冬牧场之间,给古道上往来的商旅提供一杯热茶和道路的资讯。
二
吉木萨沟,是“他地道”在天山北麓的一段。刚走出吉木萨沟,一片开阔地上立着一尊骑马军人的雕像。雕像的原型或者主人,在2000多年前也和我一样,是从天山南麓翻越“他地道”而至此的,他是那支远征军的领队与灵魂,而我,是时隔2000多年后他的追随者。
头顶是一轮生铁般冰冷的天山月,我一个人慢慢踱向那尊塑像,静静立在塑像前,内心再次温习史书中有关塑像主人的记述,它们像一座座移动的岛屿向记忆的彼岸靠拢。
2000多年前的故事,像一艘小船被历史巨浪倾覆在时光的大淖中,沉睡的时间长了,打捞、梳理就成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既需要翻阅资料,更需要实地调查!知与行的坐标处,是对塑像主人及其同行者一起缔造的故事大厦的追溯与描摹。
公元74年春天,汉明帝再次组建了一支一万四千名精锐骑兵的远征军,这是汉朝第二次向遥远的西域派出远征军队,旨在清除匈奴在天山一带的残余势力。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官为奉车都尉窦固,副将为驸马都尉耿秉和骑都尉刘张为,耿恭担任司马,跟随这支部队出征。
朝廷一声令下,催生了一部战争大片的所有元素:长途出征前的精心谋划、征集粮草时的紧张有序、将士们和亲人告别的泪水;接着是猎猎旗帜开始飘扬,将士们开始对远征之地的各种想象甚至不乏取胜还乡后的荣光与羡慕。
走过平原、戈壁、绿洲、山地,远征军警惕万分地接近天山,战争开始了,但不是大规模的对阵,而是遇到偷袭之敌的反击与搏杀,埋葬同胞时的感慨与情谊;再然后,这支军队沿着“他地道”穿越天山,出现在天山北麓今吉木萨尔县地界,他们开始快速筑城,以城来抵御匈奴骑兵的一次次进攻。
耿恭所在的这支远征军抵达天山北麓前,一个词已经成了汉廷的噩梦:姑师!这是一个被史学者称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姑师像一张保存着完整地图的羊皮卷,西汉派出的第一支远征军,像一把匕首,一道寒光划过,羊皮卷被划得七零八落:姑师被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及山北等六国。车师前、后两国就像一对孪生兄弟,跨居天山南北。姑师的王权被一条山脉切割,车师前、后两国的底层民众,依然保持着来往,在天山深处踩出了一条交易古道,道因国名,这便是后来人说的车师古道!
亲爱的读者,这时该惊叹出一个“哦”来。我从天山南的吐鲁番开始寻找的“他地道”,一路而来,脚下其实就是这条车师古道。如果说那时的新疆大地是一个棋盘,一条隐秘的小道竟然以“车”之师命名,可见其大气与重要。没错,那是一支有车(读 ju)之师,翻越天山时,他们舍车牵马而行;他们在枯燥且危险的行军途中,安住下来的空隙里,或许会拿出象棋来,下棋者静默于对方的打量中,旁观者七嘴八舌指点三四;或许,史官因为这样的远征而将他们穿越的古道,写成了“车(读 ju)师”?汉代的烟云早已散去,但古道的名称保留了下来。
三
耿恭所在的远征军收复了天山北麓的车师后国,车师古道再次恢复:军人、信使、商旅再次出现在古道上。汉明帝下令,耿恭担任驻屯于天山北部的戊己校尉,驻师于他带人修建的那座带有防御性质的简易城池:金蒲城;天山南部的戊己校尉由关宠担任,驻屯于车师前国的柳中城。天山像一个驼背,金蒲城和柳中城成了汉朝挂在这个驼背两边的褡裢,里面装着沉甸甸的重任。
耿恭驻守在金蒲城时,西域脱离汉朝的实际控制已经达数十年之久,汉朝在这里的影响力如秋草般孱弱,对这支远征军而言,万里跋涉至此,无疑是一场冒险。然而,那个血性贲张的年代,从军且赶赴西域似乎成了一种个人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甚至时代品质:是对个人成功的定义,也是对国家情怀的体现,哪怕丢掉生命也值得。匈奴与汉,两种血性相遇在天山这个棋盘上,拉开一场实力和毅力、智慧和坚韧的博弈。
金蒲城很快被涌集而来的匈奴骑兵和野狼包围,小小的军堡完全符合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的名字:《胡狼嚎叫的地方》。狼的评判视野中,没有正义之师与侵略之军区分,只有强弱之判。或许,它们习惯了骑在马上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对远路而来的汉军气味是陌生的、警惕的甚至敌意的。狼群目睹了匈奴骑兵围城后,似乎嗅到了汉军在被围困日久后可能失败的信息。狼是有尊严的,是不会去吃死尸的,为了维护这种尊严,它们在等待着汉军快要支撑不住的那一刹那。白天,汉军要抵御匈奴骑兵的进攻;夜晚,要抵御另一种损毁毅力的侵扰:城外的草原狼号叫着,试图扰乱守军的睡眠。
攻城与守城,围攻与突围,双方的较量进入拔河般的状况。耿恭决定派人翻越车师古道,前往天山南麓的汉军驻守地柳中城求援。匈奴首领意识到:掐断外援求助的信息通道,是实施包围战的必要条件。匈奴的精锐骑兵,埋伏在古道的某个隐秘部位,耿恭派出的求援人员,全部遭到伏击。汉军的求救信息,一次次死于半道中。匈奴人始终没能掌握汉军的驻守实力及下一步的意图,汉军即便俘获,也是刚被俘就服毒、咬舌或互相刺杀身亡以免落入敌手。
宁死不愿被俘,这是那个时代的汉人风骨:有派往西域的使者张骞被俘后始终未降,逃命后依然不忘使命,返回汉地后开始第二次出使西域并开辟了一条伟大的丝绸之路;同样为使者的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多年,一直坚持不降。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有关气节的故事,更是那个时代的汉人标准。
时间变得慢了起来。金蒲城内,这支没有外援的汉军,一寸一寸地熬着时光,和匈奴骑兵、狼、饥饿、寒冷做着艰苦的对峙。
一轮冰凉的天山月,在圆缺变化中,冷冷地注视这场对峙!
匈奴人的攻城频率加快,耿恭下令让军中善射者给箭头上涂上毒药,然后走上城头,冲匈奴士兵喊话:汉军的箭神奇,一旦射中,会让你们生不如死。匈奴士兵自然不理会耿恭的喊话,继续攻城;中箭者退回军营才感到剧痛,继而伤口血流不止,血水像沸腾一般往外喷,史书中记载说“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匈奴军营中暗传着“汉兵神,真可畏也”的赞叹!
汉,一个连对手都敬畏的王朝,一个不仅在武器装备和生产技艺上领先时代的王朝,还引领着那个时代周边地区、邻邦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潮流,这才是支撑帝国旗帜高扬的重要营养,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容器。
四
匈奴军队失去了围城的耐心,撤退了。
耿恭赶紧带着部队撤离金蒲城,向西转移到今新疆奇台县境内、第一支汉朝远征军修建的一个军事小堡:疏勒城(不是现今新疆喀什地区的疏勒县),试图以这里为据点,继续和匈奴军队较量,匈奴骑兵很快又包围了这里。
春天来了,耿恭带领这支孤军看不到外援的希望。天山脚下,寒冷不好熬,酷热更不好熬。死亡的气息像长了翅膀的秃鹫,穿过夏日的骄阳直逼而来:匈奴骑兵切断了疏勒城中汉军的水源。一切外援被切断,连水都没了,考验汉军毅力和对国家忠诚度的时间到了。
耿恭下令掘地挖水。一寸、一尺、一丈,挖出的黄土堆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土坑像一条张着嘴的旱鱼,一直向外冒着热气!军心再次摇动,大家心里嘀咕:这里能找到水么?这时,马刚拉出的粪便,就会有人抢到手里,用嘴一嘬,榨取那可怜的一点水分,汉军出现“笮马粪汁而饮之”的情形。
耿恭的心里或许也没底,但他和任何一个优秀的将领一样,任凭内心波澜万丈,脸上写着大海般的淡定和平静,下令士兵继续往下挖。奇迹出现在到地下45米的刻度上:冒出的水挽救了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这就是唐代诗人王维《老将行》中“誓令疏勒出飞泉”的典故。
水的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依然像把剑,高高悬在这支孤军的头上。他们把弓弩上用动物筋腱做的弦和盔甲上的皮革等都统统煮着吃了,不少战士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这片陌生土地上,没有死于战争,却被饥饿夺走生命,但没有一个人偷偷出城去投降。
匈奴军队的眼里,困守孤城的这支汉军,就像一块硬铁。
疏勒城头,那面经过四月云、五月风、六月雪、七月雨、八月霜、九月寒浸染的军旗,被风吹得残破不堪,像一位宁死不降的将军,高昂着头颅,发出的豪迈笑声如一道道光束,照进幽黑的时间暗室,点亮了那支远征军的精神之烛。
底线还未出现,考验不断升级,匈奴首领以耿恭当他们的白屋王为代价,实施招降。惊人的一幕出现在那天的疏勒城头:为了提振将士的士气,耿恭不惜损毁战争中不斩来使的契约;那位招降的匈奴使者,被耿恭派人押到城头,当着城墙外不远处的匈奴人砍头。招降者的血被分进倒有酒的碗里。尸体被横在一个临时做的铁架上,铁架下堆满了天山的干松木,随着耿恭的一声令下。松木被点燃,熊熊火焰烧烤着无辜的招降者,也烧断了守城汉军的投降之路。
招降者尸体的焦味,被天山的风吹到对方的营帐里。匈奴的首领和战士亲眼看见耿恭和随从们端起盛有匈奴招降者血的酒碗,集体大笑着喝下那碗血酒,昭示了这支军队绝不投降的决心;烧烤招降者的那一把火,烧掉了匈奴人对这支军队的招降幻想。这件事发生的1000多年后,另一位汉室将军岳飞写下了千古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强敌与久困前,壮美与信心是展示给敌方的,而恓惶与不安的种子,只能在内心悄悄发芽。外援依然未到,粮食危机一天天加剧。匈奴人也似乎拿这支坚守的对手没有办法,他们在围城的牧帐里点火取暖,饮酒吃肉!双方的僵持,成了一场耐力的比试!
缺粮的危机还没解决,寒冷带来的危机随着第一场雪降临了,大地像一张白纸,等待着奇迹的书写。
疏勒城里,耿恭不知道, 八个月前,下旨让他们出征的汉明帝已经驾崩,18岁的太子刘炟即位后早就忘了先皇曾派出过那么一支远征军,整个朝廷似乎也将耿恭忘记了。不久前,天山南部的匈奴联军展开围攻,设在车师前国的西域都护几乎全军覆灭。这意味着唯一能就近援助耿恭的一支力量,彻底被匈奴人摧毁。
疏勒城,成了远悬于汉朝视野外的一处孤岛。
求援就是求生,耿恭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部将范羌,这是他在这场战争赌博中最后的一个筹码了。如果范羌失败,命运之风,会吹灭这支军队最终的一束希望火苗。
积雪越来越厚,似乎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坟场。耿恭和他的将士们还能熬过眼前的寒冷之冬吗?那时,有多少狼夜袭城中?有多少狼被汉军猎杀变成了度日的粮食?似乎,整个天山的狼都闻讯而来,奔跃在车师古道上,向古城四周涌来。或许,古道从那时便有了一个民间意味的名字:野狼谷,这个名字至今仍在叫,而且有个民间企业家建了一座狼园,里面养了几百匹狼。
穿越野狼群聚的天山深谷,该具备怎样的勇气?范羌是在求援信息屡屡送不出去、粮草断绝多日、狼群长嚎于夜伺机袭击汉军的绝境中,带着求援的最后希望,将穿越“他地道”。
雪成了最好的伪装,范羌和随从反穿羊皮袄,白色的皮袄融入雪地中,是几个白点融入一片白色的海洋中,那不是白马入芦苇的诗意,不是银盘盛白雪的浪漫,是借助死亡之色完成的冒险。在雪色和寒冷的保护下,范羌成功地溜出了疏勒城,古道被雪淹没,范羌只能凭借沿着古道来时的记忆,凭着本能向天山深处找路而行。2000多年后,我穿越车师古道时,即便是夏天,也能见山顶积雪,何况他是隆冬之际穿越的。何况冬天的狼是最缺食物的。
传统的史料中总是给帝王将相着墨很多,认为影响王朝历史走向的命运主角是皇帝与将相,其实,处于金字塔底层的那些人往往才是历史剧本的匿名作者,这些被搅动在历史齿轮上的小人物,常常被忽略。如果没有范羌这样的小人物,“他地道”上悲壮的一页或许就该重写或者空白了。范羌一行像几片逆行的雪花,从低处向高处攀升并成功地穿过了“他地道”。
站在天山南麓,范羌才知道,柳中城的守将关宠和守军早就集体战死。范羌和随从依旧反穿着羊皮袄,像几粒白色的盐,滚动在天山脚下的茫茫雪地里。他们让我想起这样的情景:几个扇动红色翅膀的蝴蝶,穿行在一片玫瑰花海中;几个时刻保持着警惕的蜥蜴,在茫茫沙漠中贴地而行;几辆破旧的绿色老解放牌汽车,穿行在茫茫林海中。他们以融入大地之色的伪装穿过了“他地道”,一直徒步到几百公里外的敦煌城。
敦煌守军将领的飞书抵达洛阳,朝廷才想起有这么一支军队被派往远方。朝廷围绕救援展开了争论,司空第五伦为首的一派认为,远征军要么被匈奴人收拾得尸骨无存,要么归降匈奴了,这样的事例在汉代又不是没有过。司徒鲍昱那段铮铮谏言回响在大殿:“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此际若不救之,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这段荡气回肠的话,飘进了皇帝和大臣的耳朵;多少年后,从史书中飘进我的眼里。一个守信用的王朝不能遗弃捍卫国家尊严的人,不能不救自己的英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英雄,决定了这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高度,也会决定其民众的忠诚度。鲍昱的谏言,成了汉朝援救耿恭率领的远征军的动员令,一场汉代版“不抛弃、不放弃”的拯救英雄大戏,在汉章帝的一道圣旨下启幕。
公元75年的冬天,范羌给集结于敦煌的7000名援军做起了向导,贴着天山南麓,向西快速出发。积雪掩埋道路,大地如纸,援军的脚印成了戳给天山脚下的印章。这印章盖得吃力,也清晰而有力。一个多月的行军后,援军收复了位于天山南麓的“他地道”南起点:柳中城。
望着身披一件白袍般的天山,援军上下无不嘀咕:山那边的疏勒城,是否失陷?耿恭是否也和关宠一样,战死于匈奴骑兵之手?分歧再次产生,很多人已经对山那边不抱希望了,这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冒雪踩冰地翻越天山了。范羌坚信,山那边的汉军,如一只濒危的狮子正发出临终前的脉息。范羌的呼吁响彻雪地:“愿意跟我去救校尉的,马上出发!不愿意的,可留在这里。”当场,有2000多士兵响应,他们踩着皑皑积雪翻越天山。
救援军急行的足印,像一把蘸足墨汁的巨毫,悬空挥洒于宣纸般洁白的“他地道”,歪歪斜斜地书写出一场汉代军人对同胞的救护传奇。
越过“他地道”,援军在疏勒城下看到这样一幕:为了阻止匈奴骑兵攻城,耿恭下令每天往城门、城墙处浇水,夜晚的巨寒立即将这些水冻成冰,一座光滑的冰城成功地挡住了匈奴骑兵,这意味着城里的守军也无法出去:这是一场赴死的守卫战。援军只好在城外点火,烧化厚冰。城门开启时,守军和援军“共相持涕泣”。对前者而言,这一滴泪,是一群军人为自己的尊严而流;对后者而言,是为敬仰真正的汉家骨气而流。步入城堡,援军比匈奴人更诧异:包括耿恭在内,死守疏勒城的,只有27名将士!这是度过200多个艰难日夜的最后守城者,将一曲“汉歌”高唱于天山脚下。开始,这支几百人的合唱团阵容庞大,耿恭是总指挥;最后,剩26人时,依然坚持唱完,耿恭依然坚持指挥:这场合唱,听众和观众都是敌人。
2000多名援军成功地拯救了27名将士的生命,随着他们的撤离,疏勒城由孤城变成了死城,死于历史记忆之中。
离开疏勒城的那一刻,耿恭勒马回首的刹那,坐骑突然一跃,天山的胸腔内回荡起一声长鸣,那如鼓槌般的嘶鸣,擂响了天山的鼓面;耿恭的枪穗迎风飘出天山下的一抹艳红,那是匈奴军队不甘的双眼瞪出的血丝,是死于此地的汉军将士的血色,是一位汉家将军书写的忠字牌彩虹,它定格成一种宣示:凡我疆土,必守不弃。在视国如家的军人眼里,没有一寸疆土是多余的!这种宣示,成了一面看不见的旗帜,红如云霞,流淌在后世代代视这片土地为祖国疆域的军人心里。多少年后,有了左宗棠在70岁时命人抬棺进疆,林则徐流放伊犁时不计个人荣辱投身当地水利建设;有了王蒙的《巴彦岱时光》、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茅盾的《白杨礼赞》、周涛的《阳光容器》、沈苇的《新疆时间》、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
两个月后,援军带领生还的远征军撤回玉门关。
五
尽管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在玉门关外迎接的中郎将郑众还是惊诧不已:远征军归来者,仅仅剩下了13人,个个“衣屦穿决,形容枯槁”。出玉门关时是7000男儿的庞大队伍,从疏勒城中撤离时剩27人,又有一半人或死于匈奴骑兵的追击中,或严重营养不良而导致体力不支死于归途!远征、守城、撤退的三部曲中,没有一名逃兵,只有这样的汉家儿男,才让其身处的朝代为后世军人立出一些标准。
玉门关的阳光照见两行泪从郑众的双颊流下,他连夜慨然上书:“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这段内容传入文学家范晔耳中,令后者心生敬意,在《后汉书》中称誉耿恭和前汉的苏武都是“义重于生”。这也是有汉一代一个将军和一个使节给后人树立的为臣、为民典范!
今天我们言己为汉人,其渊源更多是直指领受“汉”的一代影响,诸如民族识别是汉族、书写用汉字、说话是汉语,甚至穿的是汉服等等。至此,我突然领悟到,有汉一代,不仅为中国树立了汉赋这样磅礴大气的文体高峰,也为中国制定了一些隐性的公民标准,给家国精神划出了一个边界。我们赞许有节操重义气的男人为汉子,同样将背叛祖国的人斥为汉奸。我不知道后来闪耀于历史镜面的岳飞、文天祥等人,是否受过耿恭的影响。从这面镜子里,不难看到一个民族的骨体,是由这些“义士”增加钙质的,这面镜子,更需要后人时时擦拭上面的历史蒙尘!汉,树立了中国的魂魄与标准;唐,树立的是气质与精神,这一点,在“他地道”上演绎得非常精准,前者的主角是耿恭、范羌和汉军,后者是高仙芝、岑参和唐军,他们上演了两幕事关国家在西域声誉与影响的大戏。
耿恭带队远征、苦守,为后来的汉军重兴天山北麓并稳固都护府蹚出了一条路;大唐军队远征天山北麓时,同样踩着他走过“他地道”,让大唐的圣旨能够顺利抵达北庭都护府。
汉代的天幕上,征战者的辉光如星空闪耀。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班超、马援……一个个在马背上成就英名的将军,将光荣久远地留给闪亮的史册版面。披在他们身上的光环,远胜耿恭,但远征之远、苦守之艰,恐怕没有人超过耿恭吧!我们常常惊叹于世界战争史上的大城市的保卫战,往往忽略了那些在历史匆匆划过一页的小地方保卫战。疏勒城保卫战、金蒲城保卫战,汉代的威名或许不是靠这些小城守卫战成全的,正是这些一个个小战逐步积累出汉代的基业。两个小城保卫战,是耿恭挥舞的两面汉军旗帜猎猎作响于天山,那上面日渐厚起来的历史烟尘,或许让它褪色,如果认真聆听,你一定会听见它在历史的罡风中飘展出的响音。
撤离疏勒城后,耿恭返回洛阳,再也没能看到过天山之月。返回内地后,耿恭是否曾抬头西望,缅怀起艰绝苦守但心火蓬旺的远征岁月呢?他最后的人生结局是遭弹劾而被入狱免官,最终老死家中。天山,是他再也望不见的一缕香灰。
汉家将军的本色与骨气,让对手凛然起敬,却败北于史籍的遴选前:耿恭在天山北麓的这曲悲歌轻轻地闪过《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的逼仄角落,寥寥几句而过,以致后人对他了解甚少。站在车师古道北口,站在将军撤离这里2000多年后塑起的这尊雕像前。我只有默默地鞠上一躬。
我端好相机,准备给那张塑像拍张照片时,恰逢一个当地演艺团队给外地来的旅游团表演节目,舞台灯光给夜色中的将军雕像涂上了一层朦胧。我刚将镜头调整好,突然发现,一轮天山圆月恰坐在将军头盔顶端,稍一转角度,那月在枪尖上跃动。咔嚓一声,独属于我的照片诞生于此,也走进我手机的微信头像中。
六
那座雕像其实就是一张照片,是历史的相机拍摄的,远处的天山和更远的汉朝是它的双重背景,遥远却又清晰。
当地人怎么称呼车师古道的,我没从吐鲁番城区里生活的吐尔迪、天山北麓的牧民哈麦提或本土学者那里找到答案,这或许与突厥语、匈奴语的消失有关。连见证大唐威武的别失八里,这样辉煌的名字早都被如今的吉木萨尔县取代了,车师古道的乳名被丢失又有什么呢?“他地道”名字丢失又算什么呢?历史的风吹过来,一层层地掩埋着过往,裹住了功利而残酷的历史书写。他地道、车师、疏勒、别失八里等游牧文明带上的名字,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向文化交锋前的暗道里,兀自喘息乃至消亡。历史文化基因,有时很容易被篡改,尤其是权利意识灌输在使用这些名字的民众中时,他们在使用改写这些名字的强大文化下的话语过程中,开始变得结结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