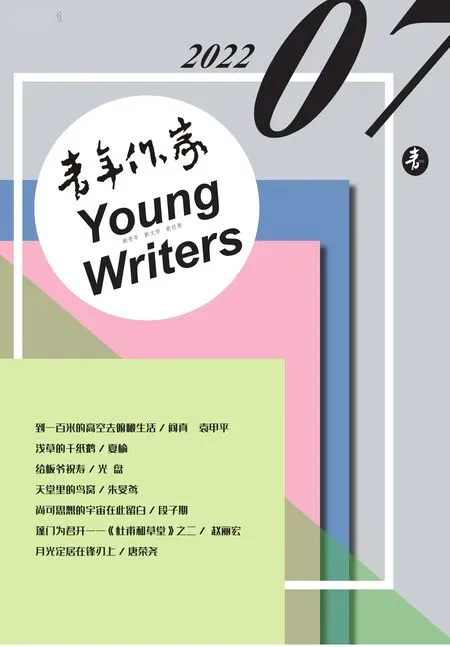评论者说 青年们的空间叙事
崔耕
如何在一个向外太空探索的时代书写古老的哲学故事?青年作家段子期在她的小说新作中给出了一种可能性。首先,将全新的时空概念引入小说:“思度星上的生命会定时祈祷,祈祷时间42秒。”这句话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充盈着饱满欲滴的叙事信息,同时符合科幻小说的惯常写法,即先构建小说的世界观,这也是科幻小说相较于其他小说而言必不可少的叙事骨骼。对于一篇科幻小说来说,《尚可思想的宇宙在此留白》一文,无论命名还是内容都表现出强烈的思辨倾向。得益于科幻的特殊文体,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哲思完全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重力束缚,变得像真正的思绪一样轻盈。这样的轻盈催生出一套完整的宇宙文明观,作者借助小说中的某一位主人公之口将其十分详尽地道出:“宇宙文明分为T0—T8阶段,T0是在大爆炸之前,宇宙和星系还未产生的混沌阶段……而T8,则能任意折返于T8以下的文明世界中,能恒顺所有阶段的文明,T8文明的终极目的是令宇宙中所有文明都攀升至T8……”(详情见原文)。这位主人公还悲观地发现,“文明大多数毁灭在科技极度发达的T3、T4阶段,用物质科技丈量宇宙,因此难以突破文明的界限。”宏大的世界观建构完成之后,作者开始让小说慢慢向读者的现实世界靠拢——很容易得知,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大致位于作者给出的“T3”文明阶段,不幸的是,这几乎已经是所能达到文明的极限。“T4”之后的文明,已经无法用具体的、及物的词语描述,于是出现了“至纯至善”“生命的本质”“本真”等抽象的哲学概念。年轻的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叙事野心,她试图通过对异质空间“思度星”的探索,追问“宇宙对他们三缄其口的秘密”。
这个存在于异质空间的哲学命题,被作者用一个贯穿全文的神秘时间符号——“空白的42秒”切出了一道细小的缝隙,似乎暗示着探索秘密的途径。通过这个小小的切口,隐约得见那个神秘的真相——静止、停顿、留白,这是“无”的几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只有经历了“无”(也可以理解为作者设定中回归本真的“T7”文明),才会重新生发出包含万物的“有”。此时的“有”,是回归本真之后宇宙文明的重新排序,是一种全新的、至纯至善、秩序井然的“有”。小说后半部分的三个小故事,分别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加深了对“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古老哲学命题的佐证。将哲思放在比想象力更打眼的位置,作者显露出更高的叙事追求,其偏成熟的笔法让这篇不长的小说拥有了一种属于未来和太空时代的史诗感。而它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当作者沉迷于对宇宙终极问题的哲思时,很容易掉进自说自话的叙事节奏中,因此未能在小说与读者之间建立起流畅的对话关系。当然这对于一位年纪尚轻的作者来说,过于吹毛求疵了,完全纯熟圆融的写作,需要更丰厚的阅历和时间去支撑。
本期另一位作者陈琛的新作《掩埋》同样用到了几个标志性的空间场所来组织小说叙事。作为一个从事功层面上完全的失败者,小说的男主人公王盛义与他存身的空间——花圈巷之间,从始至终都呈现出相互嫌弃又纠缠至深的关系,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在花圈巷这个空间,它的兴衰变迁和陈设结构,在气质上和小说中人王盛义保持了高度一致:灰暗又一成不变,如死水般没有希望——在王盛义的人生中,曾经短暂出现过改变生命轨迹的机会,奈何原生家庭的地心引力太重,不由分说地将他拉回原地,重新汇入没有指望的起点。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小说《掩埋》的“花圈巷”设置得很精巧,这个含有诸多隐喻意味的文学空间,自然不是静止的叙事容器,而是有生命的、流动着的叙事元素,有意思的是,在这篇小说中,作为叙事元素的文学空间花圈巷,其生命性和流动性却是用“丧失生命力”这一过程来表现的:“王盛义去杂物间取花圈,穿过很久没卖出去的纸房子、纸车、纸做的童男童女,看见桌上摆着的纸灯笼、纸寿桃、纸元宝,又看见墙上挂着的绣满花卉虫鱼或金元宝的寿衣寿袍。他走到花圈跟前,花圈也落满了灰,他抖了抖,扬起灰尘,吸进喉咙,咳嗽起来。花圈的中心笨拙地写着“奠”,是男人写的,王盛义环目四周,也都是男人从前的手艺,他想到了自己梦。”花圈巷的功能性(这也意味着它的生命力)被不断削弱,只有在太阳下山停止营业后,它才会以另一种身份(普通居住区)还魂。
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同样是命运不济的受害者,作者采用了一种写意式的手法,捉迷藏一般交代了发生在她们之间的情感阴谋。当两位主谋最后一次见面时,又一个隐喻性的空间出现了——一家名为安维塔的英式下午茶茶屋。据作者在其后的交代,这间英式茶屋,就开在曾经的花圈巷一带。男主人公王盛义与三位女性之间的纠葛,命中注定似的在此揭晓。被动成为阴谋实施者的妇产科医生林凌,在这间做作又不合时宜的英式茶屋里,无比慌乱地挥别过去,与阴谋的发起者沈青诀别。不知道对于这两位女性来说,在英式茶屋这个文学空间里发生的事情,是否能作为掩埋过去的仪式?从作者的叙述中看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她(沈青)摩挲着桌面,看见桌面的倒影,她和鲜花一起,俨然墓碑前的哀悼。”最后,小说在一组颇具电影画面感的明暗对比中结束。叙述一桩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按空间而非时间去建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打乱时间线的叙述给悬案的侦破增添了难度,也为在悬疑电影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趣味。而作者在一篇悬疑小说中致力于人物心理的细致描绘,以及他们面对命运无常时徒劳无功的挣扎,则得益于贯穿全文的隐喻性文学空间,它们为这些旁逸斜出的叙述起到了互文效果,以至于让那桩引人注目的悬案退回到人物命运的背后,成为作者书写命运、刻画人物的次要叙事元素。
藏族青年作家桑杰才让的作品《一路向西》中的空间,呈现出随小说主人公不断流动的特征,作者也以此命名了这篇小说。小说有十分明确的宗教背景,出场人物不多,空间变化依次为:“寺庙——东珠爷爷家——前往拉萨途中的露营地——旅店”,在这些大多数充满宗教色彩的空间中,作者对身处其中的人的描绘,却带有明显的世俗性:小说以大喇嘛打水这样的日常开头,讲述了一座修在山腰的小寺庙迎接从黎明到破晓的经过,在这个看上去无比寻常的一天,大喇嘛要带着小喇嘛出发,徒步去拉萨朝圣。小喇嘛跟大喇嘛申请带上自己的猫一起去,被拒绝之后跟大喇嘛辩论:“你要带自己喜欢的收音机,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带我喜欢的”——这一系列的行为与对话,与即将要开始的“朝圣”,显得格格不入,但又有一种奇特的和谐感,融合了世俗生活的神性,让两位僧侣身份的主人公具备了被书写的实感。他们从一个空间移动到另一个空间,不仅是寻求灵魂皈依的精神旅程,更是切切实实的肉身行为。桑杰才让敏锐地捕捉到了在朝圣路上的露营地里,神性和世俗交织融合的一面,并展示给读者一个大喇嘛听收音机,小喇嘛想着留在家中的小猫,感受到孤独的场景。对于笃信宗教的神职者来说,孤独是不应该出现的情绪,只有俗世中人,才会屡屡被孤独击中,年纪尚小的喇嘛,还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僧侣,这似乎也成为他露营第二天醒来后完全不记得前一夜惊心动魄的险情的原因——这样一起在野外被群狼包围竟能安然无恙,连经书都保存完好的神迹,大概也只有如大喇嘛一般功力深厚的僧侣才能撞见。
在小说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叙事空间——旅店,大小喇嘛遇到了一群俗人。大约是经常感受到孤独的缘故,这群俗人常聚在一起,讲僧人与寡妇的故事,小喇嘛对他们很好奇,离开旅店前特意去打探这群人的行踪,却带来让人吃惊的消息:这群人竟然同为僧人。小喇嘛提议跟他们一起去拜见释迦牟尼,大喇嘛没有回答——“今天是十五号,大喇嘛持口戒,不可以说话。”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像一个来不及解答的谜题。藏族青年作家桑杰才让无法充当谜题的解答者,只好以“口戒”为由将它搁置在那家小镇上的旅店。世俗性和神性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大概是身处宗教地区的人始终会碰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