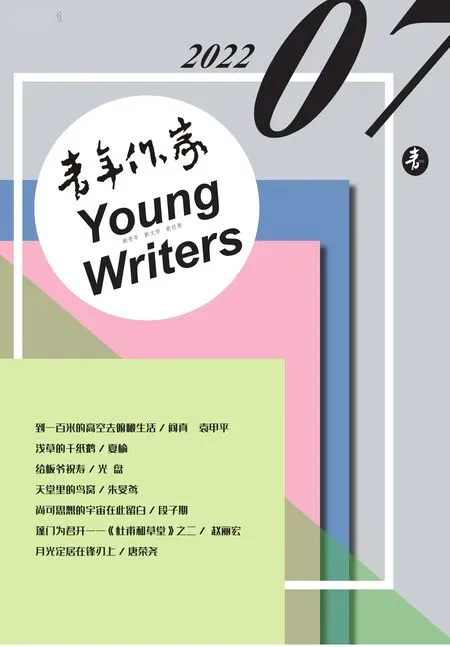小说观 站在人这边,无限追猎
夏 榆
我经常会有身在风暴中心,或深居激流漩涡的感觉。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人,沉浮于社会的存在实况,经常带给我脆弱又无能的体验。然而让自己安静下来,心定神闲坐在书桌前,也是我每天会有的状态。
更多时候,生活犹如狂飙席卷,世界仿佛深海巨浪之上的舰船,动荡起伏险象环生。战争,我们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现时的屠杀现场,远在天边,也近在眼前;战祸制造的难民潮四海涌流;瘟疫在地球上的弥漫,带给人类更广泛的恐惧,死亡讯息密集纷涌使世界惊愕。地震、海啸、飓风、雪崩、空难,在灾难与祸患面前,人之无助成为生命的某种真相。
现实的图景令人黯然神伤,似乎难以安宁。然而我还是会让自己镇定,心静神安地坐到书桌前,在打开的电脑上敲击自己想要写下的文字——虚构或非虚构文学作品。当然会有写作的虚无感,但我不会放任它驰骋。现实世界的无常显而易见,不义、耻辱、失败、挫折、无能、愤怒、沮丧、厌倦,这些深藏于词典里的词语,就是我们在某个时刻遭逢的境遇。你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实比虚构世界更复杂离奇也更诡谲惊悚。这时你的写作,需要绝对的理由支持,以使你的情感和生命免于在虚无中溃散。
“写作作为祈祷的方式。”我喜欢卡夫卡写在日记里的这个句式。如今它成为我书写的姿态,同时也构成我安坐书桌前的动力。事实上,除了肉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我们还有灵魂栖居的维度。心理学大师卡尔· 荣格说:“向外看的人,沉睡;向内看的人,觉醒。”
我更愿意成为一个灵魂觉醒的人。现在我在注视世界的同时,也愿意将目光投向自身。观看灵魂的存在,世界将成为灵魂的倒影。就写作而言,我心仪这样的叙述品质,如电影《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的制作人让·科克托回忆马赛尔·普鲁斯特所言:“恰如腹语者的声音来自胸腔,普鲁斯特的声音发自灵魂。”
就小说艺术而言,我相信小说是对存在的勘察和审视,而小说家更像语言的炼金师。
我有职业的榜样。那些我尊敬的杰出者,可以构成一个璀璨的星系。被这光谱照耀,是我私享的幸福。切斯瓦夫·米沃什,是这星系中最亮的一颗,他令我有精神共同体的契合感。睿智、精神强健而高寿,这是我心仪的创造者的境界,人类的精神高地。
“这个世界的事物应该被沉思,而不是被解剖。”米沃什的言说此刻回旋在我心里。写出《被禁锢的头脑》的伟大诗人在晚年是安详的,他构建自己独立的诗意世界,也践行个人的解放。他说:“解放意味着站在生与死的永恒之轮之外。艺术应该站在那运转的轮子之外,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激情、欲望,以某种超然的态度,接近客体的对象。生命的激情,可以通过超然的沉思而被消除。”
2006年夏天,我有机会到波兰访问,在米沃什的故乡克拉科夫停留的时刻,专程去安放诗人遗灵的教堂。我带着鲜花,愿意献上自己的敬意,同时接受他的指引。就像寒夜之星,照彻大地幽暗的褶皱。我记得米沃什的箴言,现在它成为我写作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