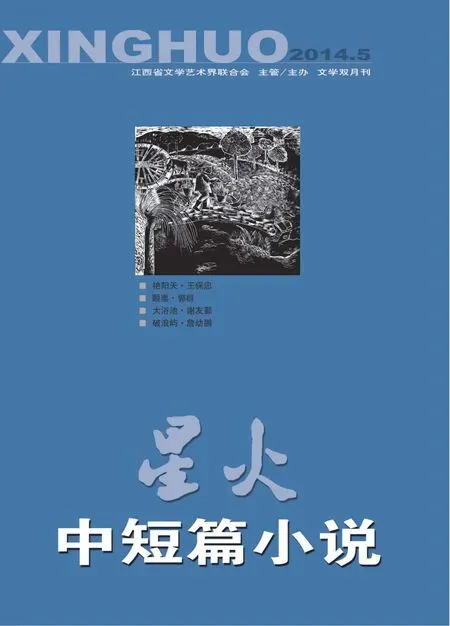影子
○付晓祺
阳光斑斓的午后,和孩子一起散步,我可以走在他左边、右边,也可以走在他前面、后面,可以拉着他的小手走……这都没关系,但得让他踩到我的影子。有时我快走几步,我走得快,影子也快,他小跑着追赶,追不上也不气恼,嘟囔着,继续快追,等追上踩到我的影子,又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你疼吗?”
光下留影,有光,就会有影子。影子与我们相伴相随。当别人踩到你的影子,你会疼吗?
“当然疼啊!”我每次都给孩子肯定的答复,他睁大眼睛吃惊地看我,一脸懵懂,“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是真踩到了你,我踩的是影子。”
年幼的他不会明白,疼痛,是生命的影子。
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说,生命的本质只是行走的影子,所有的痛和罪恶都在行走的路上消解了。只要活着,只要行走,就避免不了疼痛。
有时,疼痛的影子拉得很长,能容下几代人。
母亲在阳光下行走,看到自己的影子,悠悠地说:“昨晚我又梦到了我妈,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因思亲产生的忧伤,让人心生怜爱。
犹记孩提时代,外婆最疼爱我。那时父母工作忙,白天把我送到外婆家,外婆用故事、童谣、美食陪伴我度过了温馨快乐的童年。一生善良勤俭的外婆,生活给予她的厚爱太少太少。少时丧母,成家立业后除却工作,还起房盖屋,抚育子女,操劳不断,老来又经受病痛的折磨。生活的磨难,病痛的反复,其间的种种酸楚、痛苦,她默默承受。
记得外婆过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我去探望她,她一动就全身疼痛,只能躺在床上。若尝试着稍微活动身体,潮水般的疼痛便如影随形,生怕给路过的其他影子偷走残生里所剩无几的欢乐。
从医院出来,母亲慢慢地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太阳把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我张开双臂,母亲的影子被我的影子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一个夕阳残照的下午,外婆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她身上的疼点无声地滑动,渐渐退淡,终于彻底消散。
想起年幼时外婆给我讲过的影子故事。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样子长得像鳖,只有三条腿,人们称它为“蜮”。这古怪的甲虫背上有硬壳,头上生角,身上长翅膀,能飞上天,在暗中偷袭人类。它平时隐蔽水中,口中有一把弓,能含一口沙子喷出来,若被它射中,便会生病。即使只射中人的影子,人也会生病。
外婆是被古怪的甲虫射中了才生病的吗?外婆走后,她的影子呢?那时年幼的我对死亡的概念和意义一无所知。从此,夕阳下就只剩下我孤独的影子。
我们在意的影子出现,又离去。它确实是来过;可它确实是走了。这来去之间,经历了生活的平淡、复杂、开心、悲伤,风口浪尖,如履平地。
生命曾降临在太阳的璀璨里,虽然那光明的源头消失了,但复制出另一个生命,我们永远跟随着初生的命运,行走,或驻留。
外婆的影子是母亲,母亲的影子是我。
小时候对影子最感兴趣是在电视中看皮影戏时,一个个影子蹦来跳去,嘴巴还一张一合地说话,惟妙惟肖。
渐至年长,不再和影子玩游戏,却总会低了头看自己的影子,也总会在太阳下、月光里找寻自己的影子。
上初中学过物理,知道了影子是光沿着直线传播产生的,明亮的阳光照在比较暗的身上时,投下的是阴影。最喜欢张开手掌,眯起眼睛面对阳光。灿烂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手的影子投在湖水上,湖水随着微风的吹拂慢慢荡起涟漪,当炽热的光芒猛地穿透身体时,隐藏在身体后的那个影子会无处躲藏。
思绪在此刻游离。“你从哪儿来?是何处人氏?你为什么这样自隐,使人们看不见你的容貌,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你有妻室和母亲吗?她们是否在时时等待你的归来?你有儿女吗?他们是否常常倚门相待,当你把小小的火种放到房角以后,就用力爬上你的膝头,搂住你的脖子?你有没有一个可以共同欢笑、共同悲伤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个哪怕是仅仅可供聊天的相识? ”想起这个只有在黄昏后才能看见的,一个无声的、不露真相的、像影子一样的人形。
阳光转瞬消失,夜色低回,当月亮遁入云层,一个神秘的影子闪了出来。一个幽灵,它要做对夜晚最具威胁的事:把路灯点亮!这个黑暗的敌人,在市民集体酣睡时,在空荡的街巷中,在积雪和枯枝的路面上,踽踽而行……无人知晓它是谁,无人知晓它的来历和任务。
终于有一天,在往常那个时刻,激动人心的影子迟迟没露面,街道一片沉寂。
普鲁斯开始寻找点灯人。“点灯人?谁知道他埋在了哪儿?昨天就埋了30个死人。”掘墓人不耐烦地说。
“不过,他是埋在最穷的人那个区域。”泪流满面的普鲁斯提醒他。
“这样的穷人昨天就埋了25个。”掘墓人的语调听起来比墓穴里的铁铲还要冷。
“要知道,他的棺材没上漆。”
“这样的棺材昨天就来了16副。”掘墓人头也不抬地继续挖土。
普鲁斯到底没能看见他的脸,也没弄清他的姓名,甚至连埋他的一抔黄土也没能找到。他死后给人留下和生前一样的印象。
“点灯的人也是人生道路上的匆匆过客。活着时无人知晓,工作不被重视,随即便像影子一样消失。”“但我确信,上天已收回了他,而另一个影子已悄悄上路。不久,夜里就会再次出现火炬,贫民窟就会再现他的兄弟。”
点灯人真像影子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暮霭中吗?至少火光唤醒了沉睡的萤火虫。点灯人消失了,但光在萤火虫身上得到了延续。
有光,就会有影子。在光下,自己的一举一动,影子都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做我最忠实的伴侣,即使别人都远离而去,它却始终和我相随。
记得那是高考前的一个月夜,文科综合模拟考让我们下晚自习的时间比别人晚了半小时。回家的那条路正在拓宽,没有路灯,只有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忽然听到身后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扭头一看,一个醉酒的男子正举着酒瓶向我们逼近。我和好友手牵手快速飞奔,一路上不敢发出其他声音,只任醉鬼的叫骂声在风中渐渐消失。那晚的我们,害怕至极,一起陪我们走过最黑暗的巷底,熬过最深沉的长夜的,只有影子,它坚定不移,默默跟随我们的足迹,在我们最孤寂迷茫的时候,那么忠实而真实地跟随着,不离不弃。
此刻我投在湖光上的身影,这影子是生命的一半,天地给的阳寿是另一半;对接这一撇一捺,便是完整的“人”。我对着影子继续普鲁斯的诘问:“你从哪儿来?是何处人氏?你要到哪里去?”回答我的,只有轻柔的风吟。
影子不会说话,甚至不会呼吸,可它是我心灵的剖白。我不想靠近它,却离不开它,它像罂粟花一样隐秘,引人沦陷。
形指身体,影指身体的影子。形影不离指身体和自己的影子相依相伴,永不分开,形容彼此关系亲密。学生时代,老师讲到这个成语,从本义到引申义,极其详尽,我常在作文中写:“我和好朋友整天形影不离。”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太白的古诗是好友婕最喜欢的。2008年的夏天过后,一切关于她的片段都归于回忆,属于时过境迁后的云淡风轻。
我不曾刻意去怀念,却时常陷入回忆的泥沼。那些逝去的青葱岁月,现在想来,像被宠溺的舌尖享受着一颗颗糖果,甜蜜,美妙。
枯燥的法律公共课上,我们悄悄在下面写诗,为押韵的诗句绞尽脑汁,自得其乐。乏味的写作课老师一板一眼的教授总是提不起我们学习的兴趣,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课桌下悄悄读着《穆斯林的葬礼》,用精彩的小说情节打发无聊的时光。我们一起看云,一起听雨,一起写诗。我读她凌乱的诗句,她看我矫情的文字。
我们该是懂得彼此的。我们是彼此的影子。
毕业后,只是断断续续地联系,很少的短信,很少的电话。我们习惯在文字里相遇。好像站在对岸,我们习惯通过文字观望彼此的生活。有时枯寂荒芜,有时火树银花。
和好朋友真能形影不离吗?时光给我否定的答案。
穿越我们的时光,告别一些面孔,重重叠叠。深信,我们依然能够懂得彼此心底的那个世界。即使偶有雾气氤氲,依旧明亮如昨。
马克·李维后来告诉我,影子也会被偷走。
如果有一天,我的影子被偷走了,它会告诉别人我的什么秘密呢?
我的影子肯定会告诉他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也许那是被我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一段往事,某个夜晚被黑夜侵入后的胆小,与母亲的一段争吵,或是我从来不肯承认的一段青涩暗恋……
我的影子在哪里?它始终牢记着我生命历程中曾经的那些痛楚与欢欣。
夜的深处,世界早已疲惫不堪,我和我的影子,相对无言。
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能读懂你的所有心事?她一定会对你说,我偷走了你的影子,不论你在哪里,我都会一直想着你。
有些人只拥吻影子,于是只拥有幸福的幻影。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不妨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寻找一种崭新的人生。在光下低头看一看,或许影子比你更了解自己。
“我喜欢一个人走在有路灯的夜色里,感觉寒夜都变得很温柔,还有影子不离不弃的相伴,感觉自己也并不孤单,那个时候感觉自己与自己很近。”好友的话让我想给自己的影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影子会永远与我们相随,直到天荒地老;影子会永远与我们相伴,直到我们还剩下人生最后一丝呼吸。
“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
孩子睡前把白天学过的课文背给我听,我问:“你睡觉了,你的影子怎么办啊?”他掀开被子,说:“它跟我一起睡觉啊,你看看,它已经钻进被窝了呢。”
“你等会翻身,压到它怎么办?就像你踩到我的影子,你的影子也会疼吧?”我继续问。
他一脸调皮,“我猜不会压到它,我翻身的时候,它也跟着翻身了啊!”“妈妈,再给我讲一次安徒生的那个关于影子的童话吧。”
“热带的国度里,太阳晒得非常厉害。人们都给晒成棕色,像桃花心木一样;在最热的国度里,人们就给晒成了黑人。不过现在有一位住在寒带的学者偏偏要到这些热的国家里来……”
我开始讲述这个稍长的童话。为了窥视对面房子里的秘密,学者想入非非,唆使投射在对面阳台上的自己的影子,去偷窥,造成的后果是,他把他的影子丢掉了,它真的不回来了。几年后影子发迹,反过来要求学者做他的影子。他们遇到一个公主。影子以绅士的形象赢得公主的好感,因此公主决定选影子做自己的丈夫。影子警告学者永远不准说你曾经是一个人。学者不能接受,于是,影子对公主说,我的影子疯了,他幻想变成了一个人,他以为我是他的影子。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把学者处置了。
孩子喜欢那些装饰性的华丽描述,未必能体味作者对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的敏锐洞察与深入思考。影子就是学者本身,不过是一个人的两个品格,一者是真善美,一者是相反的人格。
想起小时候父母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了坏事,丟了魂,变成鬼,中午的大太阳底下就找不见影子。出没在夜里的鬼,月亮底下也找不见影子。年幼的我走在阳光下,月光下,总是先低头寻找自己的影子,只有看到影子,方才安心。看着影子在不同角度变换,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瘦一会儿胖,我把影子贴在墙壁上,贴在花丛里,贴在落叶上,我不敢干坏事,生怕因此把影子弄丢了。
孩子早已进入梦乡,台灯把他的影子投到左侧的墙上,我离远一点坐到他的右侧,配合着灯光把我的手指投射到墙上,墙上就出现了一幅影像—我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
有光的地方,才有影子。看着孩子熟睡的身影,我更清楚自己影子的重要性,它会无形地影响到下一代真实的影,对那个幼小的心灵,我的影会成为他心中的形。我必须常常检点自己的影子,从里到外地看,从心到形地整。
我闭上眼,在一片漆黑里前行。“前方就如同闭上眼后的那般漆黑吗?”对着脚下挺直的影子我平静地问。
影子不作回答,再一次选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