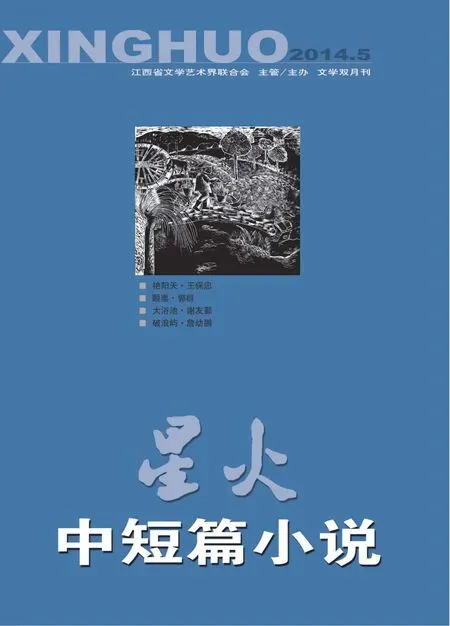等于一
○沙爽
天窗
隔着玻璃窗,我的皮肤感知到雪的气息。夜色深浓,雪飘落于不可见之处。黑暗从对面的崖壁反弹回来,在幽谷中如回声破碎,坠向寂静的谷底。我想这黑暗将如何落在雪上,雪又如何包裹起黑暗,在无数半透明的花瓣之间,搭建起千万间夜的广厦……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是高山崖洞里孤灯独坐的僧侣,苦于斯世无数难以参透的禅机。
那盏灯便是在这时亮起来的。一盏莹白色的日光灯,我看不见它,我看见的是它被世界圈定的幻影。小时候,祖父出谜让我猜:“东西不大,满屋子装不下。”我答不上来。祖母搁下纳着的鞋底,悄悄指一指屋顶上吊着的日光灯。如今那盏灯隐于岁月,光晕溢出,将黑暗切割出一个规整的方形,大小和形状都近似于一面普通的穿衣镜,只是与地面平行—我是说,它飘浮在这黑夜的横截面上,是一大块突兀现身的冰,而未知的河流于其下奔涌。
我瞪住它看,震惊于这人世的不可思议。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住了五年有余,五年之间,我曾无数次向窗外眺望,而这扇天窗,始终隐匿于我知觉的盲区。庚子年疫情伊始的那段时间,闭门蛰居中百无聊赖,我才留意到这座厕身在车棚后边的狭小庭院。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是小区车棚的一部分。这座房子的北侧山墙确实与车棚相连,但朝西的这一侧却开有门窗,门前有狭小的过道,通往南边的一块迷你菜园。再细看,菜园的旁边还有一扇门,连接着河北梆子剧院的停车场。
这是我到天津后,第一次看见有人居住的平房,而且,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我猜测着住在里面的人—是剧院的工友和他的家属?这周围几个小区的住宅楼,哪怕是建于三十年前典型的“老破小”,每平方米售价也在五万元左右。假设一个工薪族每月攒下三千元,积三十年之力,才能在这一带买下二十个平方,即使其产权只剩下二十年。这世间有人住千万元豪宅,有人租住在敝陋蜗居,有人住进下水井。水泥森林有它自然天成的筛选系统,一种无根的植物由此诞生。至于这幢开有天窗的平房,是否会为无根之木提供某些过渡的可能?
既然整整五年,我忽略了一扇天窗的存在,那么很有可能,我还忽略掉了更多的东西—那些生活和其他生命试图传递给我的,并等待着我回应的讯息。它们中的一部分,也许还会在未来重现;而另一部分,则永远地消失了。
是的,就是那种一旦错过则永远错失的恐惧,有时它会化身为一扇天窗,向我遥遥示意。每天午夜,这窗中的灯光反复闪烁,向苍茫天宇发出微弱的求救信息。它来自爱尔兰女作家爱玛·多诺霍的《房间》。在这部小说里,十七岁的女孩乔伊因为接受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求助请求,被其绑架并强奸,囚禁在地下室里长达七年,并于此间生下了儿子杰克。七年之中,乔伊不止一次尝试逃走,然而,地下室的墙壁和屋顶均以钢板铸成,唯一的天窗外也焊有铁栅栏。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钢铁牢笼里,乔伊教杰克认字,督促他坚持运动。她告诉他,电视里的世界是假的,连那个有时会来地下室的老尼克也是假的。每天临睡之前,她熄灭灯光,再按亮。再熄灭,再按亮。她祈求有人能够发现她发出的求救信号。天窗之上,夜空高悬,星月清冷,除此空无一物……每当念及这样的场景,我就感受到那种彻骨的绝望。如果你创造了一个谎言的世界,又将如何去打破它呢?当老尼克失业,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乔伊知道她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她告诉杰克,其实电视里的世界都是真的,在这逼仄的地下室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真实的世界,那才是他们要努力奔赴的地方。
为什么假的又突然变成了真的?刚满五岁的杰克,不知道还可以相信什么。这时,一枚落叶轻轻飘落在天窗上。一枚真实的叶片,在此时,有如神迹—作为唯一的证人,它证实了窗外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树木,阳光,飞鸟,以及大地上疾驰而去的时间。
等于一
现在,允许一个正向的回忆来到心里
曾经在生命里,你感觉到深深的连接
一个深刻的完整
带着深深的自信
或许是在大自然里产生的一种体验
或许是与深爱的人在一起
或者是成功地克服一个艰巨的挑战
…………
循着视频的引导,我开始尝试一场自我催眠。记忆的画面切转,闪回—我的生命中有过哪些难忘的正向时刻?相较而言,快乐总是随风飘散,而痛苦更易于留下凹痕。挑战?深爱的人?大自然?记忆的窗帷掀开了一道缝隙,我看见夏日将尽的草原。清晨的阳光清澈如水,草地上新绿铺展,仿佛刚刚出生的婴孩。原来新生是这样突然降临的狂喜,是这样无垠的宁静与安恬。我几乎要怀疑我身在梦中—那柔和的、葱茏的梦境,一幅飘曳的丝绸,在这里和那里,它微小的起伏投下深绿的暗影。几头黑白花的奶牛正在享用早餐,离得最近的那一头,慢慢地向我转过脸来。时间凝止,车厢消逝。隔着一扇窗,我看见了天堂。
返程的列车上,对面的下铺坐着一个方脸薄唇的男子,带着那种长途旅行的人惯有的慵懒和倦意,百无聊赖地打着呵欠。
他说他是在满洲里上的车—他出差到俄罗斯已经半年了。“你去过俄罗斯吗?”
“没去过,但我想有机会去看看。”
“看什么?”
“贝加尔湖啊,西伯利亚森林啊,之类的。”
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森林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树吗?—你到海拉尔做什么?”
“看草原啊。我一直都想来呼伦贝尔看看。”
“嗯?那不就是草吗?哪儿没有草?那些,那些。”他用食指一下下点着。草原的无垠美景于车窗外掠过,草们在夕光中向我颔首作别。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即使我们坐在同一个车厢里,面对着同一扇窗子。天堂?天堂只存在于某些特定人群偶然遭逢的时刻—那种类似于被催眠的时刻。但是有些人很难被催眠,这是艾瑞克森说的。
我把这些讲给我的好友听。当我讲到那个天堂般的草原清晨时,不由自主地,我的眼睛再一次盈满了泪水。
以后有机会,你也去草原上走走吧。我说。
好友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她的丈夫不喜欢那些荒凉的地方,他更喜欢繁华,喜欢都市。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巨大的牡丹图,占据了一整面墙壁。在他们家海边别墅的客厅里。
我吸一口气。荒凉?为什么我从未想过草原是荒凉的?而所谓的荒凉,莫过于人到中年,你才发现自己始终独自一人。对一些人来说,人生是可能拥有旅伴的,如同一加一可以大于或等于二;而对于另外的一些人,一加一仍然等于一。
孤窗
那扇窗很小,开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是那种上悬窗,铰链装在窗框的上方,向外推开到最大限度时,可以勉强容一个成人钻过去。
我踩着凳子爬上去。窗外是一座狭小的庭院,三四米宽的样子,还堆了些杂物。旁边是另一幢房子。我到那幢房子里洗漱,再翻窗回来,整理背包准备上班。但是有一件东西被我落在了对面的房子里,需要再次翻窗去取。几次三番下来,我心头焦躁,钻过窗扇时的感觉也越来越糟。既然全家人都要这样辛苦地攀上爬下,为什么不干脆在这面墙上开一扇门呢?
一念及此,我对我父亲说了这个想法。这是我父母的家。在墙上开一扇门,首先要征得一家之长的同意。
但是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我父亲锁紧眉头。他酝酿中的怒火还未迸发,我已胆战心惊,惶然无措。正当此时,有一物破空而至,沉重地击中我的肋骨。
是我的猫,和它花样百出的叫醒服务。
我把这段梦境讲给沙琳听。沙琳发过来一个捂脸的表情,说:“就是这样。一句话不合心意,爸就要发火。”
但我的心神还盘绕在梦中的窗扇上。那窗和那院子,一切都恍如旧识。连同穿过窗扇的瞬间油然而生的幽闭恐惧,以及肺部遭受挤压时强烈的窒息感,它们穿越梦境,将我整个地裹挟。
那扇窗,开阖于我的童年与少年。如今想来,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北方城市,那些如火柴盒般簇拥在一条条巷弄里的简陋平房,大抵都砌有这样的一扇北窗。它不可能开得太大—北国的冬天寒冷漫长,当朔风呼啸,天地间亿万支冷箭齐发,钉在窗扉里的那一块半透明的塑料布哗啦作响,仿佛里面藏有活物一般。对一个胆小的孩子来说,这块悬在半空中的塑料布,是整个冬天的噩梦之源。
这扇窗开得很高,很可能高过我的头顶—九岁时,我的身高有没有超过一米二?我对此竟然全无印象。只记得有一次,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尝试穿过南窗上的铁栅,但没有成功。那天是六一儿童节,一大早,我们全班在学校操场上集合,列队进入人民公园。我的上衣口袋里揣着母亲给我的五角钱,虽然算不上一笔巨款,但至少囊括了十几个选项的节日套餐。公园大门口处的套圈游戏,玩一场只需要五分钱。坐一次“宇宙飞船”,一角钱。滑梯、跷跷板、秋千都是免费玩。一根足以作为午餐的大麻花也只要两角钱。刚出锅的玻璃牛五分钱一茶碗。我一定抵挡了无数诱惑,才留住了那五角钱。快到中午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在公园门口分了手,我走到卖麻花的小摊前,一摸衣兜,才发现里面的钱已不翼而飞。这时我想起来,同时不见的还有我的钥匙。其实钥匙就躺在家里的高低柜上面,早上出门时,我忘了把它挂到脖子上。
真是一个悲伤的儿童节。而童年的悲伤在于,无力解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这一刻,我既无法穿越窗户上的那一排铁栅,也没有办法让家里的猫咪帮忙把高低柜上的钥匙叼出来。我的肩膀嵌入了铁栅里,但是我的头太大了,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去。人为什么要长这样大的一颗头呢?既然他们总是这样丢三落四,忘东忘西。我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弃了,我无处可去,还饿着肚子。我祈祷这只是一个梦,只要睁开眼睛,这无从索解的噩梦就消失了。这种失真的感觉难以描述,它是一个死结,是一团越缠越大的虚无。直到如今,每当生活向我展露出它锋利的牙齿,我就会身不由己地退回到那个午后,回到那个九岁的孩童的体内,重温她无边无际的惶恐与孤独—初夏的大太阳明晃晃的,照彻了这人间的苦恼和荒凉。
那个儿童节剩下的半天时光,我是怎样度过的?我是否曾步行二十分钟,前往我母亲的单位求助?其实这本该是一条最佳选项,为什么我却选择了漫长而徒劳的尝试?有一次,好友说起她小学二年级时的经历:整整一个月,每天下午放学,她被一个高年级女生追打辱骂。她不知何以如此,或许原因仅仅是,对方享受这种欺凌他人的乐趣……她在恐惧中煎熬了一个月,却从未想过可以向母亲求助。而直到如今,与我的相处仍然是母亲生活中的最大困扰—作为至亲,是什么始终横亘在我们与父母之间?即使在梦中,那扇理应存在的门,仅仅是提及它,也已经触犯了某种禁忌。
关于儿童节,后续的经历模糊成一团,清晰的是那些铁条—在反复尝试越窗入室的时间里,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了我家这道铁栅的形制:一根根铁条紧紧嵌入钉死在窗框上的木槽里。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撼动它们中的任何一根。如果我是个贼,面对这样一道严防死守的铁栅,大约也要绝望的吧。
是不是就在那一天,灵光乍现,我绕到屋后,翻越北窗进入了家中?家里可能并没有我需要的午餐,但它提供了某种屏障,某种回到出发之地的安全感。
我家的这扇北窗,外面是别人家的庭院。在这庭院与巷弄之间,隔着一人多高的水泥院墙,因此站在巷子里,很难发现我家的这扇后窗。这就是北窗没有安装铁栅的原因—虽然邻居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值得信任,但相对于数量上趋近无限的陌生人来说,邻居们毕竟屈指可数,在感觉上更为可控。
我家搬过来的时候,住在后院的这户人家,男主人姓耿。耿叔只比我父亲小七八岁,看上去却像是两代人。而且,即使是在一个孩子的眼中,耿叔与别的邻居也大有不同。据说耿叔的父亲是哪个大厂的厂长,家境好,一家人吃穿用度都很讲究。平日里耿叔不大与别的邻居来往走动,但我们两家的房子,原来住的是两兄弟,所以院子中间虽然隔了一道木栅,中间却又开了一扇小门。那一年夏天天气奇热,我弟弟与耿叔的儿子小震光着膀子在院子里玩,我也脱掉汗湿的背心,和他们疯成一团。这时耿叔推开小门,喊小震回家吃饭,迎面撞见我,耿叔显然吃了一惊,下意识地,他扫了一眼我的胸脯。
那一年我十一岁,刚刚考完小升初,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仍是一个懵懂的顽童。有好几次,出于这样那样的缘故,我经由耿家的庭院,从我家狭小的后窗翻进翻出,活脱脱的一个野丫头。
但是经由这诧异的一眼,我的童年,意外宣告了结束。
幻境
那是一场什么样的聚会呢?我只记得,去的时候好像乘坐的是长途汽车。我懒散地靠在座位上,几乎要睡着了。酒宴中许多人影穿梭来去,终于出现一个空当,我可以离开了。
通往出口的巷道空旷而曲折,光线却越来越暗。我觉得自己行走在一座山洞之中,洞壁阴冷,丝丝缕缕的恐惧气息正悄然渗出。远远地,我看见有几个人垂着头,蹲坐在右手边的壁角,一动不动。这些灰白皱缩的影子,让我疑心他们早已死去多时。在影子们空洞的注视下,我周身的血液几近凝止。
终于拐过一个弯,出口已然不远,光线也渐渐明亮起来—前面的走廊有一扇窗。一个老人坐在窗前的高脚凳上,听到脚步声,向我转过脸来。
“年轻人,这么匆忙就要离开吗?不来欣赏一下这里的风景?”
他长得有点儿古怪。鹰钩鼻大而醒目,但脸的中间部分却凹了进去,衬得额头和硕大的下巴更为突出,让整张脸看起来像一个落了单的书名号。他微弓的背是另一个更大的书名号。
出于对年长者的礼貌,我停下脚步。“什么风景?”
“过来看!”
从他面前的那扇窗玻璃望出去,我看见一泓静美的湖水。近处的水色呈现纯净的浅蓝,这蓝渐远渐深,宛如一大块渐变的锦缎,铺展向湖的对岸。在那里,是一片参差错落的崭新楼群。
“真美啊!”我由衷赞叹。真是意外,这城市里竟然有这么美妙的一座大湖。
窗玻璃共有三扇,老人坐的位置正对着中间的那一扇。我移了一下脚步,到了右边的那面玻璃窗前。奇怪,从这里看出去,只是漆黑一团。
老人哈哈大笑,“来我这里看!”
但我一闪身,到了他的左侧,啊,左边的这面玻璃也看不见!
“只有我这里能看见呢!”老人伸手来拉我。
但是我已经飞快地跑开了。老人的手臂突然暴长出两倍有余,鹰爪般的手指堪堪就要抓到我的后背,所幸我还是逃脱了。
我一边跑,一边回头冲他喊:“没有湖水!那是你设置的幻境!”
老人显然十分恼火,他低下头,按了几下什么。
我向着来时的方向跑去,试图穿过那条巷道,回到聚会的众人之中。可是我马上发现,周遭的场景已经悄然转变,我眼前的巷道正在收缩,变窄,像一个圆锥体的内部,十米远外便是这圆锥的顶点。与此同时,一个土夯的笋状雕塑出现在我的脚边。我疑心它是破解幻境的机关,但也有可能,是老人设置的陷阱。我努力睁大眼睛,试图看穿整个幻境的破绽。可是我的视力开始变得模糊,眼皮像两块一正一负的磁铁,拼命地想要合拢到一块儿。
危急之间,我在心里对自己大喊一声:“这是幻象!”
这一声厉喝穿越梦境,猛然将我唤醒。
一场梦,是不是潜意识对自我提出的某种预警?日常中我总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即使偶尔混迹于众人之中,脸上的疏离也无从隐藏。对于众口一词的某些事情我缺乏信任,执意要换个角度亲眼看看—这一看就将自己陷于两难之境。为什么我偏偏要说出真相?如果我假意相信对方的谎言,是否可以化解彼此的敌意?当某些聪明人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他们或许还可以就这座虚构之湖优雅地探讨一番……然而人到中年,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梦中,我始终没有学会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意见。理性之我深知泯然众人可以带来安全,而另一个我—那个冒失的、不顾一切的我,却一再旁逸斜出,以身涉险。
追想梦中老者的形貌,大抵来自某个卡通片里的角色。或许他就是我的大脑描绘出来的奇异博士,一旦喝下烧杯里的绿色药水,体面的绅士立即化身为邪恶的海德先生—谁能看穿这人性的双重幻影?而与其说我最初选择了信任陌生老者的善意,毋宁说,是他的老迈消解了我的部分戒心。这么多年过去,盛年的博士已垂垂老矣,但是他变化出更多的伎俩,用以谋划意义未知的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