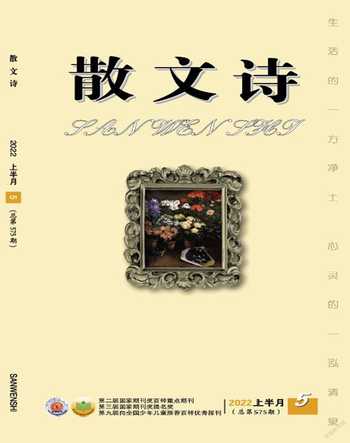接近黄昏
思之青:1982年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目前在一所中医医院从事宣传工作。201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清明》《安徽文学》《散文诗》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理事。
2020年2月17日下午4点:晴
雪还在融。
融化后的雪水从屋檐上往下流淌。完整的水流被屋檐切成了水滴,持续而有节奏地滴落到台阶下的水渠里。
阳光落在雪上。
白雪具有了锐利、饱和的色彩,流动的状态更加明显了。光滑蓬松的雪面一點点往下沉,融化后的雪水从它的内部往外抽离,滑向屋檐,从凹槽的边缘往下滴落。
阳光在水滴里滚动。清晰的水流显现着水渠底部的石纹,暗红色的颗粒变成了飘忽的影像,在水光中跳跃。
午后,雪便要融尽了。
只有房屋背面阴暗的角落里还残留少量的雪块,点缀在黑色的泥土上。雪块很薄,浅浅的一层,稀疏的纹理中,显露出被遮盖住的青黄色的苔藓。
等到雪完全融尽了,那些苔藓便如暗花似的印在泥土上。希望雪完全融尽,恐怕要等到傍晚,这已经相当快速了,因为,这是春雪。春雪,总是来得急切,去得急切,让追的人乱乱的,慌慌的,不敢去提起许多事儿。
阳光从尖尖的屋顶上往下退。
绯红色的院墙被屋顶的阴影斜角切成了两半,一半橘黄,一半暗棕。院墙的尽头,种了一排冬青,冬青也被斧子伐去了一半,只留下矮秃的树干和一群叽喳鸣叫的鸟雀。鸟雀时而停留,时而飞翔。
黄昏,已经很近了。
吸足了水的泥土散发出一股腥甜的气味,像是刚捞出水的鱼,冰冷而光滑。野草的叶子丰盈地舒展开来,又慢慢地卷缩回去,只把细长的藤蔓依依地伸到远处的云霞里去。
空气中晃动着温热的力量,把越来越浓的暮色拉进窗子里,把孩童的背影,老妇的头巾,梅瓣的余香,藏进瞳孔的暗波里。
我把这一切都安顿在这里,从清晨到正午,从黄昏到黑夜。
往后,还有雨水,惊蛰……
2020年2月26日正午11点30分:阴,伴有短暂小雨
她正在收拾屋子。
她把废弃的物具从角落里一件一件挑出来,再把它们装到篓子里,搬到屋外的台阶上。她低着头,进进出出,偶尔听到隔壁的屋子里有人在低声谈话。当谈话声止息的时候,她只听到自己的鞋子跨过门槛时的摩擦声。那声音似乎连接着屋外的春天。
被阴雨濡湿的春天,悄悄地浸透到她的目光里。
她拾起一只破碎的木盆,坐到门槛上,想要把那些散开的木片重新拼凑到木盆的圆底上。她把那些木片一片一片地镶上去,用手扶着,可是,渐渐地,她便灰了心,手一松,木片又开了。
她坐在门槛上,门前的椿树上,突然飞来了一只鸟。
她侧着头,迎着光看过去,只看到光秃的枝丫上一团小小的黑影。有一瞬间,那团黑影比真实的色彩还要具体,比真实的飞翔还要灵动。那团小小的黑影落在椿树上,连同那在光秃的枝丫间交错形成的镂空里浮动的阴云,共同雕刻了一个美丽的、永恒的瞬间。
她好像看见了生活的样子,无边无际无时无刻向远处蔓延的生活,无着无落无根无襻漂浮的幻影,但它们时而会聚集,形成一块坚硬的顽石,或者一阵扑朔迷离的细雨,或者邻家断断续续的话语声。
她又感觉到了曾经出现过的那种美丽而忧伤的气味,像是一种花朵从记忆深处泛滥出的味道,它们绽放到极致,几近腐烂。但现在还没有,它们就在记忆深处保持完美的妖娆,然后,在某个出其不意的时刻,从忧伤的源头漫上来。
她从未像此刻这般笃定各种事实存在的依据,因为,她曾经感觉过,她确定心灵的洪流漫过以后是漫长的寂静。她渴望这样的寂静在夜晚到来的时候,赋予烛光深沉的意义。
她渴望这一切。
她坐在一块青石垒成的门槛上,在那不动声色的面容下,谁也无法去破解刚刚经历过的一场细微而激烈的自我较量。
她想,或许,此刻的季节会信守承诺。
她把那些木片从地上拾起来,一片一片地丢到了篓子里。
2020年4月16日下午4点43分:晴
现在,正是向黄昏趋近的时候,如同某种带有色泽的水流、棕黄的流沙,或是碧绿的湖水,它们向生活的某个中心,不确定的中心部分蔓延,缓慢而幽深地灌入最浓郁的地方。
几日前的黄昏里,我把一株玫瑰挪到墙角种上了。
我站在院门外的台阶上观看它,直至它的叶片逐渐枯萎。它像极了某种事端,我是说它存在的整个背景,以及它本身。但我已经丧失了更多想去描述它的欲望,我常常如此丧失信心,这个错误是由我造成的,但此刻,我只剩下了无动于衷地观望,什么也不想做。
我注意到它根部的泥土,在烈日高照下变得灰白干结,有整齐的裂纹在产生。我的目光从它的枝干延伸到院墙,并越过院墙,我看到了天空。
这时,我又想起了黄昏。
现在,正是向黄昏趋近的时候,但往往因为我们被淹没其中而忽略这种意识。我们把它设置成为背景,任其在我们身后变幻莫测,层层推进地挥洒着光晕。我们只是静坐其中,它因为精密高深的演变而被我们忽略。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打开灯的时候,才会恍然瞥见窗外的流星。
我们失去的太多了,我们的悔悟不仅仅在于丢失的部分。我们同样习惯于把拥有过、如今却静置一旁的事物弃之不顾,同样把它们设置成为背景,让它们作为忧郁的借口,为空白填上空白。
晨暮之间是一盏灯的象征,或是区别。时日轮回总是螺旋上升,不会跌落,亦无旧迹可循。
静立光影之间,有时候是自私的。
我把玫瑰换了新址。我在观望无声的存在间忽略生命中本是高昂的部分。我以卑微的同情换取自然赐予的静姝。
杏树结了青涩的果实,喜鹊在欢叫。
把屋檐的线条拉向夕阳下沉的地方,就完满了。但此刻,关于那株玫瑰,是否还有某些不确定的部分?关于牵强,我们总是说漏了太多的东西。
2020年5月21日早晨7点:晴
对面楼房的院子里,有女人在用铁桶接水,她将装满了水的铁桶提到院子中央,倒入一只红色的大塑料盆里,她拾起一堆衣物浸入水中。铁桶与水,塑料盆底与潮湿的地砖,它们都在早晨的阳光里,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布谷鸟的叫声退去了,它们沿着铺满阳光的屋顶,密集的树冠,纵横交错的高压线,一直退向远离城市的田野、山林里我们遍寻不到的地方。
一天的生活,仿佛是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断裂。
它被推向一个鼎沸的高峰,再滑下来,随着日光逐渐升温,再涌向一个新的顶端,继而在昏昏沉沉的疲倦中,等待黄昏来临。
我从未对一件具体的事物有过强烈的渴望。我观望,是因为我们从不为彼此所有,未从属,未拥有,我们因此而能更加看到对方的灵魂。是的,我确信,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不可捉摸的灵魂,它们隐于内部,也无时无刻不在向外部呈现。它们是流动的,扩张的,隐忍的,没有形态的,但同时也在含蓄中收拢起无限。
我着迷于此,就像女人为一件饰物而着迷。
城市闪烁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各种各样的声响。从晨起到黄昏。黑夜是某种事物的沉寂,并在沉寂中重生。于是,黎明像是剥去了一层旧衣的新生的肌肤,我们都是在其间蠕动的卵,破壳的契机隐藏着不可言说的奥秘与欲望。
人的欲望,生的欲望。
我们把粗鄙的语言隐藏于生活的美妙中,并且加以指责外露的斜侧的部分,我们习惯于此,并乐此不疲,我们强调并用明确的标志对此区分。
我们与之碰撞,疼痛,麻木,抑或清绝,日复一日。
我躺在一张大木床上,我在一间位于顶楼的屋子里,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之中。我把脸贴在散发着棉布气味的枕上,像是平卧在清凉的湖水中。流动摊贩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小巷中穿行而过,从他喉咙里滑出的叫卖声,绕着车轮,在水泥路上滚滚向前。
阳光逐渐强烈,被粗糙的墙壁磨碎成金色的粉末,撒在地面上,水泥地上裂着细小的口子。没有风,天上没有成块的云朵,十字路口的中心立着临时红绿灯。到处是结结实实的成条索状的声响。它们穿过我的屋子,在天花板上扭成结,又从敞开的窗洞里荡出去。它们,仿佛穿过我的身体,像雷鸣穿过夜晚的高空。
不作停留,亦没有伤口。
这是寂寞的,与寂静无关,亦与这一刻尚未散尽的梦魇无关。它类似于孩童手中的柳鞭,往墙壁上摔打,一遍一遍地抽过去。
2021年2月10日晚上9点:阴天转多云
砖块在墙角立着,蛛网高悬。
一场密布的陷阱已成废墟。
黄昏正在降落,紫色的云朵滑过光滑的堤岸,微风拂过。
关于冬日?关于我的一切?我想,总有机会向您表述。正如村外的那棵白果树,它与生命中的谎言并列生长。
万物婆娑,我立在廊下。
新生的岁月细腻高洁。远处的铁轨发出粗糙的吼声。
列车,蛛网,被紫色淹没的堤岸,它们在新生的韵律中再次密集,然后勾勒出造废墟的轮廓。
总有一些荒废的语言被抛掷在白昼里,正因为如此,我至今保持缄默。但你看得见我的样子,我穿过狭窄的走廊,回声,停留在走廊的另一头。
我去过一间屋子,相似于天花板上悬挂的十二月。
还剩下一天的光景,我想,有些事物该停留在中断的时刻,然后,锋利的裂痕在风霜雨露中逐渐迟钝。有些事物可以,有些事物不行,这是宿命,并非抉择。
我有点倦乏了,让我对轨迹犹存的永恒性充满信任,我难以做到。我幻想着一些植物的名字,把它们储存在一只密封的玻璃罐中。
我又想起了那些洁白的盐粒。
我想起了那些在瓦罐中冻结的盐粒,还有十二月里的深夜,雪粒子敲我的窗。
我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我已然在向您表述,关于最后一日,飘荡在那间屋子里的来自荒原的风。
2021年7月30日傍晚6点30分:晴
我几乎是带着执拗去喜欢黄昏,仿佛认真地完成一整天里所有的琐事,只是为了等它,并且,我知道它总会在固定的时刻,沿着一道柔美的曲线缓慢地降落。
因此,我静坐于窗前,在一种盛大的静默中,去感知随之而来的一切变化,它们只是分散于黄昏里不同的片断,它们在逐渐浓郁的气流与色彩中翻滚、剥离、凝聚,继而形成这段隆重的时光里无法辩驳的完美。
夕阳的光晕,如同一片温熱的水流,慢慢倾注到物体的内部,使它们在本能的存在中无声地膨胀,将体内溢满的热情流泻出来。于是,在黄昏的笼罩中,一切都显得饱满而又轻盈。它们,时而脱离自身原本的轮廓,在空气中漂浮;时而又回顾自身,把长长的背影拖曳在城市的街头,或者乡村小路上。
但是,白昼不同,漫长的黑夜,让黎明的分界线显得模糊不清,我几乎难以预测它到来的确定性。尽管我知道对于自然界恒定的变化流动性,它会像黄昏一样如期而至,但是,黑夜所不断下压的雾气与纷杂的梦魇,会将一切固定的驱动性涂抹上分离的讶异。我们似乎要经历一场战争,才能甘愿将冗长的夜晚所掀起的浪潮碾压下去,然后,拼尽全力,浮出水面。
我难以诉清形成这一切影像的渊源。我站在露台上,面对一座城在凹陷的部分里晃动的夕阳的光泽,试图寻找一切存在的线索,为白昼纠正它本该有的慈悲与豁达。但总有某个时刻,它显得微弱,并且无力。
当我承认这一切的时候,一种奇怪的现象诞生了。
在黄昏尚未到来之前的所有部分开始变得坦然,它们以无比安宁的姿态,随着时光流动的韵律,慢慢蓄积着自身的热情。我仿佛可以暂时脱离此刻被禁锢的局面,而漂浮于紧密的视线之外,与它们平等地背对命运。
在我的体内,同时存在着两种声音,这是我在预知到这种新奇现象诞生后所衍生的寂静时意识到的。一种是在童年时期便停止生长的对于现实欲求的分辨性,一种是跟随时代而苍老的却在孤独的领域蓬勃生长的抽象化。它们同时存在于我的体内,时而交错,时而背离,时而对峙。但此刻,它们竟如此和谐地朝着同一方向蔓延。
它们将我与现实里存在的一切情感紧密连接,我依赖于此,并无法逃脱。我甚至可以确定我生命里的一切痛感正由此而来,它们既为我带来幻象的盛宴,也让我流连于烟火之气承托的稳固。
当暮色渐深,我走向街头,站在熙熙攘攘的路口,突然想起儿时母亲将我留置在姑姑家里的景象。周围的一切,似乎与我相关,又似乎与我无关。那应是我第一次感知在异乡时内心所有的空落与荒芜。
我带着一丝惊奇与胆怯,看窗边的天色一点点变亮,然后,远处响起公鸡打鸣的声音,黎明,仿佛是被拉开的一道口子,露出里面精彩、沸腾的生活,我坐在弥漫着雾气的湿漉漉的院子里,笨拙地梳理着我的长发。
2021年9月18日傍晚6点30分:晴
当暮色开始侵扰我的屋子,并逐渐灌满整个房间时,我听到窗外的空气在白昼的余温里咝咝碎裂的声响。它们裂开一道带有波纹的曲线,把优美的弧度,沿着墙壁,一直弯进房间的地板里。
这时候,我感觉天空神秘极了,所有在此刻呈现的阴影,仿佛都具有一种对生命宣誓的象征,包括我在人群的缝隙里遥望远处闪烁的灯火。
黄昏的街头弥漫着梧桐叶的气味,当天色接近昏暗时,人声的浪潮便掀起层层交叠的浪花,覆盖住霓虹交织的小城。
我穿过斑马线,走出屋子,又转回来。
沉沉暮色把我托起,街灯的光,在微风里漾着小小的涟漪,仿佛空中飘起一小朵、一小朵无根的红莲。
我站在玻璃门外,疾驰的车流,在我身后汇聚成一条河。
我站在玻璃门外,再也无法慷慨地回赠我的岁月。
它们,寂静地存在于一切轮廓模糊的事物之间。白色台阶落满了栎树的花儿,当鸽子回巢,所有关于象征的描述,开始进入静止的状态,它们,凝结成一袭粗粝坚硬的布匹,然后,等待一切可能出现的声响,细细地划出一道裂缝。
我已经不再质疑这一切。穿过斑马线,走上台阶,我站在马路的尽头,遥望远处起伏的地平线。昏黄的灯光在微风里摇曳,梧桐浸润了烟火的温情。它们存在着自身本该存在的样子,它们向我涌来,又迅速退去。它们在来去之间,传递彼此存在的暗语。
然后,又自己悄悄地抹去。
然后,来去的路逐渐变得舒缓,它们朝向浩瀚的天宇,轻轻地抖落季节的音符。
我想,这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也在来去的路上,在时而稠密,时而轻薄的时空里,织就一次回眸的瞬间。
2021年11月13日下午4点:晴
当我停止了思考,风,开始在我的周围盘旋。我无法辨别它的方向。它,一层一层地穿透我的皮肤,抵达我的体内。
现在是下午4点钟的光景,阳光正在缓慢地回缩,风的力度,让空气具有了质感。阴影越拖越长。
我站在走廊上,视线,掠过一片朦胧的金色,一片在模糊的光影中荡漾的原野,看向远方。另一座城,另一片烟火。
当暮色开始浮动,当那些面孔转身面对生活。
我停止了想象,让所有的思索缓慢地降落在大地,眼前的这一切开始变得柔软,如同一匹光滑的幕布,被风轻轻地掀起一角。
真相与华丽的掩饰,都如此合理地陈列在原本的位置上。
然后,一些不易察觉的瞬间,在生命的背后缓慢地蠕动,土地向云层靠近,漫长的地平线把十月切成细小的果块。秋日的晴空似乎带着情人的笑靥,把柔美的脖颈轻轻地探向传说中的冬季。
我停止思索,危險便降到最低限度。但我的胸口,似乎有一层薄冰在裂开,它开出了花朵的形状,风,传来了某个港口的哨音。
那些陌生的面孔,在来去之间织就了一场浩大的雪夜。掌灯的行者,把灵魂交给上苍,把身躯匍匐在繁密的岁月里。
其实,我们都是在灯影的虚薄处跋涉、寻觅的路人,当我们偶尔交汇,世间,便有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