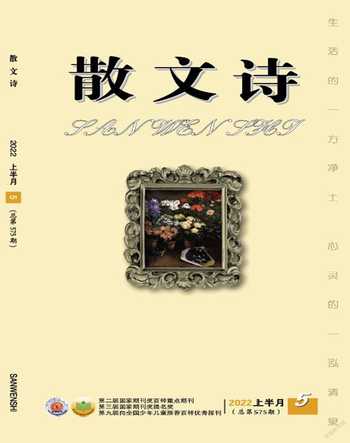滩涂地
姜桦
九月末,海边草原
九月末,走过海边草原,大米草的叶子在水边渐渐变得枯黄,阳光中的绿色,被一阵秋风悄悄运过那面倾斜的土坡。
侧身于草丛的雏鹤正在安静觅食,或者四处张望。天空掠过晚霞的鞭子,轻轻落向远处的土岗。
秋天,身边的云断断续续,头顶的天空也那么不着边际,只有我不声不响站在这里。回望生活,如翻阅一页页发黄的草稿,时间,让一张熟悉的脸庞带着一些不同寻常的褶皱。
人过中年,一条河已经流过了急弯。不再不着边际地幻想、憧憬,也不再无端地抱怨。走过海边草原,把一切都放下,想象自己是一粒即将掉落的草籽,迎着秋风,我所能做的,就是任其腐烂,或者重生。
中秋夜:望月
月亮不小心踩碎了这满地撒落的芝麻花,窗外的银杏树,那些金黄的树枝,绝不会错过天空。
躲过云层的果实悄悄改变着星星的位置。一匹藏进月光的白马,寂静的秋夜,那一只胖乎乎的蝈蝈有青草绿的嗓子。
中秋夜,我坐在石阶上看月亮,从东边的海面,到西边的山顶,风儿嘟着嘴巴,唱起一首首小情歌。
白象漫游,满河成熟的绿菱围着新藕。
一大片湖水在头顶上打旋,桂花浓郁的香味很难被谁移开。
海边芦苇
海边芦苇用稠密的根须紧抓住脚下的泥土。茂盛的枝干,除了搭起一座坚固的城堡,还将过滤下白花花的盐。
海边的芦苇是坚定的。犹如一块石头身处于波涛中心,再大的风浪都掀翻不了它。
而它们的站立,并非为了成为灯塔,只是为了能够让漂泊的风,靠向渐渐远去的岸。
生活在海边,我从来不会把芦苇写成植物。
在粗暴肆虐的大海面前,生命如此脆弱,连最大的天空都会被击碎。
只有那些芦苇,一次次抬起它们倔强的头。
给大海盖满雪
夕阳下的大海透着蒸腾的热气,我却要在它上面覆盖上雪。一条残腿搁在颠簸的浪头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迟钝的中年。
跟着那些云,大海上堆积着鸟的歌声。海水从沙滩上轻轻掠过,涛声再大也带不走它们。
在海上,死亡总是不可拒绝。是谁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阴影是死亡本身!”
犹如苦难是生活本身——哦,又是谁,给大海盖满了雪?
一个想法如一阵狂浪,在渐渐裂开的身体里颠簸。没等我在诗中写下这个句子,一场雪,已自己落满了大海——大海从此多了金子。
每一朵浪花都是金子。风吹来,金子在裂开,回避与逃遁都无济于事。
海边的云
如果确定存放不下,我们就退回去,退回到海上去,退回到天上去。大海的潮涨潮落,只是为了给滩涂和远方传达一封口信。
菊花和芦梗结成花环,大海留出无垠的花边。众鸟远离,这壮丽的辞别,一朵朵浪花被我捧在了胸前。
退回去,退回到海上,退回到高高的天上去,纵然离开千万朵浪花,我都会说我曾经来过。一万年、一百万年以后,所有的浪花和水鸟都消失了,那只海龟还会驮着一片月光。那枚贝壳,也依旧会完整地保存着大海的回声。
大海,浪花的母腹;天空,云彩的故乡。我曾和大海唇齿相依,和寂寞的海滩,默默交换永不消逝的爱。
枯枝牡丹
海边土岗,一株生长了700年的枯枝牡丹。枯枝上的牡丹,一个不可拆分的词,可以点火,可以凝霜。今晚,坐在雪地上劈柴的人,头頂的月光,被他看成是一片流星雨。
除了一节枯枝的身体,谁愿意接受开花的念头?春寒的风中,又会有谁将我收容?一朵花蕾靠近一根树枝,一只嘴唇紧挨一块石头。一些枯枝,一束牡丹,只有在冰雪开口之后,它们栖居的这片园子才能回到葱绿,这树枯枝才能证明自己年轻过。
在春天的黄昏默默走近它,像一片雪独自坐在枝头,像一片月光紧靠在山腰,将一只唇印留在最黑暗的角落,跟着一个爱过的人,我们,重新回到曾经住过的地方。
白菊花
十月,在滩涂上采摘野菊花的女人弯下腰身。当阳光温柔的指尖悄悄抵达,她们会将那些白色的菊花轻轻拥在胸口,也一并将整个秋天揽在了怀里。
白露刚过,时近秋分,大片的芦苇花还没盛开,于是,菊花先成为秋天的主角。在大海边的滩涂上,菊花的白是从一群女子的指尖直接进入身体的,碗里盛着药汤,一股凉意留在我们的肝、脾脏和胃。
整整一年,通常我不会直接写到菊花。只有到了秋天,遍地菊花,才会被一阵阵秋风一次次想起。
海边禅寺
海边,诵经声稳住这座千年古寺。透明的月亮悬在一棵大树上。那株象征世代平安的银杏树,金黄的叶子正扑簌簌洒落下来。
听一地落叶,如听一条河。那略带节制的水声,一个下午就像是一千年。大海边,那被一条运河串起的一个个盐场早已不见,但流水还一直横亘在这棵大树脚下,那条古盐河,一直还叫做从前的那个名字。
整个夜晚,我一直坐在窗前,静静地看着那轮被流水放大的月亮。河流节奏放慢,伴随夜虫低低的诵唱,我在安静的血管里,翻找最后一把盐。
秋风冷
凉爽的天气突然变冷。仅仅只是半个下午,院外的那些树叶,都被涂上一层冷艳的红。
坐在一张墨绿色的布艺沙发上,我小心翼翼地往踝关节上抹草药,如一条蛇游进骨头,所谓的草药,其实就是一把采自乡间的野草的汁。
只是,它来自一百里外古黄河岸边的老家,来自带着野菜味道的少年。
一座小桥横亘河面。那两只桥孔多像我母亲的眼睛。从地里归来的母亲,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野草,一路急匆匆跑回来的样子。黑色瓦罐依旧翻滚着药汤,仅仅就是这么小半个下午,我摇着粗实辫子的母亲,已白发苍苍,如此老迈。
几十年过去,一把来自乡村的野草,它的汁液还是绿色的。凉飕飕的秋风灌进脚踝,门前那棵柿子树,靠向大地的一面,那些叶子还没有完全红出来。
大海不会轻易抹掉一个人
哪怕是你自己走到了波浪深处,大海也会一次次将你还回来。
还给海湾!
还给沙滩!
幽僻安静的地方,折断的树枝,被波浪摆放得整整齐齐。
草地上的野花,兀立树顶的白鹳,你我都是大地深情生长的植物。
泥土,用覆盖保存下了一个人;
大海,不会将自由的灵魂轻易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