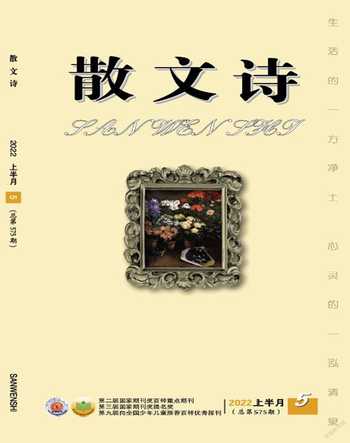时光斑斓
吴春
风铃草
站在大漠的星空下,旧时的衣襟兜着满怀的伤感,英雄无觅,红颜已逝。
这里埋葬着历史的烟尘、房屋和灯火,又在另一个世界里,以不同的面目呈现。
破损的城墙古风习习,天高过山顶,又低于水面,成就一方净土。
风铃草啜饮百代霜雪,存活下来,与骆驼刺、芦草一起,忍受着大漠荒凉干旱的压榨,从容开出洁白的花朵,像一颗心,始终怀着美玉。
它让大漠戈壁温情敦厚起来,让爱情美丽起来,故事里的纷繁,也被简化成了两个人的名字:樊梨花,薛丁山。
一株风铃草就是一串跌落的马铃铛,等一场搁浅的风花雪月,被柔情征服了的身体,状如蒿草,提起数盏亮晶晶的明灯,纤尘不染,为自己,也为尘世,开启一缕微光。
风铃草一路躲避秋风的追杀,风越紧,它的反抗就越有力,口含激烈的呐喊,响成驼铃声声。
世界,由此安于一條长长的丝线上。
烽 燧
锁阳城东北角,有烽燧立于城墙,一身孤傲,看尽烽烟,看尽斜阳。
烽燧中间留有一个门洞,像一只干涩的眼睛。
站在门洞内避风的站岗士兵,宛如眼中黑色的瞳孔,不停警惕地转动。
风吹过,吹薄了壁垒,吹薄了汉唐的衣衫。
别说英雄无泪,其实,英雄都有一副古道热肠,总在家园受到侵略的时候,一马当先。
无数个陷落的日子,烽燧,白天吐出烟雾,夜晚高举火焰,送走春夏秋冬,寄走戍边兵士对家乡的怀念。
春日,锁阳城披上碧绿的罗裙。在夏日,换上多彩霓裳,有雨雾,有升腾。凉薄的心事,被微醺的情怀撞得醉不成诗。
城破了。
城墙下,是双方阵亡将士的尸骨,他们把血肉归还给了大地,借助旺盛的草木完成对心灵的救赎,并宽恕了客留异乡的自己。
一千多年过去了,烽燧依旧挺立着,它替古人守望未来,把锁阳城看作九万里河山的缩影。
红柳,饮尽月光
背着光阴行走,在无人怜惜处,暗自抚摸一路的创伤。
以盛大对抗荒凉,走在易衰的草木之间,为自己的灵魂撑起一片吉祥的云霞。
内心的火焰雕刻在脸上,沉淀下来的朱砂红,代替了葱茏的生活,代替了流年的风风雨雨,遗世独立。
古城之上,羌笛声渐远,铁马冰河也不曾入梦。移动的太阳,年复一年,收割满城人语春光,收割清冽的酒香。
穿着铠甲,手持长矛的将士,在两千年前驻守的丝路重镇,完胜风霜雨雪的侵袭。遍地芳草,以奔跑的姿势,接替士兵站岗。
高高低低的红柳,饮尽月光,成长为风华绝代。
尽管开花的时候没有香味,低吟的时候没有听众,但它选择了大漠,就等于选择了孤独,选择了广阔。
红柳抱紧内心的火焰,直面瀚海黄沙。它的存在,让一座废弃的城有了动力,有了永恒不变的精神。
古河道
一路收集雪山圣水,拜谒山石,凭借内心的辽阔,流向更为宽广的辽阔。
一条河生出数条河,身体被划分成有形的疆界,被冠上了不同的地名,用几千年的时间完成一生的承诺。
她流经的地方,必定有鲜花,有草地,并引来无数的牛羊与炊烟。
水,接受了贫瘠抑或肥沃的土地,以流动的方式,证实她对人间的热爱。
也曾涉足山涧、平原、戈壁、沙漠,平凡的日子有暗香盈袖,亦有如诗吟叹。
有人为了满足野心和欲望,迫使流经锁阳城的河流改道,斩断了疏勒河的一条臂膀。
时光陨落在这里,土地失去原有的气色,一座城呈现出废墟的面孔。
天地空荡荡的,牛羊归去,田地空阔,遍地骆驼刺用尖刺迫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撑起一片向晚的天空。
偶尔赶着牲口经过的人,如天地间移动的逗号,拖着铿锵有力的句子,被人反复吟诵,修改。
干涸的古河道,匍匐在荒草、砂砾、大漠中央,不问今夕何夕,不问俗世沧桑——
它,始终保持着流淌的姿态,替锁阳城披上了一件挡风遮雨的衣裳。
塔尔寺
缭绕的佛音,让远方拥有了纯净与安宁的情怀。
与锁阳城仅隔一公里的西夏大型寺院——塔尔寺,隐身荒漠中央,普照着塔尔寺的月光同样也照着锁阳城,正如一幕盛大的道场连接另一幕盛大的道场,安慰彼此虚空的岁月。
塔尔寺,身前是巍峨的祁连山,身后是纵横的阡陌。
晨钟,晕染彩色的旋律,撞响一天的慢时光;
暮鼓,让一只鸟找到了回巢的路,找到了属于它的宁静。
坐在佛前的人,从内心的高地俯视人间,认清一切苦难的根源,轻轻拨亮身侧燃烧的油灯,让肉体与精神合二为一。
风雨来临。
嵌入每个砖瓦缝隙中的禅音,不着痕迹,阻挡着其对塔身的侵蚀,殿宇、塔群承接阳光,吸收精华,长成不坏之身,走过风云变迁的历史,并沿时光的经络,找回失落千年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