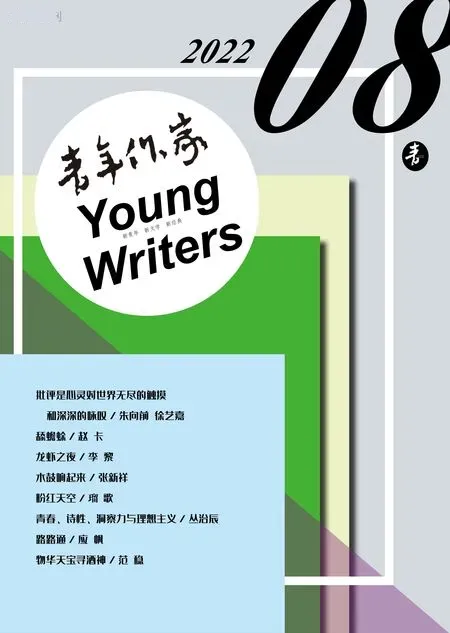城市是斑鸠的吗
周万水
城市是属于斑鸠的吗?不好说,现在城市里住着很多斑鸠,说城市不是它们的,的确也说不过去。
城里有斑鸠,也有蝉。蝉是很吵闹的。夏天,城里有树的地方,蝉的叫声都是铺天盖地的,像张网,密不透气,连一丁点风都漏不下来。那些树一动也不动,每片树叶都在单调嘶哑的蝉噪共振中隐忍着。它们始终步调一致,巨大的树冠里,到底藏着多少只蝉始终是个谜。仅就数量而言,这城市更像是那些蝉家族的领地。
与蝉叫声的浮躁和无节制的大合唱相比,斑鸠是很克制的。我的楼下就有一些斑鸠,它们都住在树的高处。小区里的树多是常绿的,有樟树、杜英、女贞、桂树和广玉兰,有着葱郁树冠的樟树和浓密枝叶的杜英树都是很适合斑鸠筑巢的。斑鸠的声线极富磁性,辨识度很高,低沉而徐缓,“咕咕咕”“咕咕咕”的,沉郁悦耳,哪怕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仍有很强的质感。一听就会让你想起雨后某个乡村的早晨:山前一抹湿润的岚烟、水田里耕牛的倒影、泥路边豌豆花上的露珠……脑海里顿时生出“斑鸠声里叫春晴,绿水如环抱画城”的意境。
我知道那些斑鸠就住在我家附近的树上,我还是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棵树。它们的声音立体感很好,却又带着些隐秘性,你很难准确判断那“咕咕”的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的,尽管那些高大的树枝几乎接近我的阳台。我经过那些树下,有时刻意停下脚步认真聆听,那“咕咕”的叫声仿佛就在某处,却还是无法判断,那听上去有点飘忽的声音来自哪片枝叶。后来看约翰·巴勒斯《湖畔小屋》,羡慕不已。很显然,我没有约翰·巴勒斯对自然的那种惊人观察力,他能区别湖水在一天内细微的颜色变化,而在寻常人看了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蓝。他聆听一只歌雀的吟唱还可以有视觉上的感受:“我追寻过去,发现一只吟唱的歌雀,这歌声悠长清晰,激昂有力而又甜美凄婉,宛若一条长长的弧线。”约翰·巴勒斯甚至能够通过歌雀的声音判断是去年的那只歌雀又回到了那片栖息地,在他的意识里,他和那只歌雀有着某种天然的感应,当然不只是一只歌雀,还有那些同样蓬勃在自然里的每一种生命,它们每一次的回归和复苏,都与人类心灵的期待有着神秘契合。这是他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结果,是他注视、聆听、触摸获得的感受。我们不具备这种能力大概是因为远离自然太久,感觉已经迟钝和退化。
在城里,高楼密密麻麻,生活在这里的人,理论上是有很多邻居的,可大多数其实也就跟陌生人差不多。彼此隔离着,都不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在各自平行的几何空间里忙碌着。只有小区树上的斑鸠大概算得上大家共同的邻居了。每年我们都能听到斑鸠的叫声,有时还能在地上的落叶间看到它们觅食的身影,多是那种褐色的珠颈斑鸠,脖子上围着一圈黄白色的斑点。它们小心翼翼,不是因为害怕人类,而是源自城市寄居者天然的警觉。在你还没看清它们模样时,它们便急速离开,只瞥见展开的尾巴露出一圈白色的羽毛。当然,我们还是没法辨别这个春天在树上鸣叫的还是不是去年那只斑鸠。那些落在地面上的叶子倒是跟去年没什么区别,斑斑驳驳的,细细一看,每一片都酷似一幅抽象画。
我有时觉得,那些斑鸠像极我1103单元那户神秘的邻居,他们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却一直很陌生,偶尔看见也就一匆匆的背影。这单元共有四户人家,对门是一家三口,一对夫妻和一个女儿。他们住的这套房子是租的,原来的住户是一个独居老人,儿子常年在美国,后来老人去世,房子也无人看管,就低价租了出去。这两口子在附近开了间“小珊快餐店”,早出晚归,难得一见。小珊是他们读小学的女儿的名字,她的作息时间跟她父母很一致,都属于那种起得比鸡还早的人,一年下来能看到他们的时间很少。她十岁了,梳着两条小辫子,遇到我总是很短暂地一笑,然后就是一副跟她年龄极不相称的行色匆匆,走起路来,搭在书包上的小辫子一跳一跳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错把斑鸠看成是鹧鸪,后来才知道这有多么风马牛不相及。鹧鸪是一种体形很大的鸟,还是一只与诗共生的鸟。“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因叫声凄清惊心,自唐宋以来,这种鸟就一直在诗人忧郁的情绪中出没,千百年都没飞出那空旷孤寂的羁旅,充满各式各样的离愁别绪。我没见过这种鸟,却总是与它在一些典籍中不期而遇。它不时从某一行文字中飞出,藏在寂寞的时空里,津渡寥廓,驿馆孤寒,叫声里夹带霜月亘古的清辉。后来,我在网上听到过鹧鸪的叫声,完全体会不到那种古老的忧郁,没有了颠沛的情境和体验,我们与那些古老的诗意终究还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与鹧鸪相比,鸠也算是一种频繁出入古典诗词的鸟,从《诗经·召南·鹊巢》的“惟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和《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唐诗里的“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但这里面的鸠,多数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斑鸠。有的可能是布谷,有的可能是杜鹃,还有可能是八哥或云雀之类。在古代是没有现代生物学概念的,人们对鸟类的划分大概只是凭感觉粗略归类,诸如鸠、鹊、鸦等等。鸠大概就是今天鸠鸽科中体小尾长,属于鸽子表亲的那一类鸟,斑鸠不过是其中的一种。随着人们对鸟类的细分,现在的“鸠”几乎就是特指斑鸠了。
与鹧鸪相比,斑鸠现在已经是一种很平民化的鸟,它早就飞出了《诗经》,成了人间一只很普通的鸟,离我们世俗的生活更近,更接近田垄和炊烟。当你路过一棵树下,能听到斑鸠的叫声,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很真实。毕竟我们活着的状态还是需要有些轨迹来证明的,就如一阵风吹过无声的原野、一只水黾掠过安静的池塘。可见世间万物,彼此都是参照,不同的只是它们栖息的姿态。
几乎所有的鸟都是酷爱阳光的,斑鸠也不例外。我们几乎不知道,在有下雨、飘雪和刮风的天气,它们是如何生活又如何死去的,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让雨水打湿羽毛的,让它们的巢穴不被树上的积雪压垮,它们在大风中又保持着怎样的身姿……这一切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关于斑鸠的故事,我只听说春天樱桃熟了的时候,它们会因贪食太多樱桃醉醺醺的,变得容易捕捉。至于传说中的“鸠占鹊巢”的主角其实不是斑鸠而是杜鹃鸟。不过据说斑鸠对筑巢确实不是很讲究,它们很擅长寄居,这让它们的迁移变得比较随意。
在所有那些气候恶劣的日子里,你是很少能听到斑鸠的叫声的,它们好像已经逃离城市或从来不曾存在。在那些潮湿阴暗的日子里,你带着烦恼走过那条熟悉的小道,忽然听到斑鸠久违的“咕咕咕”叫声,心情顿时变得愉悦,因为你知道好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阳光又将穿过树荫,洒满潮湿的地面。古人说“今朝雨声绝,又听斑鸠啼”诚不欺人。我们未必能够听懂那些鸟语,可我们知道那一个时刻,斑鸠和所有的鸟叫声此时都透着欣喜。在很喧闹的都市里,一天的好心情是可以从一声鸟叫开始的,从这点来看,斑鸠算得上是个好邻居。
晴好的日子,斑鸠声里,树叶缓慢飘落,铺在树下的石凳上。石凳上通常都会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扶着杖,安静地享受着余生的阳光。不远处一只花狸猫眯着眼躺在女贞树稀疏的光影里,对斑鸠的声音无动于衷。女贞树的花是浅黄色的,由无数米粒大的花簇拥而成,每遇风过,或一只鸟儿落下,花粒便从叶间跌落。猫的皮毛上也覆盖上一些花粒,它眯着眼,一脸不耐烦,不断地扬起爪子划拉着那些从空中落下的细小花瓣,还不时对树上的动静保持着警惕。这里是小区里老人常聚集的地方,他们都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牌或者唱歌。傍晚时,空地上就成了孩子的领地,他们在那里追来逐去的,嬉闹声散落一地。他们的来历和生活轨迹跟栖居在树上的那些鸟很相似,很多人原本不属于这座城市,住在一堆比树更高的楼群里。
斑鸠和麻雀、布谷一类的鸟都具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背景,它们和现在城里大多数人一样,不是城里的原住民。它们的传统居住地通常在山地、山麓或平原的林区附近,也会在接近人的集居地和村庄周围的边缘地带活动。我的童年就是在乡下度过的,在那里人们把斑鸠叫作“斑鸡”。鸠可入诗,鸡差不多就成美食了。一字之差,尊卑处境迥异。据说斑鸠肉质鲜美,还能治偏头痛,常常被人当成一种野味猎食。斑鸠种群数量不是很大,也不喜欢成群结队,所以知名度远远不及体量更小、数量庞大的麻雀。一个种群过于兴盛,总会招来一些麻烦甚至灾祸,麻雀就是一个例子。小时候,乡村里的麻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山林、草丛、田野、屋檐、晒谷场,包括城市的公园,到处都是它们的领地,这种其貌不扬的小鸟,机灵、胆大,毫不忌惮人类的存在,也最易受人类攻击。我当年那些小伙伴的弹弓几乎都有射杀麻雀的记录,它还曾被当作“四害”遭到大规模捕杀,差点被搞得灭了族,等到后来平反,乡村的麻雀已日见稀少,一度成了人们怀旧的对象。
一度受到惊吓的斑鸠们一直都很小心地生活在乡村,努力避免成为人类的食物,尽管也曾经受到麻雀连累。与人类共享生存空间带来的好处总是大过潜在的威胁。随着乡村农耕文明某种程度的衰退,一些斑鸠开始寻找新的生活空间,城市也不例外。这是它们经历无数次生存危机所作出的本能选择,所有动物都是如此。我们也一样,在永恒的自然面前,众生都不过是暂时的寄居者。
追寻城里斑鸠的来路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我居住的小区旁边一条是铁路,很多年前还是城市的郊野,现在,高大的建筑和街道代替了原先的山林和荒野。一些鸟继续向城市边缘的乡村迁移,一些鸟儿在仅存的绿地上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这里面当然包括斑鸠。和那些突然拥有城市户口的城中村的居民不同,斑鸠们是不需要上户的,它们有迁徙的自由。只要有翅膀,有树林和天空,家园大约只是它们一次飞翔和驻足之后的选择。所以,有些斑鸠可能是来自很远的地方,它们迁徙的理由,或基于生存或基于自由。它们有的可能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有的则在这里长期生息繁衍,有了二代、三代、四代……最后成为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平行空间的主人。
夜晚,当城市稍稍安静下来的时候,火车穿越城市的轰鸣不时传来。透过桂花树的淡淡清香,偶尔也有斑鸠的叫声,那声音有些撩人,会让你微微泛起些愁绪。你无法分清那缕愁绪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斑鸠的。这里可能也不是它们的原乡,它们是否也有“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牵绕?当然,这样的情境是不常见的,喧闹的城市一般不会在意一只斑鸠的情绪的。
在城市里,河流是熙熙攘攘的人,每天匆匆邂逅的人都是有迹可循的,只不过他们的来历更加复杂。就像我这个曾经的乡下孩子,后来进了县城,再后来又到了省城。我1103那个开快餐店的邻居、在小区里晒太阳的白发老人,还有那些匆匆来去的快递小哥、送餐大哥,每一次开门,见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面孔,说着夹杂不同口音的普通话。他们大多都有相似的经历,来这个城市的理由要么是因为生存,要么是因为梦想。他们中间很多人永远不会有城市户口。户口这东西,红色的塑料皮夹着几页纸,却能决定大部分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没有对应的户口,你永远只能是某个地方的寄居者,那种不安就像小时候在小河里游泳,一只“嗡嗡”叫的牛蝇不断地围着你转。
我是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的。少年时,我从乡下进城读书,也曾是一个寄居者。一次,隔壁班一个同学试图欺负我,班上一个同学站出来恶狠狠地替我出了回头。这事儿过去数十年了,我仍然心存感激。后来这位同学成了一名军官。一次见面时,我很感激地对他说起这事,他居然不记得了,说:怎么?还有这事?他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自然不知道这件事对一个乡下孩子的心理是一个多么大的支撑。就像下雨,重不重要,雨本身并不在意,只有地上的那些草木才知道。
我的邻居还是早出晚归,他的快餐店是在附近一片棚户区旁边,周边是一些小理发店和茶馆。说是茶馆,其实就是小市民打麻将的场所。那地方是个老厂区,路边有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曾经有过很多家小印刷厂,如今几乎都倒闭了,低矮的房子被改造成许多门面,写满旧标语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最多的是治疗各类皮肤病的。有几次路过,远远看到他们两口子在店里忙碌着,生意好像不错。离开很远了,稀里哗啦的麻将声还在耳边回响,中间夹着一个长沙女人的吆喝声:糖油粑粑,臭干子……不远处,一个住宅小区正在修建,一些头顶红色安全帽的身影在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中晃动着。
按照城市规划,这块棚户区很快就会消失,在城市里,那些高楼总是比树要长得快。
上楼下楼,我还是能经常碰到邻居家的小女孩小珊。我写下这些文字就是受了她的启发。据说她的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好朋友》,别人都是写的张三、李四,只有她写的楼下树上的斑鸠。当然,老师的评价说她是胡思乱想。我没有读到过这篇文章,但我觉得她说的是真话。她从乡下来到这座陌生的城里,斑鸠大约是她记忆里最熟悉的事物了。我理解她对于那种鸟的感情。就像我当年从乡村来到城里,看到一只麻雀都会觉得有久违的亲切。她每天都要从那些树下走过,那些斑鸠就在树上,“咕咕咕”的叫声落到她书包上,被她独自背到学校,又被她背回家中。我想她的语文老师很难理解孩子敏感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一个孩子,觉得一只斑鸠是她的好朋友,一定有她的道理。这种想法只属于很少的人,因为大多数人因为习惯会变得迟钝,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这么诚恳地对待一只素昧平生的鸟。这孩子的心就像记忆中的乌桕林,田野荒芜,林下的草很软很软,她的梦静静地升了上来,她希望那些翅膀驮载的阳光是温暖的……
我一直想对她说:你那篇作文写得真好。
我不是一个鸟类爱好者,对这个城市里寄居的大多数鸟类,都叫不出名字,从它们翻飞腾挪的姿态中我不能确定它们的身份,也记不住它们的样子,就像那些每天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瓦尔登湖,一些人前往,一些人放弃,真正能抵达的人并不多。当自然被微缩在公园和绿地里,在城市里想象自己的《湖畔小屋》,大半都是矫情的,完全没有了生物学的意义。人是很奇怪的物种,有些东西,我们宁愿想象和怀念,也不愿去真实地拥有。我们离开乡村,我们让乡村凋敝,我们砍掉那些树,让老房子烂掉,然后待在一个混凝土搭建的空间去怀念自然。这很像《雷雨》中的周朴园怀念侍萍一样,你不能说是假的,说到底还是不想拥有。我知道这其中必然有许多无奈,如果我真的是一只斑鸠,我又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不好说。时间总是往前走的,过去的日子是因为回不去,才让我们格外怀念。
那年,好事者在城市五一广场仿修了一条小溪。我看着一大群孩子打着赤脚在那里快乐地玩耍,不免心生怜悯。那不是一条真正的溪流,没有湿润清新的自然气息。水里没有小鱼、小虾和螃蟹,岸边也没有灌木、苔藓、芷兰和菖蒲,但孩子们却是开心的。这条人造的小溪早就不在了,相信还有人记得它。现在,很多孩子衣食无忧,备受宠爱,却唯独少了开心。缺少了对真实自然的体验,他们的生命当然是不完整的,这其中也包括城市公园里的鸟二代。
年前,邻居告诉我,他们要离开了。这两年生意不太好做了,那片棚户区改造后,门面租金也很贵了。他们打算去宁波打工,让孩子回老家读书。还说孩子可能不太习惯城里的生活,有点抑郁。我问他们,孩子有什么表现,他们说也没什么,就是不太爱说话,还经常问一些古怪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死了,我那几个娃娃(布娃娃)怎么办?我笑着对他们说:呵呵,没事,孩子长大了。
我是有过类似经历的,不免有些心疼这个小姑娘了。她还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些不时袭来的阴影可能还要折磨她很久。
走的那天,一家人向我道别,两只很旧的行李箱拖在地上轰隆隆响,让人想起曾经坐过的那列绿皮火车。小珊倒是很开心的样子。她背着书包,抱着一个大白鹅布娃娃,朝我招了手,怀里的鹅脑袋不断地点着头。我不确定小珊是不是在心里跟那些隐藏在树上的朋友道过别了,那天天气不是太好,没听到鸟叫。
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某个城市,得到善待和获得生存的空间。一些人还会不断地迁移,在不同的城市寻找下一个栖息的地方。城市是不会感知到他们离开的,穿梭来去的火车、大巴,把一些人带来,又把一些人带走。在乡间,关于斑鸠还有一句谚语:草窝里的斑鸠,不知春秋。这句谚语对斑鸠是不公平的,春秋是什么,不就是活过来的日子吗?城里、乡下、树上、草间,都是日子,也都是春秋。
我可能还会待在这座城市里,曾经的邻居自此消失,这样的流动每天都会有,我希望那两口子能挣到大钱,从此有一个安稳的家,也希望小女孩能够找到更多的快乐。
当又一个春天来了,天气晴好的日子,楼下的绿荫里还会传来斑鸠们的叫声,我依然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是我去年看到的那几只,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