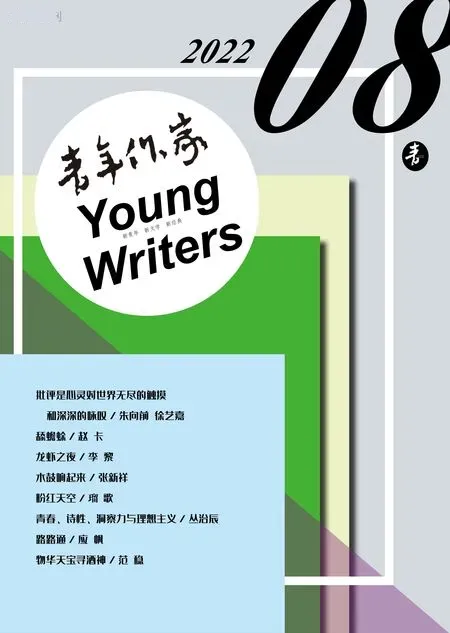未来主义诗歌运动
瑠歌
在墨西哥北部的沙漠里,一个高大的男人,正拖着半死不活的肉体,行走着。
阳光照在眼睛里,使他看见了一幕幻觉。
他觉得自己在完成一幅作品,主题是在沙漠中行走,观众就是自己。
这幅作品无法被保存下来,完成之后,他就会死去,他也无法说清楚,自己从中体验到了什么。
这或许不是个糟糕的结局——他得意道,完成了某种成就后,随之而来的死亡也就不值得怜悯了。
他甚至认为渺小的死法是应该的,当你成就了一件伟业时,结局不应该是一场戴着花环、受万人簇拥的葬礼。
地上有一只干死的猫,使他从幻觉中回过了神,他意识到大脑开启了自救模式,如果一直清醒地看着没有变化的沙漠,他的肉体一定会放弃抵抗。
他迈动双腿,咒骂着太阳,继续行走。
在夜晚的风刮起之前,男人找到了偷渡者说的洞穴。
他躺了下来。
举起水壶,朝喉咙里灌了下去,又从怀里掏出一块饼干,捏碎,撒在嘴里。耳边传来呼啸的风声,头脑陷入了昏迷。
醒来时,他的背像一块断裂的木板,被乱放的玫瑰花刺刮得伤痕累累。他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意识到自己在沙漠中,接着站了起来——双腿的剧痛没有丝毫消退。他看着洞穴外的阳光,惊恐地走了出去。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他必须赶在凌晨之前越过边境。
太阳照在头顶上,他却无法再像昨天那样,将自己幻想成一个伟大的人,他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只剩下风打在肉体上的感觉。
几个小时后,他听见了一声轰鸣,趴在了沙丘下。
是边防部队的车,他们下车了,正在朝这里过来。
他感觉边防部队的人就埋伏在沙丘后面,拿枪对着他。
过了不知多久,他站了起来。
四周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只秃鹫。
到了傍晚,男人终于来到了墨西哥的终点,前面是一排铁丝网,后面是更多的沙漠。四周没有一个巡逻的士兵,在看不见的地方,哨塔上的人在检测着铁网下的一举一动。
他埋伏在一块岩石后面,静静等待着午夜的到来。
风刮起了地上的沙石,他用披肩盖住了自己。沙漠上升起了一轮清冷的月亮,一层紫色的薄纱映在天空中。
几个小时过后,他醒了过来。
周围是一片接近永恒的黑暗,正是那种他日夜在沙漠里已经熟悉的黑暗。他朝着铁丝网的方向看去,那里有一些微弱的灯光。
他看了下手表,现在是一点过十分,哨兵们正在换岗。
时间稍微晚了一些,他开始朝着铁网奔跑。
在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奔跑后,来到了铁网前。
他将披肩取下来,缠在了手上,爬了上去,很快又滑了下来。隔着披肩的手指无法有力地握住铁网。他犹豫了两秒钟,赤着手爬了上去。
铁刺离他的鼻子只有一厘米不到,他取下肩上的披肩,盖在了铁刺上,大叫一声,从上面翻了过去。
凌晨一点十九分,一个墨西哥人落在了阿美利卡的土地上。
他的披风被挂在了铁丝网上,裤腿被划破,衬衣被撕烂,肚子上和手臂上流着鲜血,在茫茫黑暗中,朝着前方走去。
走了十公里后,他来到一条公路旁,在路灯下,他发现自己浑身血迹斑斑,双腿几乎失去了行动力。前方有一座亮着灯的广告牌,他朝着光亮爬了过去,鲜血滴在沥青路上,他爬到了一座小旅馆前,用尽全力站起来,推开了门,顺势倒在了柜台上。
“水……”他用浓厚的墨西哥口音,拼出了一个单词,这是他在阿美利卡说的第一句话。
脸一直对着墙的女招待转过了头,她的表情就像得了厌食症一样。
“你的血蹭到地板上了。”她说道,转身进入柜台后面的房间,取了一杯冰水和一瓶酒精出来。
墨西哥人的双手撑在吧台上,视线正好对着女招待的锁骨与胸口两个紧致的乳房。
“没事,我其实没流多少血,差不多都干了。”他的话里夹杂着许多墨西哥语,使女招待一句也没听懂。
墨西哥人将冰水一饮而尽,冰冷的水顺着他的脖子,流到了胸口的伤痕上。
“先进来吧。”说着,女招待把他扶进了过道,放在了一座破沙发上,女招待身体的触感,顺着她的肌肤传了过来。
“你可真够沉的,牛仔。”她喘了口气道。
他沉甸甸地躺在沙发上,女招待撕开了他的衬衣,将碘酒洒在上面。
“哦……”他发出了漫长的呻吟,就像与某种甜蜜又痛苦的玩意儿在调情一样。
“忍耐一下。”女招待说,“不要乱碰,否则感染了……”
伤口被简易处理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枚破碎的纸币,递给了女招待。
“这些钱只够你住三晚上的。”她说。
“足够了。”他说。
“谢谢你。”女招待说,随后从前台的柜子上取了一把钥匙,递给他。
“自己能走么?”她问道。
“谢谢你,我没问题。”他说。
之后女人回到前台,拿出一个墩布,开始清理地板上的血迹。
腿部逐渐恢复了知觉后,他迈着艰难的步伐来到酒吧,酒保是一个神色淡漠的女人。三个胖子围在一张桌子前低声细语,没有人在乎他走了进来。
“一扎啤酒。”他说。
神色淡漠的女招待接了满满一大杯酒浆,递给了他。
他举起啤酒,一口干了下去。
哦,阿美利卡,阿美利卡,他的味蕾有些失效,尝不出来,天堂的啤酒与墨西哥的有什么区别。
“看见那个墨西哥傻大个了么。”在酒吧的角落里,一个俊俏的男人说。
“你说哪里?”黑发女人将紫罗兰色的瞳孔望向了吧台,在此之前,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的男人。
“你是说坐在吧台上的那个大个子么。”
“没错,墨西哥人,连夜从墨西哥的沙漠里走过来的。”
“走过来的?”女人的瞳孔微微张大了一下。
“没错,穿过两百公里的沙漠。”俊俏的男人说,“这样的家伙很多。”
女人关切地看着墨西哥人满是伤痕的裤腿,俊俏的男人欣赏着女人天真的面庞。咧嘴一笑。
“他们以为阿美利卡是天堂,这里和沙漠的另一边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看上去很痛。”女人说。
俊俏的男人并没有理会她,接着说道,“让我们喝完这杯酒吧,麻烦再给我买一杯。”
于是女人站了起来,走到吧台边,在等待她的鸡尾酒时,她与坐在吧台上的墨西哥人对视了一秒。
女人回到座位上后,便用右手撑着脸,将她紫罗兰色的眼睛朝向了另一边。
“你感到忧伤么?”俊俏的男人说。
“有一点。”女人说。
男人喝了一口苦涩的鸡尾酒。
“面对这种事情,最好的方式是保持沉默,或者大笑……如果我们哭哭啼啼,或者义愤填膺,一切就会变得很难看。”
女人没有说话,眼睛里微微闪着泪光。
“喝一口酒吧,宝贝。”俊俏的男人摸了摸她的脸颊,将杯子推到她跟前。
女人将散发着薄荷香的苦艾酒,一饮而尽。
“今晚会是个美好的夜晚。”俊俏的男人萎靡地笑道。
吧台上的墨西哥佬还坐在那里。围在餐桌旁,议论着如何赚到钱的家伙们已然离去,只剩下角落里的男人与褐色皮肤的女郎。
一直沉默不语的女酒保,从箱子里取出一张黑胶唱片,压在唱片机上。在嘈杂的声音下,一个落魄的女人,开始诉说起她的故事。
她的抱怨很老套——自己一无所有,每一份工作是多么艰难,每一个人是多么刻薄。今天她被一个暴躁的男人殴打了,明天她又要在宿醉之后,早早地起床,重新面对一切。她的嗓音十分糟糕,激不起一点怜悯。
她带着哭腔倾诉完后,唱片机安静下来,几秒钟后,一种来自蓝色星球的和声开始响起,它与人类的内心不谋而合。
他们所处的小屋,变成了一团蓝色光芒。
女酒保闭上了双眼,坐在吧台上的墨西哥人只留下一道背影,没有人能看见他的脸。沙发上的女郎擦拭着眼泪,躺在她对面的萎靡男人,从兜里掏出一支笔,在暗淡的光影下,在桌子上写道:
音乐是超越了一切知识的启示
唱片停止了转动,女郎微笑着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干净的东西。”之后,音乐又一次响起,结束,他们走上楼梯,拉上了窗帘,在窄小的床上拥抱,音乐又一次响起,在睡梦中结束。
第二天上午九点四十三分,一群吵嚷的墨西哥人走了进来,他们点了许多份啤酒和玉米卷饼。
两个坐在角落,吃着香肠的白人牛仔嘀咕道,“这些老墨,闻起来永远跟玉米卷一样。”
随后,一切开始变得无聊——从阳光、窗台上的灰尘,到哈欠连连的女人。过了一会儿,一队穿黑衣服的人踢开了旅馆的门。
为首的男人戴着黑墨镜,留着胡子,身子骨像一只病恹恹的豹子。
“国土安全局。”他轻了下嗓子,有一种漫不经心的声音说道。酒吧里喧哗的老墨们顿时安静下来。
前台的女招待面无表情地剪着手指甲,无视着陆续进来的队员们。
戴墨镜的长官环视了一圈,迈着他的长靴,来到餐桌前。
一个卷发胖子怯怯地望着他,率先递出了他的证件。
戴墨镜的长官扫了一眼,还给了他。随后,旁边的墨西哥人依次将证件递了过去。长官一一检阅后,最后走到了一个马脸的精悍男人旁。
他抖了抖手指,示意男人把证件递过来。男人瞪着他,缓缓地从衬衣兜里,掏出一张红纸。他拿过去,将那张纸撕成了碎片,接着朝部下们抖了抖手指,几个黑衣小伙子便冲了上来,将马脸男人押了出去。
之后,长官拖着他的黑色长靴,走到吧台旁,瞥了一眼低着头、咬着嘴唇的女招待。女招待什么也没有说,从柜子上取出一瓶十二年份的波本威士忌,倒入一个精巧的杯子里。
长官取下墨镜打量了她一眼,接过他的波本酒。
一饮而尽后,他拖着长靴,走到了坐在角落的两个白人身旁。两个高大肥硕的牛仔,举着手中的叉子,严肃又骄傲地看着他。
“给他们来两扎精酿啤酒。”长官命令道。
随后他走上了楼梯,指示他的队员们敲开每一扇房门。
一个单身母亲在换衣服,士兵闯入时,她柔软的屁股正好对着门外面。一个拥有黄种人血统的壮汉试图抗议,胸口严实地挨了枪托一下。
其中一名士兵走到了走廊尽头,用枪托顶开了一扇门,门是虚掩的,缓缓地张开了,一对熟睡的男人与女人抱在床上,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进来,照在他们的胳膊上。
年轻的士兵沉着脸,缓缓将枪口退了回去。
最后,士兵们站成两排,给长官开出一条道,让他迈着缓慢的大步穿了过去,来到最后一扇房门旁。
门并没有上锁,长官推开门,一个穿好衣服的墨西哥人坐在床边,阳光从窗户照进了窄小的房间里,使他看上去像在牢房里平静地等待余生的耶稣。
长官用锐利的手指摘下了鼻梁上的墨镜,说道:
“你的披肩挂在铁丝网上了。”
随后,墨西哥人在两个士兵的押送下,走出了旅馆。离开前,他想起自己还有两个晚上的住宿费压在前台的女人手上,之后,他望着沙漠无聊的天空——它与墨西哥的那一头看上去没什么两样。
然后,他就上了移民局的车,被送往专门关押偷渡者的地方。
一天一夜以后,紫罗兰色瞳孔的女人坐在旅店的小酒吧里,闻着酒杯里的茴香味。
“那个墨西哥人不见了。”她望着空荡的吧台说。
“是啊。”俊俏的男人躺在沙发上,似乎并不关心。
“你在想什么呢。”女人说。
“未来主义诗歌运动。”男人面无表情地说。
“什么?”
“未来主义诗歌运动。”
“那是什么?”
“每一个人类的未来。”他说着,打了个哈欠。
“那会是什么呢。”女人说。
“孤独、无聊又琐碎的日子。”
“再帮我买一杯酒吧。”男人说。
于是女人站了起来,走到吧台边,要了一杯鸡尾酒。
男人躺着沙发上,眯着眼睛说,“谢谢你,宝贝。”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们上楼去吧,享受一下午后的阳光。”
“好啊。”女人温柔地说道,将他搂在怀里,扶了起来。
随后他们回到了窄小的房间里,他搂着女人的腰,躺在床上,让她轻抚着他的耳朵。
“所以你平常都干些什么呢。”女人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他的脸颊说道。
“我写诗。”
“那不算一个正经职业,不是么。”女人笑道。
男人点头说,“对,实际上,我什么都不干。”
女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抓了抓他的头发。
“能给我看看你写的诗么。”她说。桌子上放着一张白色的便签。
“看吧,”男人说,“我写得很糟糕,但是我从来不介意在任何地方朗读出来。”
女人拿起便签,看着上面柔软的字迹。
抱有以下意图的
诗歌
皆失败了
——死亡
怀才不遇
一种关于更美好社会的幻想
以及对当下的讥讽
只有以下事实
是成立的
在哈气连连的午后
打开阳台的门
鸟儿在阴霾中不断
鸣叫
“我觉得写得很好。”她笑道。
“写得不好。”男人说。
“但是我爱你。”
说着他钻进了她的怀里,将耳朵贴在了她的肚子上。
他们在床上躺到了第二天中午,男人站起来晒了一会儿太阳,女人去楼下买了一瓶龙舌兰以及几块三明治,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床上,躺在一起,断断续续地喝完了那瓶龙舌兰。夜深的时候,他们终于穿好了衣服,从床上起来,来到楼下的酒吧——哪里昏暗,没有别的人,他们就坐在哪里,静静地享受着蓝色的灯泡映在墙上的光。一整天几乎没说过话。
两周以后,一个大个子墨西哥人被遣返回了老家。奇怪的是,他只被关了十多天,而有些人出于复杂的文件原因,通常要在里面等上几个月,看守所里的伙食比他以往吃的食物可口(他们每天吃番茄煮豆,偶尔还能吃上香肠与煎蛋)。他回来坐的是大巴,用半天穿越了他徒步跋涉几天的沙漠。
他回到了墨西哥边境的那座小城,直接走进了一间酒吧,坐了下来。他没有点酒,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后来他坐到了门口的台阶上,在烈日下,低着脑袋。
一个孩子走了过来。
“你回来了?”他说。
“我被遣返了。”大个子说。
“阿美利卡有什么。”孩子问。
“一道铁丝网。”他说。
“那是什么?”孩子不解地问道,“阿美利卡没有金子么?”
大个子没有答话。
孩子接着说道,“我叔叔告诉我,阿美利卡有一座巨大的红色岩石,上面有一座大赌场,有数不清的钞票,可以买下好几个墨西哥。”
“小伙计,”大个子说,“你可以帮我买一些吃的么。”
“可以啊,你把钱给我吧。”说着孩子伸出稚嫩的手。
可是大个子并没有给他钱,于是孩子就扫兴地离开了。
后来大个子墨西哥人来到他之前工作的农场,有一些牛仔在给农场主清洗马匹,看见他没有说什么,之后他走进大棚里,发现他的床位已经被一个新来的墨西哥人占了。
他同其他几个牛仔讲了话,他们将他带到老板那里,大个子将自己的遭遇讲了出来,祈求老板再给他一份工作,老板爽快地答应了,能干活的人永远不嫌多。
他说自己的腿受伤了,只要躺上两天就能恢复工作。于是他们同意他在一张木板上躺下来,并且给他水、土豆和玉米卷饼。
大个子在木板上躺着,一言不发。晚上,几个同宿舍的牛仔围在一起打扑克,他们可怜的收入全部归到了一个人手上,人们唉声叹气地回到床上。
第二天依旧如此。
第三天早上,大个子没有去工作,而是直接离开了农场。
他来到小镇上,在酒吧里坐了一会儿,之后一个恶棍走进来,坐在吧台上,索要了一杯酒。
大哥子走了过去,在他耳边悄声道,“我认识你的表哥,我欠了他一笔钱还没还,您可以帮我向他求求情么?”
“拜托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什么都愿意做。”他哀求道。
恶棍听后,感到很高兴,他决定先把他揪到后巷揍一顿。
于是他拉着大个子来到后巷,准备朝着他的腹部打出一记刺拳。
大个子捏住了他的拳头,同时脑袋朝着他的鼻梁顶去。几个回合后,恶棍倒在了地上。
大个子从恶棍衣服里掏出了一沓钞票,将他肥硕的躯体拖进了巷子深处,离开了这里。
之后,他去商店里买了一副新手套、一双靴子和一件披风,又买了水壶和干粮;上了一辆小巴士,在最北边的站台下车,朝着荒漠深处走去。
几天之后,一个墨西哥人徒步走到了边境的铁丝网附近,他每走一步,就要歇上一步的时间。他在一处岩石下藏了下来,揉了揉已落下永久残疾的左腿。
他坐在地上,静静地等待月亮显现。月亮出现了,他注视了数个小时。
夜深时,他开始一瘸一拐地朝着铁网走去。
他走得非常费力,可是他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世界原本就只有他一个人。
他来到铁网前,翻过了墙上的铁刺。他的全身又一次被割开,随后,从地上爬起来,一步一步朝前走去。
一支玩具箭射在了他的屁股上,让他扑倒在地上。
“好球!“射箭的士兵欢呼道。
黑夜中一辆熄灭的卡车突然亮了灯,朝着墨西哥佬奔去,墨西哥人连忙爬起,屁股上又挨了一箭。
“我跟你打赌,今晚一定有人会翻过来。”他得意道。
“赶紧给我十块钱。”他朝开车的家伙伸出手。
开车的人闷闷不乐地说,“你上次打赌输了还没给我钱呢!”
接着两个人下车,合力把屁股上中箭的墨西哥人绑了起来。
“这家伙可真沉!”射箭的士兵骂道。
墨西哥人感到一阵天翻地覆,在黑暗中,手电筒的光不停扫过他的眼睛。
“这个蠢货在哭什么呢。”射箭的士兵将他踹进了卡车里,合上了仓门。
开车的士兵说 :“这些蠢货肯定永远不知道,我们的红外线设备,即使在黑夜下,也能看见他们的肥屁股。”
“赶紧给钱吧!”射箭的士兵指着他笑道,之后他们打开收音机,放起了粗俗的乡村摇滚乐,一路上不停骂着。
在十公里外的一间小旅馆里,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两点,酒廊里空无一人,女酒保从箱子里取出了一张黑胶唱片,放在唱片机上。难以捉摸的忧伤旋律,顺着楼梯,传进了每一个孤单的小房间里。
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有一对年轻男女抱在一张小床上,月光从窗户照在了他们的肉体上,在白色的床单上留下一道蓝色的幻影。
“未来会怎么样。”女人抚摸着怀中男人说。“孤独、琐碎又无聊。”男人说。
女人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捏了下他的耳朵。
“你害怕吗?”男人问。
“不怕。”女人说。
过了一会儿,楼梯底下的音乐变得无忧无虑起来,就像一个人在夜幕下的天台上吹起口哨。
“我们站起来,跳一会儿舞吧。”女人说。
“好啊。”男人说。
于是她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他们随着月亮照在地板上的斑驳光亮,开始舞蹈,一会儿,月亮就变成了红色。
第二天早上,沙漠上出现了一片乌云,他们沉浸在小房间里的阴郁中,不愿打开眼前的房门。他们一整天只吃了一份卷饼,靠着一瓶烈酒充饥。
隔日,太阳再次照进了这间木头做的旅馆,一些吵嚷的墨西哥人和骄傲的白人牛仔走了进来,他们大口吃饭、说脏话、喝酒,之后便离开了。到了下午,酒吧里只剩下那对年轻男女,与一只在光柱上爬行的瓢虫。
男人躺在女人的腿上,温和地闭着眼睛。
女人沉醉地看着他,用指尖划过他的耳朵。
“我身上的钱马上要花完了,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呢?”女人说。
“我不知道。”男人说,用指尖抓住了女人的手。
女人没说什么,只是轻轻捏了下他的手掌。
七分钟之后,男人说,“我很开心。”
“为什么呢?”女人笑着说。
“我已经知道如何实现了。”男人说。
“实现什么?”女人说。
“未来主义诗歌运动,”他说,“无论未来多么令人感到无聊,诗歌都会继续下去。”
女人没有说话,只是笑嘻嘻地捏着他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
她说道:“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